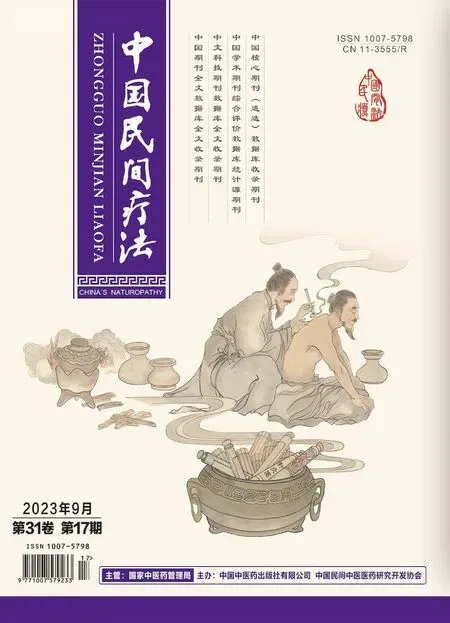葛根湯加減臨床經驗述要
袁 媛,高立珍
(1.湖北中醫藥大學,湖北 武漢 430061;2.湖北中醫藥大學附屬十堰市中醫醫院,湖北 十堰 422000)
葛根湯為辛溫解表劑,一般臨床上主要發揮其發汗解表、生津通絡之功,針對外感風寒實邪之證。在現代臨床應用過程中發現,葛根湯可治療多系統疾病,如腰椎間盤突出癥[1]、反復上呼吸道感染[2]、高血壓合并糖尿病[3]、胃腸型感冒[4]、難治性鼻竇炎[5]等。在《傷寒論》中,筆者認為臨床運用葛根湯僅局限于太陽表實證,然葛根湯并非只用于治療《傷寒論》中所涉及的病種,基于“異病同治”的理念,將其靈活運用臨床各科,取得顯著的療效。
1 濕疹病案
患者,女,50歲。2021年11月10日初診。患者確診為濕疹5年,經中西藥物久治而乏效。患者每于季節交替時發作,以秋冬為甚,瘙癢劇烈,嚴重時抓破流黃色膿水。局部皮膚破潰,范圍不斷擴大,夜間瘙癢程度加重,反復結痂、破潰,遇熱后瘙癢、疼痛癥狀加重,納食、睡眠欠佳,大便溏,小便黃。于醫院就診,診斷為過敏性皮炎,予以激素類藥物治療后稍緩解,但反復發作,病情逐漸加重。患者曾出現黑朦1次,數分鐘后自行緩解。2014 年行子宮+卵巢全切術后停經。刻診:患者頸部及雙下肢瘙癢難忍,皮損處有脫屑,右側頸部有一約5 cm×5 cm 的皮損,色暗,可見明顯抓痕。患者面色黃,體瘦,額頭中央有“川”字皺紋,頸部僵痛,怕冷,白天困倦,精神較差,大便溏,每日2次,小便可,舌質淡紅,苔白膩,脈沉。西醫診斷:過敏性皮炎。中醫診斷:濕疹(脾濕運阻證)。治則為健脾化濕,祛風活血。予以葛根湯加味:葛根30 g,麻黃10 g,桂枝15 g,白芍15 g,甘草片10 g,生姜10 g,大棗15 g,白術15 g,茯苓15 g。5劑,每日1劑,水煎分3次飯后溫服。囑患者覆取微似汗。
2021年11月24日二診:患者服藥后微微出汗,瘙癢明顯改善,頸部皮損變淡,雙下肢皮損消退,頸部僵痛較前減輕,精神轉佳,大便仍溏,每日1~2次,舌質淡紅,苔薄,脈沉。予以葛根湯合四物湯加減:葛根30 g,麻黃10 g,桂枝10 g,赤芍10 g,熟地黃15 g,當歸15 g,川芎10 g,防風12 g,蟬蛻9 g,刺蒺藜12 g,白鮮皮20 g,制首烏20 g。5劑,每日1劑,水煎分3次飯后溫服。
患者服藥后電話告知皮膚瘙癢基本消失,因苦于服藥,故停藥觀察。
按語:《素問·至真要大論》認為“諸痛癢瘡皆屬于心”,故許多醫家在治療此類反復發作、瘙癢的皮膚疾病時,皆考慮為臟腑熱盛,治療立足點集中于清泄臟腑內熱,臨床多使用五味消毒飲、當歸飲子、消風散等[6],但驗之臨床,有時效果并不理想。高立珍老師診治此類患者時,并不局限于給患者止癢。本患者以瘙癢為主癥,其特點為瘙癢反復發作,且以秋冬季為甚。患者頸僵痛,無汗,惡寒,精神困倦,正如條文所述“項背強,無汗惡風”,選用葛根湯為基礎方。因患者苔白膩,為有濕之征,故加白術、茯苓健脾利濕,用本方取效的關鍵在于覆取微似汗,汗出則癢減。二診時患者諸癥改善,考慮患者久病耗傷氣血,而皮膚依靠血之滋養,故合用四物湯養血活血,達到“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之效;同時加用防風、蟬蛻、刺蒺藜、白鮮皮等祛風止癢之品,可加強療效。
2 不寐病案
患者,女,14歲。2020年12月29日初診。患者訴近期自覺疲憊,困乏不適,但難以入睡,自覺焦慮不安,影響日常生活與學習。患者于醫院就診后完善相關檢查后未見明顯異常。后轉入失眠科就診,診斷為失眠,予以西藥調整睡眠質量(具體藥物不詳)。患者服藥后睡眠質量緩解,但自行停藥后,病情復發,且癥狀較前加重。刻診:患者前額及肩背部散在痤瘡,色暗,可見明顯抓痕,已結痂。患者面色淡白,少氣懶言,語聲低微,自覺頸背部僵硬疼痛不適,頭悶脹,怕冷,易受涼,平素不易出汗。白天困乏,精神萎靡,夜間煩躁,難以入睡。患者提及若出現難以入睡情況時,前額及肩背部則起痤瘡。既往有“心臟瓣膜缺損”病史,偶有心慌。大便干,每日1 次,易解,小便可。經期正常。舌質淡,邊有齒痕;苔白膩,脈沉。西醫診斷:失眠。中醫診斷:不寐。治則為補脾益氣、祛瘀活絡。予以葛根湯加味:葛根30 g,蜜麻黃6 g,桂枝20 g,白芍20 g,甘草片10 g,生姜10 g,大棗20 g,香園葉10 g,白術15 g,茯苓15 g,澤瀉15 g,當歸10 g,川芎10 g。5劑,每日1劑,水煎,分三餐飯后溫服。
2021年1月8日二診:患者白天精神好轉,夜間入睡較前容易,面部及肩背部痤瘡明顯消退,繼服原方7劑以鞏固治療。療程結束后患者不寐癥狀明顯改善。
按語:臨床治療不寐多從調和營衛的角度出發,其思路多局限于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酸棗仁湯等。本患者雖以不寐為主要癥狀前來就診,但患者有頸部僵痛、無汗、惡寒等陽明經征象,患者舌質淡,邊有齒痕,脈沉,此為濕氣之象,且患者不寐時頭面及肩背部易起痤瘡。痤瘡屬于中醫“肺風粉刺”范疇,《雜病源流犀燭》記載:“粉刺屬肺,總皆血熱滯而不散之故。”六經中手足陽明經行經頭面部,陽明經為氣血之經,若氣血運行阻塞,郁結成熱,堆積于頭面部,則易形成痤瘡[7]。“頭為諸陽之會”,手足三陽經均循行于此,陽明經為多氣多血之經。該患者不寐,心神難安,氣血運行至頭面部而受阻,陽氣郁結于上,則面部易生痤瘡,根據“其在皮者,汗而發之”的治法,予以透邪發表,使面部陽氣升發,達到陰平陽秘、陰陽調和的目的,則不寐解、痤瘡消。四診合參,高立珍老師考慮本患者辨證為太陽陽明經絡瘀滯不暢,使陽難以入陰,最終導致不寐。張元素提出“風升生”的藥類理論,認為葛根味辛、氣淡,質清易上行[8]。高立珍老師認為本方中葛根的作用有二:一為升陽,脾氣運化失常,則水濕困阻,木克土,能散濕邪,又因其可升陽,則使濕氣上行,由肌表發散;二為醒神,其性上行至頭面部,可開竅醒神。佐以茯苓、白術以強化健脾滲濕之效;患者大便干、頭面及肩背部易生痤瘡,此為熱瘀于內,予以澤瀉清熱,當歸、川芎活血行氣,以達疏通運行之效。
3 痹證病案
患者,男,38歲。2021年5月13日初診。患者確診為類風濕關節炎多年,經中西醫藥物治療后病情控制欠佳。患者每于氣候變化時發作,以冬春為甚,下雨前1 d疼痛癥狀加重,嚴重時難以入睡,影響日常生活。于醫院完善風濕免疫檢查提示:類風濕因子明顯升高;紅細胞沉降率、超敏C 反應蛋白升高;血常規、尿常規、肝腎功能未見明顯異常。西藥予以抗風濕藥物治療后,患者自覺手指關節及膝關節疼痛無明顯好轉。刻診:患者雙手指間關節明顯變形,屈伸活動不利,自覺雙手指近關節腫脹感,晨僵明顯,自行活動數小時后僵痛感稍緩解。足跟腫脹,雙膝關節脹痛不適。患者體瘦,面色萎黃,手足易冷,腰部怕冷,不易出汗,自覺疲憊,難以提高精神。夜間睡眠質量差,易醒,醒后難以入睡。大便質稀,不成形,每日2~3次。舌質稍暗紅,苔膩,脈沉。西醫診斷:類風濕關節炎。中醫診斷:痹證(風寒濕痹)。治則為祛風除濕,疏經通絡。予以葛根湯加味:葛根30 g,生薏苡仁30 g,麻黃10 g,桂枝20 g,白芍20 g,甘草片10 g,干姜6 g,大棗10 g,茯苓30 g,白術30 g,防己10 g,黃芩片10 g。5 劑,每日1劑,水煎分3次飯后溫服。
2021年5月21日二診:患者自覺四肢關節疼痛較前稍緩解,指間關節屈伸活動仍不利,白天精神較前好轉,但夜間仍易醒,醒后難以入睡。大便仍稀,每日2~3次。舌質暗,苔厚膩,脈沉。處方:上方葛根加至60 g,加蜈蚣1 條。5 劑,每日1 劑,水煎分3 飯后溫服。
2021年5月25日三診:患者訴左小腿僵痛不適,精神轉佳,大便偶成形,每日兩次。舌質紅,苔膩,脈沉。處方:葛根60 g,麻黃10 g,生薏苡仁30 g,桂枝20 g,白芍20 g,甘草片10 g,干姜6 g,大棗10 g,茯苓30 g,白術30 g,防己10 g,黃芩片10 g,香園葉10 g。5劑,每日1劑,水煎分3飯后溫服。
患者服藥結束后,雙手近端指間關節疼痛明顯緩解,四肢無僵痛之感,手足畏汗,怕冷癥狀明顯改善。
按語:本案患者諸身關節疼痛,不易汗出,高立珍老師認為發汗是治療關節疼痛的重要突破點,除不易汗出外,患者還有精神困倦、夜寐難安、手足易冷的癥狀,這些則是選擇葛根湯的根據。對于痹證而言,經絡不通,不通則痛。葛根湯中葛根甘平而涼,走陽明經,行津液而潤筋脈,有舒經通絡之效,麻黃、桂枝辛溫發汗,疏太陽之邪,芍藥、甘草生津養液,緩急止痛。因患者舌質微暗紅、苔膩,表明有濕熱之象,故用薏苡仁清熱利濕,黃芩清熱,茯苓、白術健脾祛濕。患者自覺怕冷,腰部易涼,高立珍老師考慮為風邪傷表入其內所致,故加防己祛風邪、解表止痛。二診時,患者疼痛癥狀緩解,但仍感精神萎靡,則葛根加倍。三診時,患者肢體僵痛,故加蜈蚣等蟲類藥通經活絡。
4 小結
在臨床運用葛根湯時,應抓住“頸部僵痛、畏寒、無汗、精神困倦”等特征,時刻謹記病機,牢牢把握證與癥相結合,臨床上根據患者的癥狀及體征,靈活運用葛根湯加減,使其在臨床上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