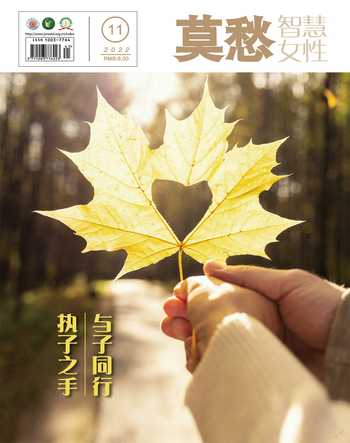凝望十年好風(fēng)景 拓路踏歌礪初心
馬寧

看望全國(guó)“最美家庭”梅應(yīng)愷家庭

婦聯(lián)執(zhí)委深入工廠車間宣講習(xí)近平新時(shí)代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思想
十載征程春華秋實(shí),沐風(fēng)櫛雨砥礪初心。黨的十八大以來(lái)的十年,是揚(yáng)州綜合實(shí)力提升最快、城鄉(xiāng)面貌變化最大、人民群眾得到實(shí)惠最多的十年,也是揚(yáng)州婦女事業(yè)成績(jī)斐然、婦聯(lián)形象不斷刷新、婦女風(fēng)采熠熠生輝的十年。
十年來(lái),揚(yáng)州市婦聯(lián)堅(jiān)持以習(xí)近平新時(shí)代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思想為指引,充分發(fā)揮黨和政府聯(lián)系婦女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推動(dòng)?jì)D女工作躍上新臺(tái)階、婦女運(yùn)動(dòng)實(shí)現(xiàn)新跨越。
凝望這十年,團(tuán)結(jié)引領(lǐng)堅(jiān)強(qiáng)有力
全市各級(jí)婦聯(lián)組織堅(jiān)持黨的領(lǐng)導(dǎo),引領(lǐng)廣大婦女在共筑夢(mèng)想中樹立志向、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在建設(shè)“好地方”揚(yáng)州的過(guò)程中激揚(yáng)巾幗之志、奉獻(xiàn)巾幗之力、彰顯巾幗之美。
思想引領(lǐng)潤(rùn)物無(wú)聲,“巾幗心向黨”系列群眾性宣傳教育活動(dòng)如火如荼,10萬(wàn)余場(chǎng)各類宣講輻射100多萬(wàn)人次,不斷增強(qiáng)廣大婦女對(duì)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志愿服務(wù)細(xì)致入微,組織動(dòng)員15萬(wàn)名巾幗志愿者、600多個(gè)巾幗志愿服務(wù)組織活躍在揚(yáng)城大街小巷,積極投身疫情防控、文明勸導(dǎo)、家庭賦能、困境關(guān)愛等志愿服務(wù),奮斗堅(jiān)守、向陽(yáng)而生的溫暖形象已然成為“好地方”揚(yáng)州的靚麗風(fēng)景,投身疫情防控,聞令即動(dòng)、全力迎戰(zhàn),市婦聯(lián)掛包的淮海路157號(hào)封閉小區(qū)接受了國(guó)家、省各級(jí)領(lǐng)導(dǎo)的防疫工作督導(dǎo),彰顯了婦聯(lián)人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
榜樣先進(jìn)深入人心,充分發(fā)揮婦女在社會(huì)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兩個(gè)獨(dú)特作用,持續(xù)挖掘選樹各領(lǐng)域各行業(yè)三八紅旗手(集體)、巾幗文明崗、最美家庭等優(yōu)秀典型近4000個(gè),在建設(shè)“好地方”揚(yáng)州的火熱實(shí)踐中展現(xiàn)新時(shí)代巾幗風(fēng)采。
凝望這十年,巾幗發(fā)展潮涌風(fēng)勁
全市各級(jí)婦聯(lián)組織胸懷“國(guó)之大者”,引領(lǐng)廣大婦女把個(gè)人夢(mèng)想融入到為國(guó)家富強(qiáng)、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奮斗的實(shí)踐之中,繼往開來(lái),爭(zhēng)創(chuàng)一流。
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火熱激揚(yáng),成立婦女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基金,出臺(tái)婦女雙創(chuàng)基金應(yīng)對(duì)疫情防控、支持巾幗家政提質(zhì)擴(kuò)容和鄉(xiāng)村振興巾幗行動(dòng)的專項(xiàng)政策形成“組合拳”,累計(jì)發(fā)放婦女創(chuàng)業(yè)擔(dān)保貸款15.6億元,始終保持回收率99.9%;連續(xù)四年舉辦巾幗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大賽,打造女大學(xué)生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的“夢(mèng)想驛站”,建立揚(yáng)州市巾幗融創(chuàng)空間,支持婦女投身新領(lǐng)域、新產(chǎn)業(yè)、新業(yè)態(tài)創(chuàng)業(yè)。
鄉(xiāng)村振興蓄勢(shì)添能,融合多方資源開設(shè)“巧富課堂”,組織全國(guó)技能能手、鄉(xiāng)土人才、淮揚(yáng)菜烹飪技藝傳承人等走進(jìn)農(nóng)村,舉辦各類實(shí)用技能培訓(xùn)300多期,帶動(dòng)數(shù)萬(wàn)名農(nóng)村婦女學(xué)新知、創(chuàng)新業(yè)。
科技融合乘風(fēng)而上,聚焦科技創(chuàng)新,出臺(tái)科技創(chuàng)新巾幗行動(dòng)實(shí)施意見,推動(dòng)實(shí)施女性科技人才引領(lǐng)、成長(zhǎng)、女性助力、關(guān)愛四大行動(dòng);開展女性科技人才尋訪活動(dòng),建立女性科技人才信息庫(kù);開展“科創(chuàng)未來(lái)·她力量 ?強(qiáng)國(guó)復(fù)興·我先行”女性科技人才主題活動(dòng)、“科創(chuàng)她力量 ?巾幗綻芳華”女性科技工作者沙龍活動(dòng)等,團(tuán)結(jié)引領(lǐng)女科技工作者、女企業(yè)家在產(chǎn)業(yè)科創(chuàng)名城建設(shè)中展現(xiàn)巾幗擔(dān)當(dāng),貢獻(xiàn)巾幗力量。
凝望這十年,平安底色持續(xù)擦亮
全市各級(jí)婦聯(lián)組織堅(jiān)守“溫暖之家和堅(jiān)強(qiáng)陣地”初心,堅(jiān)持男女平等基本國(guó)策,暢通婦女訴求表達(dá)渠道,切實(shí)維護(hù)婦兒合法權(quán)益。
“未病先防”固本強(qiáng)基,性別平等咨詢?cè)u(píng)估“四個(gè)必須”模式成為全省示范,推動(dòng)在揚(yáng)州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成立全省唯一一家性別平等研究中心;“微家+議事會(huì)”、組級(jí)議事會(huì)等做法為全省婦女議事工作提供了鮮活的經(jīng)驗(yàn)。
“狠下猛藥”久久為功,“守護(hù)成長(zhǎng)、幸福一生”兒童青少年關(guān)愛保護(hù)工程將女童保護(hù)課程納入全市教學(xué)計(jì)劃,培訓(xùn)志愿者講師682名,開展課程2200余節(jié),受益人數(shù)11萬(wàn)多人次;積極推廣人身安全保護(hù)令和家暴告誡制度,我市發(fā)出全省第一份人身安全保護(hù)令、全省第三份家暴告誡書,高質(zhì)量維護(hù)婦兒合法權(quán)益。
“最后一米”溫暖人心,“護(hù)在身邊”的婦女兒童權(quán)益保護(hù)法律服務(wù)工作站實(shí)現(xiàn)市縣鄉(xiāng)全覆蓋,“定點(diǎn)維權(quán)+流動(dòng)普法”模式在全市推廣;2個(gè)公益性心理咨詢服務(wù)中心、180多人的公益心理咨詢聯(lián)盟溫暖了疫情防控期間的點(diǎn)滴瞬間,切切實(shí)實(shí)將黨和政府的關(guān)懷、改革發(fā)展的成果、婦聯(lián)“娘家人”的溫暖送到廣大婦女和家庭的心中。
凝望這十年,和諧氛圍向上向善
全市各級(jí)婦聯(lián)組織深入踐行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引領(lǐng)廣大婦女為形成人人相互關(guān)愛、家家幸福安康、社會(huì)和諧發(fā)展的文明新風(fēng)貢獻(xiàn)力量。
優(yōu)良家風(fēng)春風(fēng)化雨,“文明家風(fēng)·科學(xué)家教”“最美家風(fēng)”等巡講覆蓋全市,累計(jì)開展線上線下巡講近1100場(chǎng),受眾達(dá)52萬(wàn)人次;“講、秀、曬、薦、議”尋訪市級(jí)以上最美家庭300戶,各地家風(fēng)館、家風(fēng)長(zhǎng)廊、家訓(xùn)家書等將德善潤(rùn)家的良方送入千家萬(wàn)戶。
實(shí)事辦好碩果豐盈,積極回應(yīng)婦女兒童需求,高標(biāo)準(zhǔn)建成市婦女兒童活動(dòng)中心市民中心部,提檔升級(jí)婦女兒童活動(dòng)中心解放橋部;率先建成婦女兒童規(guī)劃分性別統(tǒng)計(jì)網(wǎng)絡(luò)直報(bào)平臺(tái);聚焦婦女兒童生存發(fā)展中的突出問(wèn)題,推動(dòng)在全省率先設(shè)立困境兒童助學(xué)基金,累計(jì)發(fā)放助學(xué)金1401.2萬(wàn)元,受益7006人次,《關(guān)于進(jìn)一步完善困境兒童關(guān)愛保護(hù)機(jī)制》工作信息得到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國(guó)務(wù)院副總理劉延?xùn)|和國(guó)務(wù)委員王勇的批示;發(fā)揮市翔宇婦女兒童基金會(huì),持續(xù)做好“春蕾計(jì)劃”傳統(tǒng)品牌,打造“勵(lì)志女孩”等創(chuàng)新品牌,籌集百萬(wàn)資金招募百名愛心媽媽結(jié)對(duì)幫扶百名留守困境兒童,試點(diǎn)推動(dòng)“一戶一策微關(guān)愛”項(xiàng)目,探索精準(zhǔn)關(guān)愛困境婦女兒童長(zhǎng)效服務(wù)機(jī)制。
兒童友好共向未來(lái),率先探索建設(shè)“兒童友好城區(qū)”,編制《建設(shè)兒童友好城市行動(dòng)規(guī)劃》,“推動(dòng)兒童友好城市、兒童友好社區(qū)建設(shè)”納入揚(yáng)州市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第十四個(gè)五年規(guī)劃綱要和2035年遠(yuǎn)景目標(biāo)草案,牽頭完成建設(shè)方案,啟動(dòng)兒童友好公園、社區(qū)、圖書館建設(shè)指引編制工作,“兒童友好”公益活動(dòng)精彩紛呈,“童話城事”兒童議事品牌日益擦亮。
凝望這十年,守正創(chuàng)新行穩(wěn)致遠(yuǎn)
全市各級(jí)婦聯(lián)組織緊緊圍繞黨政中心,聚焦改革重點(diǎn),以敢為人先的干勁和攻堅(jiān)破難的韌勁,跑出“改革破難”趕考“加速度”。
組織建設(shè)星羅棋布,按照“哪里有婦女,哪里就有婦聯(lián)組織”的原則,推進(jìn)婦聯(lián)組織建設(shè)“全域提升”。縱向婦聯(lián)組織向社區(qū)網(wǎng)格、村民小組等延伸,橫向向社會(huì)組織、商圈園區(qū)、新業(yè)態(tài)新就業(yè)群體等拓展,構(gòu)建完善立體化、多層面的婦聯(lián)組織體系,全市成立行業(yè)(系統(tǒng))婦聯(lián)上百家、新興領(lǐng)域婦聯(lián)509家;全市300多個(gè)富有區(qū)域特色、個(gè)性鮮明的婦女微家在發(fā)動(dòng)廣大婦女助力鄉(xiāng)村振興和脫貧攻堅(jiān)、維權(quán)、促進(jìn)婦女創(chuàng)業(yè)就業(yè)、開展關(guān)愛幫扶、提升素質(zhì)、活躍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打通聯(lián)系服務(wù)婦女群眾的最后一米。
“內(nèi)孵外引”雙向奔赴,深化“婦聯(lián)+女性社會(huì)組織”工作模式,搭建揚(yáng)城女性公益“新家園”,積極發(fā)揮揚(yáng)州市女性社會(huì)組織發(fā)展促進(jìn)會(huì)作用,盤活資源建成孵化基地,圍繞“專一群體+全面服務(wù)+精準(zhǔn)孵化”理念,召集凝聚了103家聯(lián)系緊密的女性社會(huì)組織,提供內(nèi)外部學(xué)習(xí)交流、優(yōu)化服務(wù)1000多人次;積極申報(bào)實(shí)施社工服務(wù)項(xiàng)目、組織開展公益創(chuàng)投;全力探索符合揚(yáng)城本地女性社會(huì)組織及公益女性成長(zhǎng)互助需求的支持體系,為廣大婦女兒童家庭提供高質(zhì)量、專業(yè)化、可持續(xù)的社會(huì)服務(wù)。
激活隊(duì)伍“一池春水”,不拘一格從基層、各領(lǐng)域推選優(yōu)秀人才,各級(jí)婦聯(lián)選配出兼掛職副主席2582人,執(zhí)委12000多人,爭(zhēng)做廣大婦女群眾的“領(lǐng)頭雁”和“貼心人”,基層工作力量得到進(jìn)一步壯大。建立婦聯(lián)干部、婦女干部聯(lián)系制度,開展執(zhí)委履職“五個(gè)一”活動(dòng)、“在你身邊·執(zhí)委領(lǐng)跑行動(dòng)”,組織巾幗文明崗、巾幗志愿團(tuán)隊(duì)和女性社會(huì)組織走進(jìn)基層、走向一線,“崗村結(jié)對(duì)”“崗戶結(jié)對(duì)”等活動(dòng)收獲群眾滿滿點(diǎn)贊。
回顧十年的探索實(shí)踐,我們深刻體會(huì)到,必須堅(jiān)持黨的領(lǐng)導(dǎo),才能做好新形勢(shì)下的婦女工作,才能當(dāng)好黨聯(lián)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必須圍繞中心、服務(wù)大局,才能激發(fā)婦女事業(yè)發(fā)展的動(dòng)力和活力;必須堅(jiān)持植根婦女群眾,才能贏得她們真心的擁護(hù)和信賴;必須保持勇攀新高的激情和改革創(chuàng)新的精神,才能真正適應(yīng)新形勢(shì),將婦聯(lián)組織建設(shè)成婦女群眾的堅(jiān)強(qiáng)陣地和溫暖之家。
風(fēng)勁潮涌自當(dāng)揚(yáng)帆破浪,任重道遠(yuǎn)更需策馬揚(yáng)鞭,新時(shí)代的號(hào)角已經(jīng)吹響,新征程的旗幟已經(jīng)高揚(yáng),我們將在全國(guó)、省婦聯(lián)的悉心指導(dǎo)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堅(jiān)強(qiáng)領(lǐng)導(dǎo)下,在廣大婦女群眾和社會(huì)各界的關(guān)心支持下,初心如磐,奮楫篤行,聚焦婦女和家庭所急所需所盼,真情服務(wù)婦女兒童和家庭關(guān)切,不斷提升婦女兒童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把“好地方”揚(yáng)州建設(shè)得好上加好、越來(lái)越好貢獻(xiàn)巾幗力量。
圖片由揚(yáng)州市婦聯(lián)提供
編輯 周曉序 24754968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