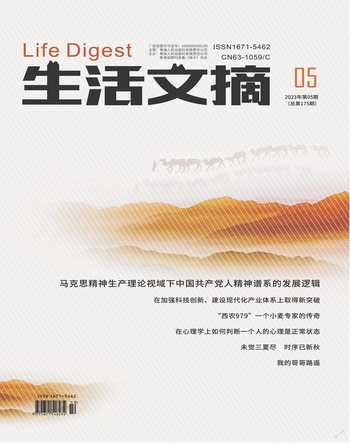從《禹貢》看中華文明的特性
《禹貢》的問世標志著中華先民首次對九州大地進行完整且理性的認知,通過對九州之間山脈河流及其走向、流域等方面詳盡描述,揭示了中華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重要的地理觀念和社會結構。《禹貢》提出的五服貢納制度,在地方與中央之間建立了秩序化和制度化的關系,形成了中華文明思想體系的基礎。《禹貢》開創了后代人文化地理研究的先河,展現了中華早期文明發展的歷史連續性,體現了中國古代大一統觀念的萌芽。
前言
距今4000多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集團匯集、融合而成的核心——華夏集團。它與周圍各集團進行著文化交流與融合,使得華夏集團最早具備了文明條件,并率先進入了堯舜禹時代的中華早期文明時代。[1]距今約3800年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建立,夏王朝以禹為核心人物。《禹貢》是先秦經典著作《尚書》中的一篇,全文分九州、導山、導水、五服四部分,記載了大禹治水及各地向冀州交納貢賦的情形。《禹貢》的成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應該是在最初藍本形成后,在長時間的流傳過程中逐漸增添了新內容,反映出不同時代的痕跡,最終成書于戰國時期。
《禹貢》開創了后代人文化地理研究的先河,展現了中華早期文明發展的歷史連續性,體現了中國古代大一統觀念的萌芽。從部落聯盟到國家王朝,中華早期文明經歷了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力相結合、宗族制度向宗法制度轉變、部落酋長制向王國政治結構轉變等演進過程。同時,以人文地理為基礎構建社會結構,以貢賦制為基本形式構建國家政治體系,這些都是中華早期文明發展的基本特征。
一、大禹治水:中華文明發展的動力
在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早期,神權與王權始終沒有完全分離。禹作為傳說人物,既是一個人又被賦予了神性。他被視為鯀的兒子、顓頊之后,排入了大一統的帝王世系中。這種人神雜糅的背景下,禹成了一個具有雙重性質的傳說人物。
大禹治水的傳說,在早期文本敘述中,主要強調大禹降土和敷土的功績。例如,《天問》中提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詩經》“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中也描述了大禹敷下土方、開辟新國家領域等偉績。當洪水來臨時,人們不得不尋找高地或山川避難,敷土成了人們生存和生活所必需的緊迫任務,這也是為什么早期文獻中強調大禹降土和敷土方面的功績。隨著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特別是戰國時期,人們開始探索解決洪水的方法。大禹治水傳說便逐漸加入,并成為主要敘述內容。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墨學派興起,將大禹視為賢能之君,通過治理洪水泛濫展現了圣王的智慧和領導才能。因此,在文獻中對大禹治水事跡的描述逐漸增多,并且被人們廣泛傳頌。
大禹治水傳說不僅是一個英雄故事,更是中華民族勇敢面對困難、開拓進取精神的象征。禹的英雄事跡和統治九州時展現出無私無我、惠民利民的高尚品質,讓九州各地區團結協作。從降土到治水,這一轉變彰顯了社會對于應對自然災害和保障生存安全的追求。《禹貢》記錄了大禹治水及各地向冀州交納貢賦的情形,通過對不同區域土壤、經濟狀況和物產的考察,人們確定了賦稅等級和貢物品類,并通過疏通水道來實現治水避災以保障民生,同時也確保了貢賦運輸的暢通。禹將九州萬邦協和為一體,成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分散的部落,這也為四方朝服納貢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推行“協和萬邦”的政治理念下取得了巨大成功,禹的功績更是中華文明形成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二、《禹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構建
在古代,由于江河水道處于自然狀態且容易堵塞,洪水泛濫成為常見現象。禹可能在一定區域內協調各鄰邦疏通水道以實現泄洪導水的目標,隨著大禹成功治理了洪澇災害,他接受了鄰邦的物產作為饋謝之禮。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初步的“禹貢圖”和《禹貢》。
到了西周時期,盡管天下未能完全一統,但周天子通過封邦建國和分封諸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天下共主。為了明晰疆域、掌握山川形勝、劃分區域以及征繳貢賦等的需要,周人對夏商已有的山川水道圖文進行了梳理和擴展,并將其繪制為反映西周時期地理物產的圖錄。由于周人對夏禹時期的“禹貢圖”和《禹貢》進行承襲與發展,符合統治合理性和尊夏心理要求。商代以河洛為中心的區域內大小邦國約有兩千,而周初諸侯至少也有八百。因此,在萬國林立的夏禹時代,以《禹貢》所載之規模,要求各地出產物品進貢至冀州或其他一地并不現實,但這并不能割裂《禹貢圖》與禹、夏之間內在關聯。[2]《禹貢》所描述的夏禹時代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存在著許多大小邦國,這些邦國之間相互封閉,缺乏交流和合作。然而,中華文明的形成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通過不同地區文化的裂變、撞擊和融合,逐漸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明。夏禹時期已經孕育出“協和萬邦”的理念,并產生了推動各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宏大政治構想的萌芽。
《禹貢》是中國古代治理思想演進過程中的重要文獻之一,它標志著九州地理劃分觀念的形成,并肇始了中國天下九州一統的觀念。《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對各地區的文化類型和文化習俗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這些論述揭示了中華多元一體文明格局的新發展以及《禹貢》對后代人文地理的影響。
三、九州:中華文化的中心觀
九州作為構建中國古代格局的一種視野,具有悠久的歷史。根據《禹貢》,大禹在平定洪水后,根據各地土地和資源的情況劃分了九州。許多文獻都提到了禹劃九州的觀念。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說:“開九州,通九道。”《左傳·襄公四年》也提到了:“芒芒禹跡,劃為九州,經啟九道。”而屈原在《天問》中對禹劃九州表示疑問。這些記載表明,“禹序九州”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九州包括了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州。關于九州起源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九州來源于戰國時期以前,是對古代部落征服和領土擴張過程中產生的區域概念。[3]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九州是基于三代歷史事實而形成,并成為戰國時期諸雄分野的重要依據。[4]不論是哪種觀點,九州的存在與變遷都成為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礎。
九州的劃分與中華文明的形成密切相關。根據《禹貢》,每個九州都有獨特的土質和自然地貌,這些因素決定了各地區物產、民風、民俗和語言等方面的差異。在《禹貢》中,冀州被標注為“正中”,冀州被視為九州之首,是天下之中心。這一觀念逐漸發展為中央王朝中心觀和中原文化中心觀的基礎,主導了幾千年的中華民族文明史。
《禹貢》不僅對各州的山脈河流進行了記述,還對全國范圍內的山脈走向和河流流域進行了整體性的描述,這標志著中華先民首次對九州大地的土地、山脈和河流進行了完整且理性的認知。通過以高山大河來劃分界域,形成了九州的地域觀和區域觀。
《禹貢》揭示了九州與中華文明形成之間的密切關系。《禹貢》中記述的各州的土地山川構成了各州的自然生態環境,而各州通過開墾土地、種植農作物、養蠶桑、修建水利設施、發展交通道路等人文活動,提高了人文生態環境的質量。這些活動促進了自然生態環境向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向轉化,并保證了國家貢賦制度的順利實施。這種理性認知是圍繞著“九州攸同”“四海會同”的國家中心觀展開的。人們將商人來往于九州之間看作是常態,將周人所居住之處視為王土,表達出中華文明中心觀念的延續與發展。從神秘觀念世界和宗教世界中解脫出來,人們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大自然(山川土地),展示了人類對自然界的理性認知,也展現了以人為主體的天人關系和人地關系時代觀念。這正是《禹貢》問世的歷史文化基礎,也是中華早期文明的主要特征所在。
四、五服制:中國古代治理思想
《禹貢》首次提出了五服制,包括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五個層次。五服制構建了夏代早期中原地區與四夷的關系圖,形成了內圈甸服、中圈侯服和綏服、外圈要服和荒服的分布格局。通過不同層級關系和地理空間上的分布格局來反映了王室與周邊部族、方國之間的關系。而“服”的含義是指對天子的服侍義務,不同“服”之間界線模糊,真正清晰鮮明的界線發生在華夏與荒服之間。
夏王朝采取了近似分封的制度,承認已存在的部族、方國政權,并推廣中原文化保衛中央和諸侯國的安全。五服制試圖在地理空間上構建一種公共秩序,以區分華夏族群與夷夏兩個群體,并確立了對天子的服務義務。這些思想和制度體現了華夏族群對于社會秩序和地域劃分的努力與設想,這一思想體系在中華早期文明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
在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上,構建了以中央王朝為核心的金字塔式文化思想體系。通過五服制度,地方與中央之間建立了秩序化和制度化的關系,形成了中華文明思想體系的基礎。這一思維定式已經深深地根植于古代中國社會,并成為古代中國最基本的思維模式。這個體系使得中央王朝既成為政治上的核心,又成為文教上的核心。它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增強了民族之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說,五服制已經成為古代中國最基本的思維定式,深深根植于中國社會。
五、結語
夏代文明是中華早期文明發展的重要階段,展現了歷史連續性和由中原向周圍輻射的延伸性。《禹貢》作為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文化遺產,展現了人文地理觀念和文明中心觀念的經典,對于探索中華早期文明具有極大的價值。《禹貢》的成書,雖然歷時較長,存在后人摻入與潤色,但仍是我們了解中華早期文明某些特征的寶貴資料。
中華文明在覆蓋長江、黃河及遼河流域的范圍內展開,以多元一體的形式形成。中國的文明發展和形成是在廣大空間中經歷了各地區文化的裂變、撞擊和融合,中華文明才孕育出“協和萬邦”的文明基因,產生推動各地區一體化的宏大政治構想。周人通過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負,將“理想的中國”落實為“現實的中國”,創建了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多民族統一的政體,這個政體不斷發展壯大,綿延至今。[5]
從《禹貢》,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早期文明的發生和發展過程。部落聯盟酋長逐漸演變為國王與群巫之長,政治權力與宗教權力合二為一,宗族制度逐漸發展為宗法制度。部落酋長更迭制被王位禪讓制取代,家天下成為新的政治形式。人文地理行政區劃構成了社會結構,貢賦制成為國家政治體系的基本形式。賜土和姓氏分封諸侯建立了官僚制度,構成了王國政治結構。而天人同構和人地同構則構成了中華早期文明的宇宙觀。這些早期文明形態和特征決定性地影響著古代中國文明史的發展道路。
《禹貢》的問世標志著中華先民首次對九州大地進行完整且理性的認知,通過對九州之間山脈河流及其走向、流域等方面詳盡描述,揭示了中華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重要的地理觀念和社會結構。《禹貢》是一部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基礎和中華早期文明特征的作品,展現了中華文明中心觀念的延續與發展,中華文明以多元一體的方式構建起來,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壯大,它孕育了“協和萬邦”的文明基因,并通過政治措施實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愿景。
參考文獻:
[1]張碧波.人文地理學與文明中心觀之始原——讀《尚書·禹貢》[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6.1.
[2]徐新強.“禹貢圖”與中國早期貿易中的水道交通[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1-11(006).
[3]史念海.論《禹貢》的著作年代[J].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3.
[4]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J].考古,1989.4.
[5]李新偉.中華文明的宏大進程孕育多元一體、協和萬邦的文明基因[N].光明日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2020-09-23.
本文為2023年甘肅省社會科學院一般單列項目《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及其時代價值》(項目編號:2023DL03)成果
作者簡介:
謝羽(1980—),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歷史學博士,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絲綢之路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