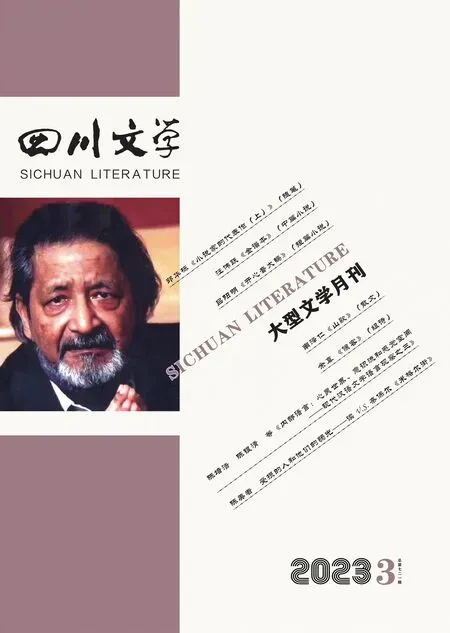關(guān)于小說(shuō)的語(yǔ)言
□文/王威廉
1
我發(fā)現(xiàn)中國(guó)的小說(shuō)家聚在一起談文學(xué),最常談?wù)摰脑掝}是某某作家的語(yǔ)言如何好、某某作家的語(yǔ)言不好。我們?cè)撊绾蝸?lái)理解“語(yǔ)言”,尤其是“小說(shuō)的語(yǔ)言”?我想,在不同的語(yǔ)境中,對(duì)不同的作家來(lái)說(shuō),肯定是大不一樣的。當(dāng)然,大部分人會(huì)從修辭的角度來(lái)理解語(yǔ)言,詞匯的運(yùn)用、句子的節(jié)奏、風(fēng)格的特征等;但這顯然是不夠的,因?yàn)檎Z(yǔ)言是寫(xiě)作的核心,遠(yuǎn)不是修辭所能概括的。讓我們暫且從一個(gè)更大的視野觀之,文學(xué)與語(yǔ)言構(gòu)成了一個(gè)奇特的現(xiàn)象:文學(xué)是由語(yǔ)言構(gòu)成的,可文學(xué)是大于語(yǔ)言的,大于語(yǔ)言的部分越多,則文本的意蘊(yùn)越豐富。那么,文學(xué)究竟是如何大于語(yǔ)言的?文學(xué)理論給了一個(gè)近乎同義反復(fù)的概念:文學(xué)性。但正是這個(gè)有些同義反復(fù)的概念,讓我們得以更加清晰地注意到文學(xué)中的語(yǔ)言。
俄國(guó)形式主義文論的貢獻(xiàn)就在于此:雅各布森認(rèn)為,文學(xué)性就是文學(xué)的性質(zhì)和文學(xué)的趣味,它存在于文學(xué)語(yǔ)言的聯(lián)系和構(gòu)造之中。他還認(rèn)為,文學(xué)性不存在于某一部文學(xué)作品中,而是一種同類文學(xué)作品普遍運(yùn)用的構(gòu)造原則和表現(xiàn)手段。那么,對(duì)小說(shuō)這種文體而言,我們談及它的語(yǔ)言,就是談及它的語(yǔ)言是如何聯(lián)系、構(gòu)造和表現(xiàn)而形成了小說(shuō)。這又涉及對(duì)小說(shuō)文體的理解,何為小說(shuō)?我不想在此下個(gè)定義,但我認(rèn)為,有兩點(diǎn)是小說(shuō)必須具備的,一個(gè)是虛構(gòu)性,一個(gè)是戲劇性。
虛構(gòu)性與所寫(xiě)內(nèi)容是編造的還是有現(xiàn)實(shí)原型的其實(shí)毫無(wú)關(guān)系,虛構(gòu)性是一種“虛擬現(xiàn)實(shí)”的邀約:讀者拿到邀請(qǐng),放下戒備,進(jìn)入文字構(gòu)造的“虛擬現(xiàn)實(shí)”中盡情體驗(yàn)另一種生活經(jīng)驗(yàn)。這就是文體劃分的意義,讀者拿到了標(biāo)明為“小說(shuō)”的作品就立刻確認(rèn)了這種虛構(gòu)性。正是這種虛構(gòu)性的要求,小說(shuō)的語(yǔ)言才必須用更多的技巧去塑造“虛擬現(xiàn)實(shí)”。小說(shuō)的語(yǔ)言修辭是綜合性的,它所涵納的是感官、感受、欲望、情緒、情感、故事、知識(shí)、思想……正是這種綜合性才能構(gòu)造出一個(gè)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相似的“虛擬現(xiàn)實(shí)”。
光有虛構(gòu)性對(duì)小說(shuō)還是不夠的,戲劇性才是小說(shuō)的靈魂。“戲劇性”在很多語(yǔ)境中已經(jīng)含有貶義,那是因?yàn)橛刑嘣愀獾膽騽⌒猿涑庠诖罅看种茷E造的作品中。好的戲劇性不是那種夸張的所謂“狗血”的戲劇性,好的戲劇性是為小說(shuō)的敘事提供一種勢(shì)能。這個(gè)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蘊(yùn)含著能量,敘事的目標(biāo)就是充分釋放事情中的能量,不然為何要無(wú)端地?cái)⒄f(shuō)一件事情呢?不然為何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敘說(shuō)下,效果完全不同呢?好的戲劇性就是能讓一件事情在敘述的過(guò)程中平地起波瀾,通過(guò)符合邏輯(理性或情感)的情節(jié)轉(zhuǎn)折,在話語(yǔ)中積蓄越來(lái)越多的心理勢(shì)能,最終讓事情的能量借助這股勢(shì)能傾瀉而出,沖擊讀者的心靈。
我認(rèn)為考慮小說(shuō)的語(yǔ)言,不能離開(kāi)“虛構(gòu)性”與“戲劇性”。因此,小說(shuō)的語(yǔ)言到底好不好,不在于修辭美不美,而在于是否更好地實(shí)現(xiàn)了小說(shuō)的“虛構(gòu)性”與“戲劇性”。我們深入進(jìn)去,還會(huì)發(fā)現(xiàn)一個(gè)奇妙的悖論:小說(shuō)文體追求的是意義的豐富性,故而在意蘊(yùn)上是模糊的;但小說(shuō)的語(yǔ)言追求的是生動(dòng)性,故而需要準(zhǔn)確。因此,小說(shuō)的語(yǔ)言是在用準(zhǔn)確表達(dá)模糊。在好的小說(shuō)里,越是準(zhǔn)確的語(yǔ)言,往往構(gòu)造了越大的模糊。就像是卡夫卡的《城堡》,K的每個(gè)動(dòng)作都很真實(shí),但K陷入了一個(gè)模糊而又虛幻的世界當(dāng)中。我們看到K的每一個(gè)清晰動(dòng)作,他越用力,他的困境愈深。
2
文學(xué)的語(yǔ)言歸根結(jié)底是個(gè)人化的。賈平凹說(shuō)語(yǔ)言跟作者的呼吸有關(guān),如果一個(gè)人平時(shí)呼吸急促,他可能寫(xiě)的句子就是短小的;如果一個(gè)人呼吸很慢很深,他可能多寫(xiě)長(zhǎng)句子。我不確定是否真是如此,但句子長(zhǎng)短肯定跟作者的思維節(jié)奏有關(guān),取決于作家的生命氣質(zhì)。比如說(shuō),海明威善于寫(xiě)短句,與他的性格肯定有關(guān)。他的硬漢形象,需要刀劈斧砍的短句。
如果是別的文體,比如詩(shī)歌、散文,作者的生命氣質(zhì)肯定是決定性的,比如李白的生命氣質(zhì)與他的詩(shī)已經(jīng)不可分割,張承志的散文也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他的生命氣質(zhì);但對(duì)小說(shuō)而言,小說(shuō)的語(yǔ)言不全然對(duì)應(yīng)于作者自身,敘事人的身份與氣質(zhì)也至關(guān)重要。敘事人是保姆還是商人,是教師還是公務(wù)員,說(shuō)的話顯然是不一樣的。除此之外,這是一個(gè)什么樣的故事,關(guān)于謀殺、情感還是倫理?它處于何種語(yǔ)境當(dāng)中?這些因素都會(huì)影響作家跟筆下語(yǔ)言的關(guān)系。因此,我們必須認(rèn)識(shí)到:好小說(shuō)是大于作家的。
除了敘事人,小說(shuō)還有自身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gè)賭徒、癲癇患者、保皇派、東正教徒,但他在小說(shuō)里面不是一味展示自己的聲音,而是讓他者的聲音也得到充分釋放,甚至他者的聲音有時(shí)更加精彩。他的所謂道德人品在當(dāng)世就被人質(zhì)疑,但并不妨礙他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巴赫金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shuō)結(jié)構(gòu)起了個(gè)名字:“復(fù)調(diào)”。這個(gè)音樂(lè)名詞,形象說(shuō)明了那種多聲部共存的狀態(tài)。所以,與其說(shuō)小說(shuō)是語(yǔ)言的藝術(shù),更不妨說(shuō)小說(shuō)是聲音的藝術(shù)。這種聲音的藝術(shù)不僅讓語(yǔ)言訴諸聽(tīng)覺(jué),還試圖讓語(yǔ)言訴諸精神的視覺(jué)。從聲音的藝術(shù)審視小說(shuō),我覺(jué)得好的小說(shuō)都有復(fù)調(diào)的存在,只是或顯或隱。正是因?yàn)椤皬?fù)調(diào)”的結(jié)構(gòu),作家在小說(shuō)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中并不能成為主宰一切的暴君,恰恰相反,作家的暴力會(huì)迷失在人性的幽微當(dāng)中,在那里,不再有自我與他者的隔閡,小我被消融,或者說(shuō),小我吸納他者變成了大我,而大我又變成了眾生,這才是所謂命運(yùn)的真正涵義。
小說(shuō)還受制于大的文化模式,故不可忽視語(yǔ)言與文化的一致性。用典雅的書(shū)面語(yǔ)去寫(xiě)中國(guó)的鄉(xiāng)土社會(huì),總會(huì)很隔。中國(guó)一直以來(lái)都是鄉(xiāng)土中國(guó),直到2011年起,城鎮(zhèn)人口才開(kāi)始超過(guò)鄉(xiāng)村人口。但這些城鎮(zhèn)人口主要是從鄉(xiāng)村轉(zhuǎn)變而來(lái),故而依然保有鄉(xiāng)土文化的種種特質(zhì)。比如,具有濃郁鄉(xiāng)土氣息的陜西方言獲得了一種文化上的契機(jī)。陜西方言既有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泥土氣息”,又在語(yǔ)法等方面符合現(xiàn)代漢語(yǔ)的“范式”,特別對(duì)應(yīng)于那個(gè)鄉(xiāng)土文化為底座的轉(zhuǎn)型時(shí)代。相較而言,北京話的“泥土氣息”太輕,大量南方方言又遠(yuǎn)離現(xiàn)代漢語(yǔ)的“范式”。陜西的一些作家(路遙、陳忠實(shí)、賈平凹等)為什么能在當(dāng)代中國(guó)文學(xué)中獲得高度共識(shí)?在我看來(lái),除了文學(xué)性之外,這就是文化上的根本原因。但時(shí)過(guò)境遷,城市文化越來(lái)越主導(dǎo)中國(guó)人的生活方式,陜西方言的文學(xué)優(yōu)勢(shì)也許會(huì)不再。近期倒是有一些川味電影、川味小說(shuō)受到歡迎,川味的興起與大西南的閑適生活有關(guān),并凸顯的是一種潑辣鮮活的文化性格,它可以是城市文化的一種類型;而南方方言的興起,則是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之地對(duì)于自身文化肌理的內(nèi)視,在文學(xué)上彰顯的是一種神秘的氣質(zhì),抵御著歷史進(jìn)程的過(guò)度裹挾。但這些方言寫(xiě)作都未能構(gòu)成陜西方言的作品規(guī)模,除了城市文化在審美上更加多元也更加分散之外,依然跟這些方言的局限性有關(guān)。比如說(shuō)粵語(yǔ)寫(xiě)作,經(jīng)常有太多生僻字詞,對(duì)廣東以外的人猶如天書(shū),需要添加大量注釋,但這無(wú)疑會(huì)影響閱讀的快感,也影響傳播的范圍。
如果把文化比喻成一個(gè)有機(jī)體,那么文明的文脈是心臟,主流文化是主動(dòng)脈,而地方文化與亞文化則是毛細(xì)血管。正如毛細(xì)血管構(gòu)成了生命最豐富的那些東西(尤其是感受的能力),地方文化與亞文化也構(gòu)成了人類生活中最豐富多彩的所在。只有從這個(gè)角度去看方言寫(xiě)作,才能獲得它的根本意義。方言寫(xiě)作,是藝術(shù)上的陌生化,是文化上的異質(zhì)性。陌生與異質(zhì),才是一個(gè)作家的獨(dú)特貢獻(xiàn)。
由方言寫(xiě)作可以延伸到口語(yǔ)寫(xiě)作的層面。方言的本質(zhì)其實(shí)就是一種口語(yǔ)。書(shū)面文化對(duì)于口語(yǔ)的態(tài)度一直是輕視的,在中國(guó)古代,士大夫的文言文與民間的白話文差別之大猶如天地。即便現(xiàn)代社會(huì),從小學(xué)到大學(xué)的語(yǔ)文教育也主要是典雅規(guī)整的現(xiàn)代漢語(yǔ),反過(guò)來(lái)可以說(shuō),這種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口語(yǔ)的。但是,小說(shuō)在很大程度上要還原日常生活,所以它必須接納大量的口語(yǔ)。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接納不是隨意的,而是依據(jù)藝術(shù)的感受去小心淘洗,重新打磨和擦亮,讓口語(yǔ)不再是從社會(huì)空間中隨意打撈的話語(yǔ)泡沫。口語(yǔ)必須服從藝術(shù)的結(jié)構(gòu),取得個(gè)人與社會(huì)之間的平衡。因此,好的小說(shuō)寫(xiě)作在某種程度上是要顛覆書(shū)面語(yǔ)言的觀念,讓語(yǔ)言重新接受生活的滋養(yǎng)。
口語(yǔ)早已不能囊括今天的社會(huì)語(yǔ)言。從沒(méi)有一個(gè)時(shí)代像今天這樣大規(guī)模地使用個(gè)性化的語(yǔ)言,網(wǎng)絡(luò)上不時(shí)就有各種奇妙的“詞”被發(fā)明出來(lái),還滲透進(jìn)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比如“沙發(fā)”“不明覺(jué)厲”“yyds”“栓Q”等等,年長(zhǎng)者要詢問(wèn)年輕人才能明白意思。這能否被視為是一種語(yǔ)言的潰爛?在古典審美主義者看來(lái)似乎如此。但問(wèn)題并不簡(jiǎn)單,小說(shuō)家不得不直面這些毫不精致卻活力四射的“亞文化詞語(yǔ)”。好的小說(shuō)語(yǔ)言應(yīng)該像大樹(shù)一般,它的根系必須向下生長(zhǎng),鉆進(jìn)現(xiàn)實(shí)的土壤,每一個(gè)根須上都帶著無(wú)數(shù)小鉤,鉤住泥土、水分乃至垃圾,從而汲取了營(yíng)養(yǎng),獲得讓樹(shù)干粗壯并向上生長(zhǎng)的巨大力量。相較而言,詩(shī)人對(duì)語(yǔ)言有著本體論上的認(rèn)識(shí):詩(shī)人跟語(yǔ)言直接作戰(zhàn),將語(yǔ)言從生活的土地中拽出來(lái)沖洗干凈;但是小說(shuō)家不能這樣做,小說(shuō)家的語(yǔ)言必須帶著土地的泥濘,不憚?dòng)诒┞冻舐睦瑫r(shí)散發(fā)著青草的清香與污泥的爛臭。如果小說(shuō)家將語(yǔ)言清洗得干干凈凈,以詩(shī)的方式來(lái)寫(xiě)小說(shuō)也未嘗不可,但那樣的小說(shuō)是博物館墻上的展示,雖然也不乏寶貴的珍品,但終究無(wú)法讓我們直接體會(huì)時(shí)代的真正痛苦與歡欣。
3
小說(shuō)的語(yǔ)言不是象牙塔,總是及物的,要與它所構(gòu)建的世界息息相關(guān)。閻連科在小說(shuō)《堅(jiān)硬如水》里,將語(yǔ)言及其世界的關(guān)系發(fā)揮到了極致。很多革命話語(yǔ)、時(shí)代流行語(yǔ)、俚語(yǔ)、俗語(yǔ)與主人公的敘事腔調(diào)充分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奔放而奇異的語(yǔ)言風(fēng)格。與讀詩(shī)不同,如果你單看《堅(jiān)硬如水》中的某幾句話,它并不能說(shuō)明任何問(wèn)題,但當(dāng)它們匯總到一起,便構(gòu)成了生機(jī)勃勃的話語(yǔ)洪流。莫言的小說(shuō)也是這樣,某些局部令人覺(jué)得冗長(zhǎng),但從整體上它也構(gòu)成了泥沙俱下的沖擊力,一種蓬勃的生命力在字里行間呼之欲出。假如莫言沒(méi)有那么多冗長(zhǎng)的關(guān)于感官經(jīng)驗(yàn)的文字,他的小說(shuō)就不會(huì)獲得那種生命力。
小說(shuō)的敘述是一種奇特的“連通器”,它驅(qū)使語(yǔ)言不再是靜態(tài)的符號(hào),而是流動(dòng)的所指,席卷人類認(rèn)知的全部事物,這個(gè)過(guò)程跟生命的誕生歷程極為相似。小說(shuō)的語(yǔ)言不在于局部的出奇,而在于整體上的制勝。制勝之力來(lái)自對(duì)能量的積蓄、勢(shì)能的提升以及能量的釋放。這種能量出自小說(shuō)的虛構(gòu)卻并不虛無(wú),它注定要改變讀者對(duì)世界的認(rèn)知與感受。
如果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小說(shuō)家尋找的是符合小說(shuō)氣質(zhì)的語(yǔ)言。我們不能說(shuō)海明威的語(yǔ)言好,福克納的不好,也不能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因?yàn)樗麄兊恼Z(yǔ)言塑造了他們獨(dú)具魅力的文體風(fēng)格,他們的語(yǔ)言與他們的文體風(fēng)格是一致的,因此都是好的。再舉當(dāng)代作家的例子:畢飛宇的小說(shuō)語(yǔ)言精致光滑,肯定是好的,而莫言的小說(shuō)語(yǔ)言雖然粗糙蕪雜,卻也不能說(shuō)不好,因?yàn)槟孕≌f(shuō)中那種磅礴大氣的生命力只能用莫言的那種語(yǔ)言風(fēng)格才能建構(gòu)出來(lái)。
我們知道,語(yǔ)言和言語(yǔ)是不一樣的,大體來(lái)說(shuō),詩(shī)歌的著力點(diǎn)更多地在語(yǔ)言方向,而小說(shuō)的著力點(diǎn)更多地在于言語(yǔ)方向。生活中生機(jī)勃勃的言語(yǔ),是小說(shuō)的重要燃料。小說(shuō)家在言語(yǔ)上的風(fēng)格會(huì)超越不同的語(yǔ)言文字。這方面我愿意舉作家?guī)烨械睦印?kù)切的小說(shuō)原文是用英語(yǔ)寫(xiě)的,但翻譯成漢語(yǔ)之后依然保持著簡(jiǎn)潔和睿智的風(fēng)格。我對(duì)此十分好奇,很想見(jiàn)識(shí)下原文,當(dāng)我讀到原版時(shí),我震驚了,他的英文更加簡(jiǎn)潔,可以清晰看到,他的漢譯本還有翻譯家的潤(rùn)色。他的語(yǔ)言在簡(jiǎn)潔中抵達(dá)了某種復(fù)雜的雋永,跨越了語(yǔ)言的藩籬。我時(shí)常設(shè)想一種在全球化時(shí)代“抗翻譯”寫(xiě)作,就是寫(xiě)作的思想、風(fēng)格與內(nèi)涵不因?yàn)榉g成他國(guó)語(yǔ)言而丟失。美國(guó)詩(shī)人弗羅斯特說(shuō),詩(shī)就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這種說(shuō)法不免偏激。不可否認(rèn),由于文化傳統(tǒng)各異,各國(guó)古典文學(xué)在翻譯層面上不能達(dá)到充分傳輸,但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來(lái)說(shuō),這個(gè)障礙基本上不復(fù)存在,因?yàn)槿祟惒辉偻耆艚^,是在共享同一種大的現(xiàn)代文明。
小說(shuō)的語(yǔ)言讓我們能夠感受到這個(gè)時(shí)代的氣息,又帶領(lǐng)著我們能夠從中超越出來(lái),來(lái)到另外的境地,讓我們知道歷史與時(shí)代絕非鐵板一塊,而是有著更多更好的可能性。但我們也知道,一方面人類文明是一個(gè)整體,而另一方面,我們關(guān)于這個(gè)世界的知識(shí)都已經(jīng)被分門別類,學(xué)科之間等級(jí)森嚴(yán),壁壘分明。我們期待著一種既入乎其內(nèi)又出乎其外的話語(yǔ)生產(chǎn)方式,而這正是小說(shuō)的優(yōu)勢(shì)之所在。在小說(shuō)家的寫(xiě)作中,根本就沒(méi)有這樣的界限,從來(lái)都是把人類的生活當(dāng)成是一個(gè)整體,將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與想象混雜在一起,從而探尋人的處境,呈現(xiàn)人的存在。
敘事作品無(wú)處不在,人們對(duì)小說(shuō)的期待也更高。好的故事、好的語(yǔ)言、好的思想、好的品質(zhì),人們?cè)谝黄≌f(shuō)中貪婪地想要獲得全部;而在以往,如果一篇小說(shuō)獲得其中的一個(gè)品質(zhì)也許就會(huì)得到認(rèn)可,所以好小說(shuō)的難度也可想而知。今天小說(shuō)家的學(xué)歷、知識(shí)背景,都有極大的提高,與這個(gè)時(shí)代的整體知識(shí)狀況也是相匹配的。但今天的小說(shuō)家最缺的是勇氣,小說(shuō)注定要去迎接人類文明大轉(zhuǎn)型的新變。如果說(shuō)20世紀(jì)80年代的中國(guó)先鋒小說(shuō)是對(duì)僵化話語(yǔ)的一種反抗,那么今天的情況更加復(fù)雜:不但要反抗僵化,還要聚攏渙散。
卓越的人文思想者喬治·斯坦納對(duì)于語(yǔ)言懷著忠實(shí)的信念,但他很早就意識(shí)到了語(yǔ)言的危機(jī)。他指出,語(yǔ)言曾經(jīng)構(gòu)成了人類經(jīng)驗(yàn)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那是一個(gè)輝煌的語(yǔ)言時(shí)代,不過(guò),那種狀況早已被打破了。當(dāng)年,他看到的是唱片的暢銷,而今天,科技支撐的是堪稱奇觀的視聽(tīng)文化,在此基礎(chǔ)上,一個(gè)無(wú)限擬真的虛擬現(xiàn)實(shí)正在文化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元宇宙”只是對(duì)那種文化的一種稱謂罷了。未來(lái)的可能性要遠(yuǎn)遠(yuǎn)大于所謂的“元宇宙”。因此,正是對(duì)未來(lái)濃霧的眺望,反而讓我對(duì)斯坦納的這段話念念不忘:“語(yǔ)言是人獨(dú)特的技藝;只有依靠語(yǔ)言,人的身份和歷史地位才尤其顯明。正是語(yǔ)言,將人從決定性的符號(hào)、從不可言說(shuō)之物、從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來(lái)。如果沉默將再次蒞臨一個(gè)遭到毀滅的文明,它將是雙重意義的沉默,大聲而絕望的沉默,帶著詞語(yǔ)的記憶。”小說(shuō)是人能用語(yǔ)言創(chuàng)造的最復(fù)雜的藝術(shù)品,因此,小說(shuō)的語(yǔ)言是沉默中忽然爆發(fā)的漫長(zhǎng)傾訴,它出自個(gè)人的肺腑,卻說(shuō)出了時(shí)代的整體狀況。
但這樣說(shuō)并不意味著小說(shuō)要被某種道德觀給綁架,小說(shuō)就是小說(shuō),好的小說(shuō)自然而然地會(huì)獲得那些我們期待的品質(zhì)。我們?cè)趯?xiě)作的時(shí)候只需要記得:好的小說(shuō)語(yǔ)言應(yīng)該具備一種生命內(nèi)在的訴求,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張力,一種細(xì)膩體貼的人文關(guān)懷,一種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一種令人重新審視世界的哲思,它們匯聚在一起,將眾生喧嘩變成人類存在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