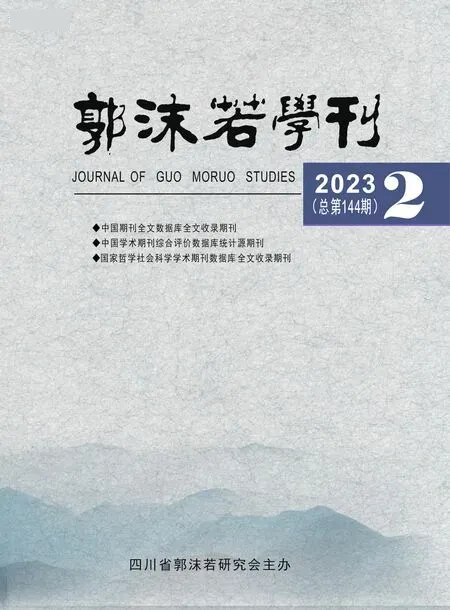大文學觀視野下郭沫若文人書法的當代觀照
李青剛 張劍強
(1.四川天府新區書法家協會,四川 成都 610213;2.西安外事學院 教務處,陜西 西安 710077)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①《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11 頁。大文學觀視野下,中國形象必須以中國文化精神和人文內涵為根基。放在書法上講,就是創作中飽含靈氣、性情、精神和才識等人文氣質,突出藝術格調和精神學養。這是中國書法自文字產生以來,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得以永續傳承的重要原因。
自古文藝不分家。清人劉熙載在《游藝約言》中說:字不出“雕”“樸”兩種。循其本,則人雕者字雕,人樸者字樸②楊寶林:《劉熙載書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由此可見,中國書法自古講究人文精神和藝術情感,所謂“人書其字,字如其人”。當代書法在取得繁榮進步的同時,出現了“技長藝短、逐末棄本、形美質空”等創作困境,展廳時代甚至出現了書法“唯技論”。救弊之道,應提倡和重視書法創作中對文字、文學、文化、文人的學習探索,以藥不學無文之病。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陳獨秀、魯迅、胡適、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巨匠,在書法上都有成就,他們的作品,構成了20 世紀中國書法的另一道風景——文人書法。郭沫若先生,就是風景之鏈中最閃耀的一環。多年來,關于郭沫若書法的研究,多數都是被其“文化偉人”的身份所掩蓋,加上部分人脫離時代背景對其書法藝術妄加評論甚至謬斷,未能全面地將其書法創作的文化精髓和豐厚遺產進行傳承和學習。大文學觀視角下,對照當代書法競技創作中人文缺失的“唯技”危機,以文人書法為鏡對郭沫若書法藝術進行研究,秉承客觀中立、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藝術評價,讓書法藝術回歸人文經典,實現書法藝術的文質兼美和守正創新,推動新時代書法藝術創作大繁榮。
一、郭沫若“書法家”身份及其書法藝術的時代爭議
近年來,關于郭沫若及其書法藝術的爭議不斷。說郭沫若是文化巨匠,沒有人敢說不;說郭沫若是文字學者,也毋庸置疑;但說郭沫若是書法家,有些人不認同,甚至以不屑的態度否定其書法成就和貢獻,歸根結底是對文人書法的不認同,是對書法的人文內涵的弱化和摒棄。今天的書法藝術面臨著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與古典情結的現代審美轉型,書法家與傳統文化斷裂,庸俗、鄙陋、粗野、媚態的“丑書”層出不窮,直接導致了書法缺乏人文精神,“韻、趣、情、雅”的文人書法在人文精神的日趨低落中竟為某些人所不齒,反而是把書法創作當成了個人裝點門面的名利場,這是書法的不幸①參見歐陽中石:《書法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郭沫若是不是書法家,歷史已經給出了評判。對于這樣一位名留青史、家喻戶曉的“全才”,為什么一些史料文獻介紹郭沫若,并未明確其“書法家”身份呢?為什么會有人不認同他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呢?為什么會否定以郭沫若為代表的當代文人書法呢?
(一)文韜才略多面成就卓著,郭沫若一生不以“書法家”為名。縱觀20 世紀中國的文化版圖,舉世矚目的文化學者不勝枚舉,但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魯迅思深,沫若才高,鐘書學富”②李青剛:《萬端“文”氣皆修養》,《現代藝術》2019 年第10 期。。郭沫若一生,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學、戲劇、翻譯、書法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是20 世紀中國文化史上難得一見的“球形天才”,他的崇高學術地位是由他在學術界的突出貢獻決定的。到目前為止,全國的高校、科研院所、知名樓堂館所、教材等名字很多都是郭沫若先生題名,可見一斑。周揚曾經說過:“郭沫若同志在學術文化方面的建樹是多方面的,他是中國的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③吳敏,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傳記文學》2019 年第7 期。著名學者、詩人北塔認為,以郭老的才華,如果他專攻一門,入選諾貝爾獎綽綽有余;當然,以他的經天緯地之才,他恐怕不屑于被某一個專門領域所拘牽④史忠平:《郭沫若的書學貢獻與書法藝術》,《中國書法》2011 年第1 期。。郭沫若的一生,首先是一個革命者,是文學家,然后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者等。書法于他一生,好像未甚經意,但又始終不離不棄,故學界對郭老多有“因文掩書”的評價。因為沒有把書法當事業,是無意當書家而成了大家。追溯歷史,盡管有深度的研究他與書法的文字較少,但就書法學科而言,放置于現當代中國書法史的歷史舞臺來看,郭沫若是20 世紀中國書法不能回避的重要人物。郭沫若平生雖未以“書法家”自居,但這毫不影響其是一位名留丹青史冊的書法家。
(二)以今知觀往史,籠統地將郭沫若其人其書置身時代漩渦。郭沫若對中國古文字的研究、碑帖的考證和書法創作等方面創造的成就被國內外書法界共知。其書作以“回鋒轉向,逆入平出”為學書執筆八字要訣⑤桑逢康:《郭沫若的文化價值取向》,《郭沫若學刊》2020 年第2 期。。書體既重師承,又多創新,展現了大膽的創造精神和鮮活的時代特色,其書法成就有目共睹。評價這樣一位文化學者,不能籠統地將彼時的時代背景、政治環境、個人情感等割裂和脫離,用此時此刻的眼光揶揄彼時彼刻的時代境況,將與書法無關的東西變成其書法藝術的標簽,這不符合藝術的客觀評論規律,也無疑是對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文人書法家的不公平待遇。藝術批評應該堅持“知人論世”的原則,以負責任的態度來對他和他的書法作品進行研究,著重揭示藝術評價的本質和主流。如果故意混淆顛倒,甚至不惜污蔑和謾罵,那就背離了評價歷史人物和藝術作品應有的原則和方法,這同無限拔高或貶低一個歷史人物的做法一樣,都是不可取的。
(三)美術化誤讀誤解郭沫若書法藝術,把書法與文化、藝術對立。近年關于“書法不是藝術”的討論,折射出眾多“書匠”在書法創作和理解過程中的“無知無畏”。郭沫若作為文化巨匠,從他一生的書法創作中可以看出,他的書法創作涵蓋了博大精深的人文文化,是史學、哲學、文學、美學的結合體,凝聚著書者的修養、才力、個性、技能和情思的積淀,也是天賦和智慧的自然融入。把個性和思想外化入書的形式,既有當代形態意象和“現代感”的風格,又有超越古人前賢書法的創新意識,提高人的文化素養,陶冶情操、凈化心靈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①譚仲池:《書法天地應深蘊人文情懷》,《中國藝術報》2014 年12 月3 日,第5 版。。由此創作出的書法作品,促進了同時期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郭老的書法作品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處處可見的郭體書法牌匾和題字,充分證明其書法作品是一種人文自信意識的反饋。但近年來有部分學者將郭沫若書法與西方藝術作品及藝術現象比較并進行美術化解構,認為郭老書法不夠現代、缺乏意象,僅僅是“名人書法”,這樣的觀點往往能在網絡上調動非專業書法人士的“碰瓷式”評論。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下,許多人將書法與文化、藝術對立,美術化誤讀書法的內涵標準及人文傳承,缺乏對書法基本的書史學理認知和審美參悟,將書法等同于西方的油畫、雕塑、裝飾藝術等具像實物進行美學品評,這是不了解中國書法本源和中國傳統文化,妄自菲薄、自娛自樂的沖動,而非基于藝術本體的創新認知和表達。
(四)展覽競技下重技而輕道,對文人及文人書法的時代認同低。從郭沫若的書法作品和相關論著可以看出,他主張書法回歸傳統,推陳出新,實現內容與形式互為一體。他強調文人應習書法,書家也應同擅文章。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文人書法,就是在此基礎上,以凸現文人個性文化、注重趣味和書卷氣的書法形式。文人書法的興起,表明文人對于古典美學的繼承。歷史上凡被稱作書法家的人,遠如王羲之、顏真卿、蘇軾,近如郭沫若、趙樸初、啟功等,在書法造詣有所成就之前或者同時,一定是文人,或者說是有相當文化修養的人。書法家不能專注追求“技”而忘了“道”,推崇書法技術,忽略文人情懷。在書法競技的展覽時代,文人少被提及,文人精神被邊緣化,文人書法自然也就只剩下“表現”而非“表達”。甚至人為地割裂書法生態,書法家變成一個個“文字的搬運工”或者“碼字先生”。從近年來舉辦的全國性書法展覽來看,很多作者臨帖、章法、形式等都無可挑剔,但一個展覽下來,自作詩詞的作者少之又少,即便是抄送古今詩詞,也是斷章少義、人為錯漏。有些作者連續多年、多次書寫同一內容和形式作品投稿,單幅作品接近完美,但多是為“展”而“戰”,缺乏人文意識和思想精神的表達。近年來國家對傳統文化高度重視,已經上升到國家文化戰略的高度,書法家應該以郭沫若等前輩文人為鏡,提升自己書法創作中的文化底蘊和人文情感。
二、郭沫若文人書法的人文價值及當代觀照
(一)追本溯源,取法傳統經典。書法是以漢字書寫這一特有的表現方式,以情感意象為內容的表現藝術。它以線條為手段,講究形體結構和造型,而非具體的對自然物象的塑造。學習書法,必須“入門有法,取法有徑”。這里的“法”和“徑”就是幾千年來中國流傳下來被認可并傳承的經典碑帖。郭沫若在書法藝術上的探索與實踐歷時70 余年,硯邊垂墨,筆耕不輟。其平生書法學習可分為早年的臨摹模仿期、日本求學書體發展變化期,歸國后風格定型成熟期。青年時期郭沫若師法王羲之、顏真卿和蘇軾,線條樸茂,結構寬博;在日本時期他潛心研究金文、甲骨,將早期造型符號融入結構用筆中,字里行間流露金石趣味;歸國后他的書風漸趨成熟,融入個人的藝術學養,形成其典型的“郭體”。郭老一生的書法實踐,都緊扣傳統,追本溯源,堪稱回歸傳統的典范。而觀當下書法創作生態,凡大成就者,皆以郭老及書法先賢為楷模,日臨不輟,虛心向古人碑帖求教請問。但還有大量的“江湖書法家”,以“我體”“無體”“老干部體”作為創作動力,月書萬卷,未見進步,此類江湖習氣不應該成為書壇導向。從這點上講,郭老的創作成長經歷,值得當下學書之人深刻體味、秉承踐行。
(二)融古化今,守本與創新并舉。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王岳川教授總結出“文化書法”的理念: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②王岳川,龔鵬程:《文化書法與文人書法——關于當代書法癥候的生態文化對話》,《中國書畫》2014 年第3 期。。這是對書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跨時空的精辟總結。郭老書作以行草見長,筆力爽勁灑脫,運轉變通,韻味無窮;其楷書作品雖然留存不多,卻尤見功力,氣貫筆端,形神兼備,這是源于他深厚的學術涵養和古文字的堅實底蘊,從書法的原創期就得以探幽發微,融古化今。他的書法作品弱化了北碑的奇突之勢,強化了南帖的豪放之氣,化古人之法為己法。他的書法創作生涯,將抒發人文情感放在第一位,但也不忽略形式的多樣化,這也是文人書法最大的特征。《蜀印錦書:二十世紀四川成都書法篆刻事略》文中評價:郭沫若的書法是建立在扎實的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是近現代甲骨文字研究的“甲骨四堂”之一)基礎之上,以其跌宕豪邁流布四方。郭沫若的書法從宋四家出來,無論用筆、結體都有宋四家意味,但又個性突出,為世所重。其書體既重師承,又多創新,展現了大膽的創造精神和鮮活的時代特色①向黃:《蜀印錦書:二十世紀四川成都書法篆刻事略》,《文藝生活》2014 年第12 期。。這是對郭沫若書法創作及學藝過程的精準評價。
(三)詩文做基,倡導人文書法氣質。“明代草書第一人”祝允明曾言,寫字時“情腸百結,順管奔流”,遂致奇崛縱橫,神鬼莫測②馬治權:《中國書法之謎》,《光明日報》2015 年4 月24 日,第13 版。。黑格爾也曾說,一個藝術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現出心情和靈魂深度③呂文明:《文人書法和現代書法的人文精神》,《書法導報》2014 年7 月16 日,第5 版。。書法家要淋漓盡致地表達感情,創作神妙之作,必須借助厚重的文化底蘊,使豐富情感見于翰墨之表。郭沫若七十歲時曾以行草書寫過一幅扇面:“有筆在手,有話在口,以手寫口,龍蛇亂走。心無漢唐,目無鐘王,老當益壯,興到如狂④李繼凱:《論郭沫若與中國書法文化》,《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3 年第2 期。。”由此可見郭沫若的精神世界里具有一種超常的詩人氣質,這種詩人氣質主要體現在對生命情感認知的兩種存在形態:一是感情激蕩時的亢奮與宏放,二是感情低落時的憂郁與感傷,兩者相互依存,互為衍化,互為迭宕。其內在精神則是張揚個性,表現自我,追求自由與超越。而這一切都與博覽多重文化相激相匯的大勢相聯系,顯示出耐人尋味的歷史文化意蘊。以文載道,直抒胸臆,詩書并舉,讓“文人書法”與“人文書法”相得益彰,提升到新的藝術鑒賞高度。近年來書壇大力鼓勵自作詩詞的書法作品,這必將引領新的人文書法創作趨向,值得推廣。
(四)碑帖博通,成就文人書法大家。商周尚象,秦漢尚勢,晉代尚韻,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代尚意,元明尚態,清人尚質,中國書法發展的一條主線都在圍繞文化的精髓和內質進行⑤馮繼紅:《中國各代書法風格所內蘊的文化精神》,《大眾文藝》2011 年第16 期。。只有涉獵不同時期的書家精髓,內化外現,方能成就經緯書才。郭沫若在旅居日本的十年中,幾乎涉及了所有的書體,不僅從文字發展的角度進行研究,而且從書法實踐的角度進行探索。甲骨文線條流暢,錯落多姿,疏密相間,自然天成;金文極富裝飾性,形象性超過了甲骨文;石鼓文擺脫了文字的裝飾因素,又超越了實用書寫的意義,具有筆法書寫的審美效果。此段時間里,郭沫若對晉、唐書法的追溯,為帖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相當一部分書作,具有完整晉人書風的楷書;有對二王書法的心領神會,無意中透露出先賢天趣妙境的行書;有受孫過庭《書譜》影響、東坡神韻浸染、王鐸醒世駭俗墨跡開啟的行草書。當我們熟悉了郭沫若書法實踐的過程,我們就會嘆服其書法藝術之人文魅力和文人情懷所在。正是因為他具有堅實的碑學和帖學基礎,才使他創立了別具風格的“郭體”。
三、大文學觀視野下當代書法創作的人文通徑
歷史傳世書法作品靠的是什么?我們臨帖摹碑向古人書法學習什么?這是每一個書法學習者需要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中國文化的記錄符號是漢字,而表達漢字的手段是書法。書法藝術發展至今,已經不是簡單的文字記錄,而是以文字為載體、表達書寫人(創作人)情緒情感、思考態度的富有美感和內涵思想的藝術作品,故被譽為無言的詩、無形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郭沫若一生的書法創作實踐,正是這種文人書法的典范,大文學觀視野下,以郭沫若文人書法為鏡,反思當下書法創作中“文”與“藝”如何并聯融通,實現“技道兩進、文質兼美”的審美尋繹?值得書界同仁深刻反思。
(一)崇尚“真善美”的藝術審美與創作標準。書法藝術滲透著儒家文化的“身心兼修”“格物致知”精神,也滲透著道家文化的“自然而然”“天人合一”的精神,書法創作自古要求必須具備“真善美”的藝術標準,不斷提升“修身修心”的藝術境界。古人十分看重“作字先做人”,有的字因人貴,有的字因人輕。當代書家忽視品德修養的提高,認為“做人”即做官、出名,只要有位子,有名氣,就一字千金。于是宣傳、包裝、游說等書壇怪相百出,這不僅擾亂了文化市場的正常秩序,分不清是與非、美與丑、善與惡,出現了創作中的“丑書”“怪書”“江湖體”“符號體”等,誤導了一大批“涉書未深”的書法愛好者,甚至讓孩童學習書法的心態都隨著家長的急功近利而浮躁。文人書法作為“修身”與“修心”緊密結合的自我豐富手段,得到了郭沫若等前輩書法大家的繼承和弘揚。“順其自然”不僅表現在書法創作的本身,還應表現在書法家對人生狀態與價值理想的追求上。
(二)強調字內與字外的文人書法美學追求。書法是造型藝術,也是人文藝術。書法作為一門歷史悠久的藝術,在幾千年的發展變化中,處處彰顯著“人”的個性與品格,也時不時地暴露出與“人”相悖的致命弱點。當前不少書家(包括小有成就的書家)以一成不變的方法去應付自己的創作,又想快速極力表達自己的所謂“個性”。這些作品表面上看或老辣或新奇,但經不起美學推敲,更談不上美學情趣與人文價值。他們將“字如其人”表面化、膚淺化,認為“如其人”即“如其表”,未能真正理解到“如其才”“如其志”這一人文美學高度。當代書法創作中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文美學意識,在展廳下的競技書法創作中,被逐步忽略,取而代之的是為評委、為名利的“無我”創作。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文人書法,是在以人為本、人藝共修的基礎上得到的藝術升華,這是當代書法家需要傳承和思考的重要命題。
(三)重視古今書論與人文學科的貫通學習。古今書論既是對古人書法創作的總結,也是對今人書法創作的指導。縱觀當前書法生態,不少人提筆就寫字,卻對于書法理論嗤之以鼻,不愿意坐市場經濟下書法理論研究的“冷板凳”,專業的書法展覽也缺少理論研討安排,以郭沫若為代表的老一輩文人書法家,用自己終生的創作經驗告訴我們:一件成功的書法作品,除了老辣沉雄的字內功夫給人以美的感受外,書寫者通過作品反映出的人文學識也是感染讀者的重要因素。當代書家必須將古今書論與哲學、文學、史學、美學貫通學習,以補書法創作“人文缺鈣”之憾。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張海先生曾提出,新時期書法創作必須充分重視書法理論的作用,主動吸收強化文學功底,加深對前輩文人的文化思潮、文學流派、文藝現象作深人的研究。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結合,必將為書法創作者創造胸有成竹、下筆有神的藝術靈感。
(四)倡導“百家爭鳴”的常態化藝術批評。普希金說:“批評是揭示文學藝術作品的美和缺點的科學。它是以充分理解藝術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規則,深刻研究典范的作品和積極觀察當代突出的現象為基礎的①梁繼:《書法批評的五個維度》,《藝術廣角》2011 年第5 期。。”縱觀當前書壇的書法批評,多套用一套形式:少年聰明好學,成年遍臨碑帖,依古變法,終成大器。這種表揚式評論的程式化,即使書作中的毛病很多,也大言不慚認為是瑕不掩瑜,將“人性化”的書法批評“人情化”,一談書評就是表揚與自我表揚,把文藝批評看成了討好書家的工具。文藝批評的過程,實際上是批評家在把握文藝創作規律的基礎上,應該開展百家爭鳴式的文藝批評(評論),這就要求對作者創作的優點和不足進行梳理歸納,對作者未來的創作提出客觀建議。書法創作者要把批評當做自己提高水平的一種手段,以一個文化人對藝術的高度責任感來對待書法批評,真正確立“百家爭鳴”藝術評論的常態合理地位。
四、結語
郭沫若先生作為當代中國文人的杰出代表,是文人書法的時代標桿。他的書法作品處處透射出一種“文”的氣息,集萬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種思緒,從筆端涓涓流出,化為與其學問修養相融合的境界,以書法藝術形式展現給后人。他的書法藝術獲得了堅實的學術根基和人文素養,其學者風范與書家風度的完美結合,構成了郭沫若書法藝術的鮮明特色。堅定文化自信的新時代,大文學觀視角下,需要我們持續創新地研究郭沫若及其書法藝術,讓文人書法得到更多認可和重視,同時也引導更多書法創作者沉下心來,走進書房案頭,閱書寫詩,臨帖摹碑,夯實人文基礎,構建人文環境,踐行審美規律,實現書法創作從高原到高峰的時代跨越,創作出代表中國文化、中國力量、中國精神的時代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