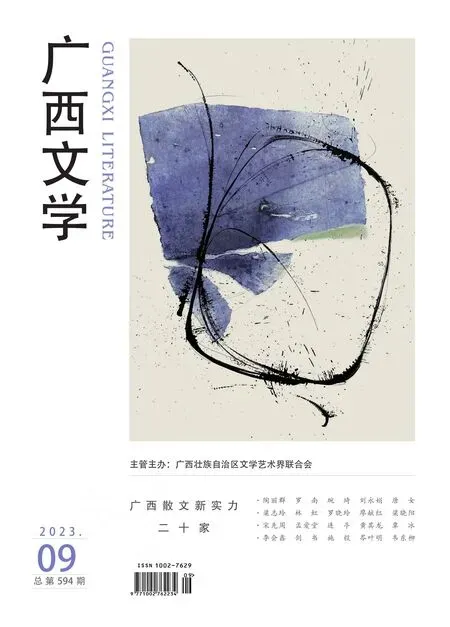一個人熱鬧
岑葉明
一
十多年前,村里修水泥路,每家每戶都要按人頭出錢,錢多可以捐。捐得最多的是從村子里走出去的大老板,十幾萬,當時的我覺得天上的星星都沒這么多。有了大老板的天文數字,水泥路修完,還剩錢,大家便提議立個功德碑。
功德碑建在村口的空地上,刻上捐贈者的名字,從大老板開始,按照數目大小往后排列。立了碑還有錢,又在碑后建了面墻,頂上加檐,用來遮風擋雨。我家人的名字沒出現在上面,與玩伴們去到那里,總成為被笑話的那一個,說我爸肯定把錢賭光了,再說我媽因為我爸太窮跟別的男人跑了,最后說我不捐錢所以不能走路。好在我的嘴巴也夠毒,說這塊碑像墓碑,祝賀你或者你爸你媽被刻了上去,明年清明節記得來燒香放炮,不然他們就成孤魂野鬼啦。
沒過幾年,功德碑旁建了個垃圾池,其他空地被人用來曬稻草,有時用來曬牛糞,不知道大老板作何感想。不過大老板很少回來,關于他的事我們所知甚少,除了很有錢。有時捐錢不到位,大家背地說他小氣,傳到他那里,他索性不捐了,便有人罵他,在言語和氣勢上排擠他,即便他曾對村子里要錢的大小事有求必應。我天真地以為自己能和他感同身受,因為父母離異、家庭貧窮,我也是被排擠的對象,區別在于他能離開村子,而我的遠離只存在于幻想中。
我性格頑劣,喜歡熱鬧,也不排斥獨處。前者源于天性,喜歡獨處則是不想回家。父親與母親離婚后性情大變,常常無故瘋癲,罵人,砸東西,我將那棟矮小陰暗的瓦房視為地獄。我不想待在里面,便獨自在外面晃悠。我自幼便深知農村婦女們議論某個人偷雞摸狗的時候,并不一定是源于誰家確實丟失了什么,而是被議論的那人有機會讓別人丟失什么。就像常年在外工作的母親,不是她確實做過什么,而是她有機會做什么,閑言碎語在這些模糊的暗示里最具有生命力。為了不成為她們的目標,我選擇往人稀少的地方走,鬼怪對我而言不比她們可怕多少。夜晚的村子幽靜、安詳,房屋里的光偶爾逃逸,大多地方幽暗。我帶著手電筒卻不打開,借著月光引路,去尋找能一起出來玩耍的人。大人們覺得小孩夜晚出去必做壞事,實際上我們也做過不少,因此在夜幕下呼朋喚友不能明目張膽,而是學著什么叫,有時學狗,有時學牛,有時學雞鴨,有時發出的聲音四不像。有時喚得出玩伴,有時喚得他們父母的叫罵。
大多時候玩伴們回家了,我還不想回,便沿著村路走到村口,爬上功德碑,躺在上面發呆。那時沒什么書看,眼睛好,能數清天上的星星。我比較它們的明暗,遙想那里居住的外星人長著什么模樣,和地球的戰爭什么時候才結束。偶爾有飛機閃爍出紅光綠點,我的視線跟著它們從天的這邊到天的那邊,反反復復。
有時我只是望著星星,心思卻不在星星上,而是想到跟隨母親離開的姐姐,她在過什么樣的生活,什么時候才能回來。父親總是在吃飯時咒罵母親,有時蓄謀著罵,有時毫無征兆地罵,我要一起表現出憎恨的模樣才能避免被一起罵。在那些獨自仰望星空的夜晚,我偶爾也會偷偷想念母親,即便記憶中跟她相處的時日屈指可數。
千百個夜晚里,我只見過一次流星,或許它們多次出現,我都錯過了。我趕忙對流星許愿,希望以后能過不一樣的生活。我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覺得只要跟眼前不一樣就好。
我厭倦村子,厭倦家庭,厭倦各種恩恩怨怨,自覺人不應該只為這些事而活。
二
聽父親說我出生沒多久就被母親帶去樂業,兩歲后回來,印象里只有些模糊的記憶。兒時的清晰記憶都離不開那個叫大橋頭的村子,輻射出最遙遠的地方是三公里外的橫嶺圩。我喜歡熱鬧,卻不總是能靠近熱鬧,父親常警告我不要往熱鬧的地方擠,因為事故和意外也喜歡循著熱鬧而去。
父親總想著付出一點心思就有很多回報,我剛學會拿筷子,他就要求我學寫字。我短時間難學會太多,他也不想太費力教,又想要我練好,便讓我反復抄寫自己的名字。在反反復復中我聽到老房子外飄蕩著充滿誘惑的歡笑聲、蟬鳴聲、狗叫聲,感到厭煩,感到厭惡,字越寫越歪。父親便大發雷霆,強迫我寫更多。我自知逃不出眼前這張紙,便在上面展開想象:每個方格都可以看成一個獨特的世界,或從自己的名字延伸出歪歪扭扭的線條作為迷宮的路線,周邊空白的區域則可以畫出具體的圖像……完事后的紙張一片狼藉,像等待打掃的戰場,有時能撕開重抄一張,有時挨一頓罵。父親沒能如愿,我練了很多字也不能寫好,反而越來越害怕寫字,持續至今,用筆寫字像被螞蟻咬一樣難受,恨不得把筆折斷。
日子空曠漫長,百無聊賴,能在很多細微的事物里生出紛繁的靈感。奶奶大病一場后,生活無法自理,父親離不開村子,打不了工,賭癮難戒,生活陷入困境。我家有些田地,又種些別人的,如果父親不把收成放上賭桌,勉強能糊口。周邊的樓房陸續崛起,我家還住著瓦房,曬稻谷時只能借別人家的樓頂。
天氣悶熱,稻谷、玉米、花生都怕雨,淋一下得發芽,發了芽做不成糧食。父親不讓我下地干活,只讓我看天。這個任務不復雜,需要隨時注意四周天空的動靜,有云也不能慌,可能是嚇人的碎云,得等到云層顯露更多,要是滿天烏云就得馬上收,小碎云就隨它過去。有種云最具迷惑性,是碎云,但又厚重,能帶來“云吊雨”,且軌跡不定,有時直直走,有時拐彎走,有時谷物收了大半繞走了,有時不想收又被淋了,十分令人頭疼。好在大多時候晴空萬里,無害的白云飄來蕩去,我忍著刺眼的日光,嘗試和它們說話,問它們從哪里來又要去往哪里,也跟他們說我的煩心事,說我對各種人和事的理解和看法,說我對未來的愿景。想象是慰藉無聊的解藥,我總是與它們嘰嘰喳喳,十分有趣,別人不得而知。
十二歲那年,我的頑劣達到峰值,和許多人在國慶假期翻墻進學校,燒廚房,往鍋里拉屎撒尿,撬開辦公室,拋撒試卷,還想著要把學校炸掉。過后不知經過了復雜的籌謀還是自發的共識,總是被孤立的我成了替罪羊,老師不是不懷疑一個人怎么能造出那么大的破壞,可能也只想找一個替罪羊,或者出氣筒。老師把我關進廚房毆打,強迫我跪在教室后面聽了幾天的課,再罰我沖廁所掃地一個學期。老師深知最殘酷的懲罰是孤立,他不允許其他人對我表現親近,更別說幫助。當然,也沒有人想要幫助我,他們大多幸災樂禍,在我掃過的地方丟碎紙屑,憋著屎在我沖過廁所后才拉出來,以此為生活的大樂趣。
我為此頹廢過一段時間,像條掉進糞坑沒人打撈的土野狗。為了應對逐漸絕望的生活,在放學后空蕩的教室里、廁所里,在回家路上看日落的黃昏,在許多無人的情景里,我構思出那些并不存在的玩伴,與他們交談、玩樂。他們性格各異,善良或兇惡,膽大或怯弱,忠實地陪伴我熬過了許多漫漫長夜。
三
終于可以離開村子讀初中了,別人能去到學校再買新的生活用品,我要從家里帶去,舊的水桶、舊的碗筷、舊的蚊帳、舊的被子……都是舊的,只有心情是新鮮的。從橫嶺圩坐大巴,大巴也是新奇的,我目不轉睛望著窗外,途中路過房屋散落的村莊,一塊塊玉米地、水稻田、樹林,和我成長的村子沒有什么不同,卻又完全不同。盡管只有十多公里,但對我而言也是一次遠行。
學校位于城鄉接合部,離市區四五公里,出了校門就是國道。國道好直好寬,我從未見過這么寬的路,路邊的房子也有五六層高,比村子里整齊多了。周末跟同學們去市區玩,第一次進城,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車,又羞于問詢,便磨磨蹭蹭排后面,看別人怎么投錢,怎么找座位坐,怎么告訴司機要下車。其他的學一次就會,讓座不太好學,有時沒在最恰當的時候起身,有時候別人先讓了。第一次讓座成功難免激動,臉頰發燙,覺得周邊的人都在崇拜地看著自己,接著腦補一場又一場做好事不留名的大戲,直到為了拯救世界獻出年輕的生命。
我在許多時候付出過自己的生命。比如學校進行升旗集會時,大家都在認真聆聽領導的教誨,而我的世界中,惡魔正在進攻這里。惡魔可以是哥斯拉,可以是三頭龍,可以是泰坦,但體型必須碩大,脾氣必須暴烈,必須所有人都看得見,所有人都驚恐、絕望,期盼救世主的出現。氛圍鋪墊得恰到好處時,我猛然抬頭,周身散發金色光芒,如離弦的箭矢從地面射起,穿透惡魔布滿鱗片的喉嚨,撕裂惡魔強壯的身體。當然,有時候不會那么順利,惡魔十分強大時,我會無數次被擊落,在地面砸出深坑。周圍的人尖叫、哭泣,這種時候心儀的女孩子一定要看見我,并且鼓勵我,不然哪怕我毫發無損也不會重新振奮。在激烈的戰斗中,心儀的女孩總會成為轉折工具,她們流下愛的淚水、發出信任的鼓勵,或者她們面臨危險絕望時,身負重傷的我發出怒吼,軀體里的力量呈指數爆發,壯觀程度絲毫不弱于超新星爆發,甚至只需眨一下眼皮,惡魔便被轟得灰飛煙滅。
年輕時的幻想和女孩們分不開。我從閉塞的農村走出,對愛情的渴望源于青春期本能的沖動和對電影書本的效仿。大家都有暗戀的對象,我也暗戀著,憧憬與她海誓山盟、白頭偕老。愛情的幻想對象有時是具體的某個姑娘,與她在爛漫的櫻花樹下相遇,眼神對視的那一刻便互生情愫,在諸多巧合后相識相知相愛,經過一些誤會和挫折,最后都能牽手、親吻。
在最初的幻想里,親吻是青春最僭越的行為,仿佛親了嘴就能圓滿大結局,過上幸福的生活。往后看了些少兒不宜的東西,也隨著年齡增長,生理的欲望加大,幻想的對象變得廣泛起來,幻想的尺度也隨之加大,有了許多不可言說的沖動、猥瑣與變態。然而在現實中,我和女孩們的愛情總不會很順利,有時暗戀某個女孩,幻想了無數的恩怨糾葛,自始至終卻未說過一句話。
進入青春期后,我變得外向、開朗、搞怪,能給身邊人帶來快樂。可我明白自己骨子里是自卑的,源于肉眼可見的矮個子,源于恥于承認的囊中羞澀,也和童年的遭遇分不開。我害怕再次被孤立,刻意隱瞞過去,想要更多人的關心。我變得心口不一,有時心里覺得是這樣,說出來又是那樣,審時度勢,見風使舵,提前戴上成年人才有的面具。只有獨處的時候,才能讓身心徹底放松,找到一種回歸自我的輕松與舒適。
我由此覺得獨處并不可怕,慢慢挖掘其中的樂趣。
我逐漸著迷于乘坐交通工具,這是一種非常安全的獨處,周邊嘈雜的都是陌生人,景象不斷變化,無人能打擾。我最喜歡坐在后排位置看窗外,情緒醞釀足夠,眼前變化的景象還可以有另一種意味:時光倒流。這樣的場域構建出完美的回憶之屋,盡管我明白深陷其中不利于放下過往,卻生不出丁點逃避的念頭。
中學時比較拮據,只能坐公交車,一塊兩塊,可以繞著城市兜兜轉轉。我對外面的一切充滿好奇,像個錯過功課的好學生狠狠補習。我縮在公交車角落觀察這個世界,觀察道路兩邊應接不暇的鋪面、琳瑯滿目的商品、神色各異的行人,仰望高聳的大樓,也看上車下車的人,觀察他們的動作和神態,猜測他們的內心。我成了偷窺者,窺視眼前所見的種種,回溯過去消逝的種種,揣摩即將發生的種種,盡管許多事暫時不得而知。
上了大學,坐大巴、動車去更遠的地方,從周邊縣鎮到其他城市,有時候呼朋喚友,有時候獨自一人。大三寒假去得最遠,從玉林坐了一夜火車去重慶,坐飛機去拉薩,又坐大巴到日喀則,在珠穆朗瑪峰腳下止步,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一次壯舉。在異鄉的冰天雪地遙望南方時,心中浮起許多情緒和感懷,不承想當年連坐公交車都緊張的小男孩,已經能心靜如水穿梭在山川人海中了。
四
十三歲那年,我看了幾本小說,寫了點故事,有了成為作家的理想。要實現理想意味著需要更多時間獨處,而非無聊能描述,需要另一個更沉重的詞:孤獨。最開始我沒有意識到什么是孤獨。我的目的很簡單,寫一部世界名著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作品才能叫世界名著,具體寫起來都是把心中臆想的東西落在紙張里,覺得這樣就能朝名著進發。
聽說網絡小說很賺錢,我非常缺錢,便開始寫些又臭又長的蹩腳故事。在小說里,我成了主角,配角都是周邊人的化身,兄弟忠誠于我,女孩們仰慕著我,討厭的人都是反派,雖一時囂張但最終都要跪地求饒。我長期浸淫在這種情境中,每一部開篇都覺得有成為世界名著的潛質。白天在自習課和英語課上寫,晚上在廁所里寫,再晚一點埋在被子里用二手按鍵手機錄成電子文檔,還沒攢夠簽約的字數就開始考慮申請哪個銀行的卡收錢,結果無一不被拒。頹廢后馬上自我安慰,自己寫的故事中主角也會受到挫折,堅持堅持就好了,再走幾步就好了,又磨了十多萬字,網站依舊拒絕,便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大罵文壇腐敗、世界無望。
頭腦里奇奇怪怪的想象有了寄托,即便沒有一部小說的構思能完整實現,我依舊信心滿滿,享受這種沖刺的激情,忘了自己曾是害怕寫字的人。我覺得自己是最獨特的那一個,早早貼上作家的標簽,想讓周邊人刮目相看。很多人認為我只是自娛自樂,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只有外公相信我的話,支持我的理想。高二那年,外公去世,我因將太多心思放在寫作上,成績一落千丈,理想重重摔在地上。我體會到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放棄了網絡小說創作,開始閱讀經典名著與現當代名家作品。
我對自己的水平有了新的判斷,別說世界名著,就算追上活著的作家也很難。于是我決定分期支付理想,第一步是先追上活著的作家們。我看他們的書,模仿他們的寫作,偶爾投給一些校園雜志,都收不到回音。高三停筆一年,早起晚休,勉強考上一所二本院校的物理系。彼時我對理想更加狂熱,即便中學最擅長物理,也要轉去讀漢語言文學。我接觸到活著的作家,閱讀經典和專業理論,了解文學史,視野逐漸開闊,懂得鑒別文學作品的優劣,迫不及待想提高創作水平。
我瘋狂挖掘適合自己的素材,那些兒時陪伴過我的,不知何時消失的玩伴重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長大了,他們還停留在過去。他們或青面獠牙,形象恐怖;或小巧可人,惹人憐愛;或平平無奇,宛如常人。他們都充滿怨氣,質問我為何將他們關在黑暗中。我說只是忘記他們的存在了。他們說遺忘的底色是黑暗,黑暗早已根植在我內心。他們整日在我耳邊絮絮叨叨,我感到煩躁、抑郁。終于,我難以忍受了,對他們大吼大叫,你們這群惡心人統統離開我的世界,不然弄死你們。在幻想中,我雙眼噴射火焰,身軀高大威猛,手提纏滿雷電的開刃大砍刀,宛如戰神與惡魔的混合體降臨塵世,俯視著這群聒噪的螻蟻!他們全都被嚇住,哇哇大哭起來。他們不得不告訴我真相:我無法粗暴地消滅他們,他們死去的唯一結果是成為我的一部分。
他們說,我如果想讓他們安靜,就得找到適合他們的去處。是的,我恍然大悟,他們與我同根同源,我要給他們找到住處,或者說找到墳墓,不然他們會讓我永世不得安寧。他們該去哪里呢?那些并不存在卻又鮮活的小人兒,我該如何安頓你們?某個深夜,敲打鍵盤的我猛然醒悟,望著屏幕上干癟的字句,找到了答案:我的兄弟姐妹,請住進我的文字里吧。
從此我的寫作不再如無頭蒼蠅,開始以自己的成長為基底,寫真實發生過的散文,寫由真實改編的小說。我的生活里全部都是與寫作相關的事,學習與愛情都得排后面。
我喜歡把自己關在不被打擾的地方寫,即便周遭有人,也能快速調整到精神狀態完全聚集于自身再寫,唯恐自己的小世界被窺探。為了真正免受打擾,有時到深夜才起床奮筆疾書,第二天迷迷糊糊上課。有時寫著寫著下雨了,站在窗邊看雨、聽雨,想起悲情的詩句,想起過往的不順,繼續融入更多相關的想象,不多時便進入一種自我坍塌的情景中,覺得人生多寒涼,如夢幻如泡影。
描摹往事是痛苦的過程,為此常常寫到疲憊不堪。我在河邊跑步,爬上山頂看日落,安撫內心躁動的小人兒。校園的風景無法緩解,我會背上書包,像多年前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坐上公交車蕩來蕩去,偶然換一輛,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戴上耳機,安靜地凝望窗外變換的景象。有時候也會不坐車,背著書包在城市里游蕩,有時快,有時慢,有時候還喜歡繞開鬧市,環繞在鬧市周邊的破敗小巷,覺得能看到城市的真實樣貌。我還癡迷于追求真實……城市的真實,人的真實,模糊記憶中的真實,小說情感的真實,愛情的真實,理想的真實。
五
真正的作家似乎對其他語言也非常敏感,我由此認定自己身上沒有作家天賦,源于創作多年依舊成績不佳,更源于對外語的遲鈍。我學不好英語,甚至字母都背不全,靠著理科拉分擠進大學,又因為英語沒能順利畢業。
我沒辦法繼續待在學校,回到貴港一家事業單位。單位的領導是作協主席,一位博覽群書、脾氣溫和的前輩,覺得我將來能有所成,給我爭取到了單位宿舍,讓我有個地方繼續沒日沒夜敲打鍵盤。
經濟是個大問題,沒有畢業證簽不了合同,連實習也算不上,有績效,最低時一個月八十五元,不夠吃一次夜宵。大學時有資助,偶爾有稿費和獎金,加上去做些兼職,勉強能過得去。而今要償還貸款、債務,要給家里,加上日常各種開支,存款很快見底,又不愿意再繼續借錢,過去只在書本網絡里聽說過的殘酷社會給我迎面一巴掌,最擅長的幻想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當父親早年在廣東打工落下的舊疾復發,不得不再次向朋友開口借錢——諸如此類瑣碎的事讓我感到挫敗。我心煩意亂,偏頭疼如鬼魅難纏,有時發呆到深夜,手上的鍵盤也敲不出字。
那種可怕的坍塌重新降臨,如綿軟的爬蟲從童年蔓延而來,包裹著我,啃食著我,淹沒了我。我再次看到賭博失利后的父親暴跳如雷,看到奶奶困于窮苦的生活唉聲嘆氣,看到那些人把我堵在角落威脅我成為替罪羊,看見為了土地費盡心血的親朋……我為此焦慮、惱怒,徹夜難眠,好不容易睡著也常常驚醒,身體里像空出一個大洞,要用食物填滿才有安全感,換來的是日益肥胖。
渾渾噩噩時,我看到了過去的自己。他還是一個小孩,笑死人,這個沒見過世面的小屁孩,竟然有那么疲倦的眼神。他透過遙遠時空凝視我,那雙眼膽怯又頑強,灰暗中搖曳著些許亮光。他似乎在說,過去那么艱難都過來了,現在害怕什么?我如遭雷擊,是啊,我在害怕什么呢?我害怕無法擺脫童年的夢魘,我害怕實現不了理想,我害怕陷入父輩的輪回。這些害怕阻礙著我,卻也是我前進的根本,所謂理想只是一個好聽的說法。
那段時間是成年后的低谷期,我沒有擊敗消極,幻想中的勇敢、果斷終究是虛幻。不過還是慢慢度過了,生活中的許多坎坷都是這樣,過著過著就成了閑談。我繼續保持創作,關于過去的文章一篇篇寫出,也慢慢得以發表。新的一年,我拿到畢業證,簽下工作,收到了些用稿通知,獲得了一筆可解燃眉之急的獎金。我繼續寫,我知道自己停不下來,文學是一條不歸路。我調整狀態,告訴自己太陽準備升起,熬過眼前這段黑暗就能到達明天。
我慢慢滿血復活。我的創造力是一口年輕的噴泉,鋪滿一頁又一頁的電子屏幕。我不再滿足于書寫過去。過往記憶是時間持續死去的尸體,我要看到時間還生動跳脫的模樣,看到現在,看到未來,于是我提筆寫科幻小說,構建遙遠未知的圖景。面對過往讓我感到沉重,卻是一件為了往前走而不得不去做的事。科幻創作讓我感到滿足,這是接受自我后的釋放,是擺脫粗劣模仿后幻想的決堤。回頭遙望,從初二閱讀第一本書后提筆,已經寫了十年,將整個青春奉獻給了這件令人著迷的事。從第一次接觸文學開始,它就不斷給我前進的力量,讓我大膽邁出一步又一步。
六
成長不只是身體的長高與肥胖,也是經過迷茫、解構與頓悟的心靈史,和大多數人相似,又不完全一樣。
童年的遭遇讓我對外界充滿警惕與疑惑,為此進行著一場漫長的追問,通過閱讀與寫作,通過偷窺世界、獨自思考與背起行囊遠行。這場追問在西藏之行時最強烈,身體越向西,越進入高原與荒涼寒冷地帶,心靈越朝故鄉走,回到童年深處與苦難開始的地方。我已得到許多答案,我想我還會得到更多答案,雖然最終難免一個又一個都被否定。
世界紛繁多變,記憶雜亂無章,我隱約記得最開始的創作源于一堆破爛玩具。父母勞燕分飛后,父親性情暴躁,我不太愿意與他說話,生活愈加貧困,唯一能緩解乏味的黑白電視機被他霸占,我又不得離家游玩時,只得把心思放在那堆玩具上。玩具有的從幼年積攢而來,有的是去撿破爛時意外所得,洗干凈后成為寶貝收藏,有折翼的飛機、斷腿的機器人、鏟斗丟失的鏟車……我將它們分成兩個陣營,互相攻擊,嘴里發出機槍嗒嗒嗒或者開炮轟隆隆的聲音。父親朝我的屁股踹過一腳,覺得腦子有病的小孩才自言自語。我不再配音,將戰場移到更隱蔽的地方,從兩個陣營到五六七八個派系,小石子與冰棒棍也成為人物、勢力、權力的象征,也不再是雜亂無章的攻伐,逐漸有了復雜的利益關系,你來我往,縱橫捭闔,一個故事或一場戰爭從開始到結束需要持續演繹好幾天,我將童年的漫長歲月消耗在這些大人認為毫無價值的事情上。
難以忘懷的年月,爸爸有一輛忠誠的、任勞任怨的二十六寸永久牌自行車。自行車前輪爆胎了沒錢修,盡管只要幾塊錢。沒氣不敢騎,會蕩壞輪轂。可沒自行車騎也不行,那是我家唯一的交通工具。爸爸想到辦法,把從垃圾堆撿回來的舊輪胎削成條,卷好,塞進自行車前輪填充。雖然沒有氣胎穩,但不傷輪轂,不怕釘子尖石,更耐用了。此后我再騎出去,成了被嘲笑的對象。不過我不在意,我生來就被嘲笑。我斗志昂揚,拼命地踩,要和他們爭個高下。他們的車太寶貝了,在平坦的水泥路上或許很快,但到了野外的坎坷小道,只有我敢不顧一切向前沖。那個時候,我最大的夢想不過是有一輛屬于自己的自行車。我渴望長大。如果我有一輛屬于自己的完好的自行車,我絕不像他們那樣懦弱,我要騎出光一樣的速度,沖進狂風暴雨中。他們會害怕未知的恐怖,我不怕,我會揮舞雙臂吶喊,像最后一個戰士沖向千軍萬馬,跌跌撞撞但不會倒下,雨滴是密集的箭穿透我的血肉我的心臟卻穿不透我的勇敢。隆隆雷聲多嚇人,萬物顫抖哭泣,我發出瘋癲的笑聲,騎著我的自行車朝未知的前路沖鋒。哈哈,我要碾碎閃電,碾碎烏云,碾碎一切阻擋我的妖魔鬼怪。我的自行車碾碎一切,我的想象力碾碎一切。看看吧,我從小就與他們不一樣,我肯定也能寫出和他們不一樣的文字。
我終于長大了。寫作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在構建各類文字中得以心安、得以蛻變。天馬行空的想象伴隨我走來,成為我賴以生存的資本。因此一個人的時候,我不感到孤獨,反而覺得這個世界熱鬧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