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中的文藝宣傳
周鐵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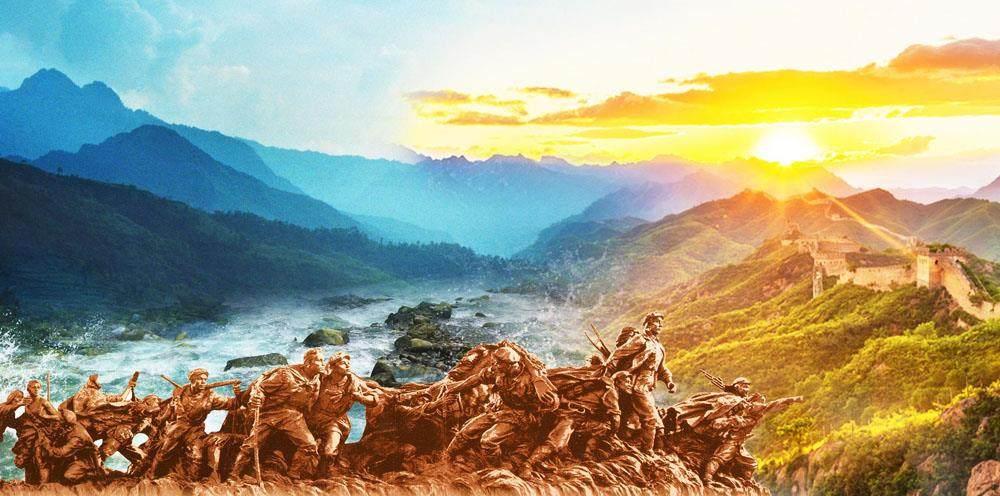
長征,是中國革命的一場播火之旅,是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在饑寒交加、艱難險惡的萬里征途上,紅軍通過豐富多彩的文藝演出、注重實效的戰地鼓動,激勵官兵斗志、發動組織群眾、擴大紅軍影響、感化瓦解敵軍,為長征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宣傳隊、工作隊、戰斗隊
長征路上,紅軍有多個專職演藝團體,稱為“劇社”,如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的“戰士”、“戰斗”、“工農”(后改名“前進”)劇社;紅三、紅五軍團的“火線”、“猛進”劇社;紅71、75、78師的“火光”、“火花”、“火焰”劇社等。人員統稱“宣傳員”。
各劇社雖有專職宣傳員,但演出大型劇目多會因人手不足,需到部隊邀請戰士、干部來客串角色,如排演大型話劇 《殺上廬山》,時任紅一軍政委的聶榮臻飾宋子文、保衛局局長錢壯飛飾蔣介石、政治部秘書童小鵬飾宋美齡、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飾德國顧問塞克特等。楊尚昆、羅瑞卿、羅榮桓、劉亞樓等紅軍將領,都曾應邀來劇社登臺演出。
長征路上的宣傳員,個個才華出眾、樂于奉獻。時任總政治部宣傳干事的李伯釗,是軍中有名的女藝術家,擅長歌舞,精于戲劇、音樂創作,擔任多個劇社的創編、導演。為做好文藝宣傳,她跟隨紅二、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一路創作出戲劇 《無論如何要勝利》《一起抗日去》,歌曲 《打騎兵歌》《兩大主力會合歌》,舞蹈 《紅軍舞》 《雅西雅舞》 等40多個(部)展示紅軍英雄氣概、宣傳北上抗日、表現民族團結的優秀作品。
蘇區政府秘書危拱之能歌善舞、能言善講,在凄風苦雨的行軍途中,月明星稀的露天營地,都能聽到她宣講的嗓音、動人的歌聲。時任“戰士劇社”分隊長的高勵,晚年仍熟記危拱之長征途中唱的 《鳳陽花鼓》 :“紅軍強,紅軍強,千難萬險無阻擋,行軍路上揍老蔣,北上抗日打東洋。”
紅軍每進入一個村寨,宣傳員除了演出,還要宣講黨的政策、紅軍的主張,教唱紅色歌曲;布置召開群眾大會會場,組織召開群眾座談會;清查、登記沒收的土豪財物;征集、購買軍糧;動員進步青年參加紅軍等。清晨,宣傳員要提前起身,到部隊即將行進的路上貼標語、寫口號,收集木棒、柴草等搭建“鼓動棚”,說唱時用來遮雨擋風;同時還要在“鼓動棚”里給戰士們燒開水,為傷病員煮稀飯;部隊通過后,又要幫助后衛團做好收容工作。
時任紅軍俱樂部主任的羅瑞卿曾回憶說:“劇社不單單唱歌、跳舞、演戲,更重要的是做部隊的政治宣傳和群眾工作,是軍中的宣傳隊、工作隊、戰斗隊。”
戰火硝煙中創作
艱苦條件下演出
長征路上,宣傳隊創作、演出的文藝節目,幾乎全部取材于部隊生活、戰地實際。1935年5月初,紅軍抵達金沙江畔,兩岸危崖高聳,江面水深流急,對岸守敵不時打來冷槍,背后的追兵也步步逼近。為激勵紅軍英勇渡江,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陸定一在戰地寫出歌詞《過金沙江》,配以當地民歌曲調:“金沙江流水響叮當,常勝的紅軍來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長。我們要渡江!我們要渡江!”
同時,紅一師宣傳科長彭加倫也創作出 《渡金沙江勝利歌》 :“鐵的紅軍勇難擋,要勝利渡過金沙江。帝國主義嚇得大恐慌,蔣介石弄得無主張,我們真歡暢。革命的運動,發展了個新局面,有把握解放川陜甘!”
宣傳員剛唱起這兩首歌,就在軍中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來找宣傳員抄寫歌詞。當天,每個連隊都響起振奮人心的歌聲“常勝的紅軍來渡江”,“要勝利渡過金沙江”。
1935年夏,軍團宣傳部長黃鎮發現路邊有許多丟棄的破草鞋,激發起他的靈感,決定寫一部展示紅軍睿智威猛、敵兵愚蠢無能的話劇。他和劇社同志在行軍中商議劇情、策劃場次,宿營時討論人物、寫作臺詞……沒幾天, 《破草鞋》 創作完成,全劇以詼諧幽默的語言、譏笑嘲諷的手法,鞭笞了國民黨軍隊的軟弱怯懦、狼狽不堪,頌揚了紅軍的足智多謀、英勇善戰。
在慶祝紅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的聯歡會上,“猛進劇社”首演話劇 《破草鞋》,受到官兵的一致好評,毛澤東連連稱贊:“好戲、好戲!”朱德豎起大拇指說:“這出戲看得才過癮嘍!” 《破草鞋》 從此揚名,各劇社紛紛排練,在長征路上久演不衰。
長征途中,劇社的各種條件十分艱苦、簡陋。演出道具多依據需要自制:竹條做鏡框,染上墨水就是眼鏡;將棉絮染黑,粘在臉上就是胡子;一頂破草帽,可扮放羊娃;一桿紅纓槍,能演兒童團。他們把打土豪沒收的服裝收集起來,演資本家就穿西服、打領帶,填個大肚子;演地主就穿長袍、套馬褂,端個水煙袋,讓觀眾看了就知道人物的身份。
晚間演出需要照明,就把帶油脂的松樹皮剁成小塊,用鐵絲捆成籃球大小,掛在橫竿上點燃。一個松皮球可燃燒近2個小時,大些的露天舞臺要點五六個,亮如白晝,但散場后每個演員的鼻孔、眼角、眉毛都沾滿黑漆漆的煙灰。
激勵官兵征服危境、戰勝險阻
為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官兵們常常晝夜連續行軍,許多人疲憊得邊走邊打瞌睡,有時一個摔跟頭,后面會絆倒一串。每遇這種情況,宣傳員就站在路旁,特別是狹道、山隘等險要的地方表演快板、說唱:“同志哥,快快走,把敵人甩在大后頭;同志哥,勇向前,紅軍就是不怕難……”節奏明快、通俗簡要的鼓動,讓官兵們精神抖擻、困頓舒緩,在輕松中加快了腳步。
翻越雪山時,宣傳員與大部隊緊緊相隨,用歌聲、口號、鑼鼓為官兵鼓勁加油。老紅軍高勵晚年時回憶說:“一鼓作氣爬到雪山半腰,忽聽前面傳來‘呱噠呱噠的竹板聲,是宣傳員劉乾益在說快板:‘翻雪峰、看本領,比比哪個是英雄,看誰最先到山頂……越往上爬,空氣越稀薄,呼吸也急促了,大家又餓又累,很想歇一會兒。這時,宣傳員們又鼓勵大家:‘同志們,山頂不能停留!不活動會凍僵,加油啊……”
草地行軍時,宣傳員的鼓動方式機動靈活。戰士們疲勞了,宣傳員就說唱鼓勵:“同志們,別泄氣,你幫我,我幫你,齊心協力過草地。咬緊牙,鼓足力,穿過草地是勝利……”看到某同志力氣足、走得快,就編幾句順口溜表揚他:“這個同志走得急,把敵人甩下幾百里,這個同志兩腿快,走出草地拿獎牌……”走得慢的聽了,會加快腳步趕上來。
當時,宣傳員創作的 《過草地》 歌,官兵人人會唱:“六月里來天氣熱,黑水蘆花青稞麥,穿過草地為哪個?為了蘇維埃新中國!”
1936年4月,紅二方面軍擺出攻打昆明的陣勢。蔣介石驚慌失措,緊調重兵增援,紅軍卻突然回師,攻克了兵力空虛的楚雄、麗江等13座縣城。部隊迂回奔襲、浴血激戰的10多天里,各軍團劇社在炮火硝煙中演出了30多場,鼓舞官兵的斗志、增強勝利的信心。
架起溝通群眾、民族團結連心橋
長征期間,國民黨反動派、反動豪紳在百姓中散布謠言,污蔑紅軍“殺人放火、搶男霸女”,“青面獠牙、專吃人腦”等,被欺騙的群眾對紅軍產生恐懼,甚至抱有敵意。許多地方的居民聞聽紅軍要來,便封埋水井、掩藏糧食,拖家帶口地遠遠躲避。
1935年3月,紅軍進入黔北桐梓地區,許多百姓被謠言嚇得四散躲藏,但留守老人們偷偷望去,見紅軍并不像傳說中那么可怕,就三三兩兩走出家門。宣傳員王泉媛、洪水等人立刻向他們宣講“紅軍是老百姓的隊伍,為窮人翻身打仗……”等。見女紅軍說得有理,講得感人,老人們消除了恐懼,四下一招呼,躲出去的人陸續回來了,宣傳隊借機演出小話劇 《苛捐雜稅多如毛》,揭露軍閥欺壓百姓、拉丁派款、強行收稅。戲演到高潮時,群情激憤,在宣傳員帶領下齊聲高呼:“支援紅軍!”“打倒國民黨!”“消滅反動派!”
話劇演完,群眾興猶未盡,宣傳員又唱起 《當兵就要當紅軍》 《紅軍歌》 等,許多青年深受感動,當即要求參軍。幾天后紅軍開拔,桐梓縣有千余名青壯年入伍。
長征,30%以上的路途是苗、瑤、彝、藏等少數民族集聚區,大多或空曠偏遠、或山高林密,群眾對外界情況所知甚少,加之語言不通,無法交流,很難消除他們對紅軍的戒備和敵意。為扭轉這種被動局面,紅軍制定出較為完整的民族政策和執行細則,宣傳隊把政策與細則的主要內容編進文藝節目,沿途為各族群眾宣傳演出。
1936年2月,紅二方面軍抵達黔西北苗族聚居地,十幾名宣傳員在當地向導(翻譯)的帶領下來到苗寨,通過翻譯向群眾講述“共產黨為人民求解放、紅軍為窮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并演唱 《紅軍歌》 《苗家救星》 等,跳起苗族舞蹈,學唱苗族山歌。苗寨群眾深受感動,也即興填詞,唱起山歌:“苗山的樹林根連根,苗家和紅軍心連心。”
1936年5月,紅軍抵達甘肅靜寧回族集聚地,宣傳員分成小組,召集回族群眾開座談會,宣講黨的民族政策,還為回族同胞掃院劈柴、擔水洗衣、表演文藝節目、教唱紅色歌曲等。見到宣傳員的所作所為,回族群眾感動地說:“常有各種各樣的隊伍經過,還從沒見過這樣的仁義之師!”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紀實文集 《紅星照耀中國》 中寫道:“紅軍占領一個地方以后,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了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
感化、瓦解敵人,擴大紅軍隊伍
長征路上,面臨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紅軍除了英勇阻擊、戰略迂回等,還采取政治攻心、文藝宣傳等方式,感化、瓦解敵人。
1935年,紅軍編印出 《痛苦士兵》 的小冊子,以五言口號詩形式揭露日寇入侵、蔣介石不抵抗的事實,鞭笞軍閥的腐敗墮落、欺詐盤剝,訴說白軍基層士兵的壓抑憤恨、迷茫痛苦等。宣傳員每到陣前喊話,都首選 《痛苦士兵》 的內容,讓敵人了解紅軍“打仗為窮人”、“北上去抗日”的主張,認識到“當兵當紅軍”、“棄暗來投明”才是正確出路。
1935年10月20日,紅軍發起直羅鎮戰役,戰斗接近尾聲,有一股敵軍守在一個堅固寨子里,紅軍久攻不下。劇社就組織20多名宣傳員,登上與寨子對峙的山頭,拿著硬紙板做的話筒,朗讀 《痛苦士兵》,然后用當地方言合唱 《當白兵苦得很》。喊話、唱歌持續了近1個小時,守敵的精神防線完全崩潰,打出白旗,全部投降。
這次戰役中,紅十五軍的一個連在葫蘆河區域,與東北軍109師的一個營遭遇。面對強敵,宣傳員唱起 《松花江上》 《流亡曲》 等。東北軍官兵被情真意切的歌聲打動,悄悄撤離了陣地。第二天,許多東北軍官兵帶著武器前來投誠,要求參加紅軍,北上抗日,打回老家去!
長征途中,宣傳隊還擔負爭取、教育俘虜工作。時任紅一方面軍宣傳干事的李兆炳,創作出一部表現白軍士兵受黑心上司奴役驅使、欺壓盤剝悲慘經歷的歌劇 《血汗為誰流》。遵義戰役中活捉千余敵兵,為教育、感化這些俘虜,宣傳員為他們演出這部歌劇。剛開始,俘虜不屑一顧,當演到一半,有些人被感動,掩面落淚;又看了一會兒,俘虜對蠻橫兇暴的“軍官”義憤填膺,振臂高呼:“不給國民黨賣命!”“我們要參加紅軍!”
埃德加·斯諾對紅軍用文藝宣傳感化、瓦解敵人給予了高度評價,在 《紅星照耀中國》 中寫道:“他們設備這么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需要……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長征途中的文藝宣傳,戰勝了行軍打仗的危境,克服了自然環境的險惡,以及物質匱乏、條件簡陋等一系列艱難,為長征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生動體現出長征精神的文化內涵,譜寫出一部永遠銘記史冊的華章典卷。
選自《大江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