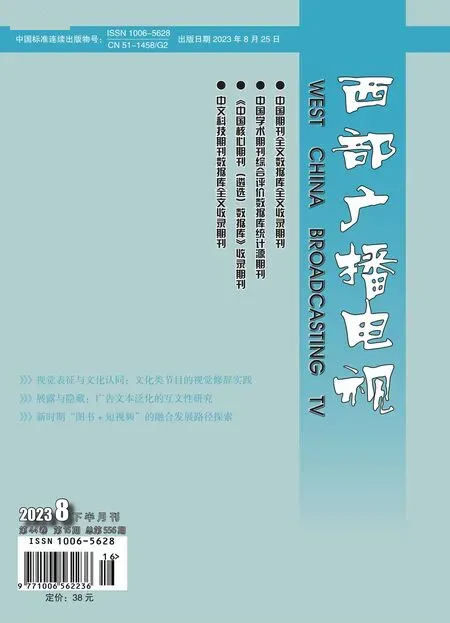“聲音景觀”下的網絡廣播劇傳播研究
——基于貓耳FM 用戶心理分析
耿鴻星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1 研究背景
隨著照片、電影、電視的誕生,人類開始進入“讀圖時代”。人們可以運用媒介技術更便捷地獲取信息,這一階段以視覺為中心,人類的視覺器官得到了全面的運用。但是,以圖像為主導的視覺文化往往伴隨著“消費霸權”和“技術霸權”,時間久了,人類很可能變成技術的附庸品。隨著網絡媒介技術的普及,視覺文化的主體地位正在坍塌,新的聽覺文化正在崛起。聽覺的回歸打破了視覺傳播的霸權地位,并開啟聽覺文化的構建。
從文化和社會的需要來看,聽覺互動對社會文化情感結構的構建和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當下,人與人的情感交流往往訴諸數字化媒介,如微信、微博,很多時候甚至連文字都被各種表情符號所替代,更不用說面對面的交流和傾聽。傳統(tǒng)的社會情感表達變得淺顯化,人們花在各種情感交流上的時間越來越少,甚至發(fā)展到抗拒、排斥情感表達,情感問題似乎正在被漠視。在此情況下,建立在聽覺互動基礎上的廣播媒體,實則擔負起了喚醒聽覺、重新激發(fā)感性情感表達的重要使命[1]。
聲音作為一種媒介,它中介了人與人、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既是人感受周圍世界的一種尺度,也是人涉入世界的一種方式[2]。因此,本研究嘗試從“聲音景觀”的角度出發(fā),分析貓耳FM 廣播劇與用戶感官的互動關系,用戶使用需求與用戶的社會背景、聲音接收環(huán)境等的關系,對廣播劇三維立體空間環(huán)境的構建問題進行細致研究。
2 研究現狀
2.1 關于“聲音景觀”的研究
“聲音景觀”研究,就是將聲音看成一種環(huán)境,通過聲音這個媒介,人們能夠跟其形成的環(huán)境進行互動,這種互動可能是肢體上的,也可能是感官上的。以往對于聲音的研究,人們更多關注聲音所傳達的內容,而忽略了聲音本身。而“聲音景觀”的出現則打破了將聲音扁平化的舊有的思維邏輯,指出了聲音環(huán)境的形塑能力、聲音的空間性以及聲音的感官互動性這些議題。“聲音景觀”研究從空間與聽者的感官經驗出發(fā)來考察聲音環(huán)境,及經由人的聽覺方式(包括解讀聲音文化意義的能力和聽覺的涉身傾向)而在內心形成的對此聲音環(huán)境的印象[2
]。
“聲音景觀”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聲音景觀”具有物理性,它存在于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聲音及構成聲音的物質材料共同構造了“聲音景觀”這一瑰麗現象。另一方面,“聲音景觀”中蘊含著豐富的聽覺文化,聽眾、聽眾所處的環(huán)境以及聲音內容是其中的重要構成要素。比如,當周末人們待在家里,聆聽手機里的美妙樂曲時,此時的“聲音景觀”表現為一種高級的審美文化。
2.2 關于中國網絡廣播劇的研究
20 世紀20 年代,廣播劇這種藝術形式應運而生。到20 世紀70 年代,廣播劇的發(fā)展到達了頂點,涌現出許多優(yōu)秀的廣播劇作品,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紀90年代,隨著新媒介技術的普及,廣播劇開始衰落。
互聯網時代到來以后,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汽車的普及,廣播和廣播劇又一次興盛。互聯網與廣播劇結合出現了網絡廣播劇,目前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消費市場。艾瑞咨詢發(fā)布的《中國網絡音頻行業(yè)研究報告》顯示,2019 年中國網絡音頻行業(yè)市場規(guī)模為175.8億元,同比增長55.1%,中國網絡音頻用戶逐年上升,2019 年規(guī)模已經達到4.9 億[3]。網絡音頻市場具有很大的消費潛力,隨著移動端的普及,許多音頻應用程序(Application, App)應運而生。
作為知名的廣播劇App,貓耳FM 極具代表性。目前,對于網絡廣播劇的研究主要從內容制作模式、盈利方式、發(fā)展策略等方面展開,缺少從聲音構建的環(huán)境分析用戶心理。本文嘗試在“聲音景觀”的理論下解讀廣播劇與耳朵互動關系的建立。
3 研究方法與思路
研究采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法。參與式觀察是通過加入廣播劇微信社群,記錄分析群成員(即用戶)對于廣播劇的理解感悟。深度訪談主要采用面對面交談、線上交談的方式,對被訪談者進行發(fā)問,并記錄訪談內容。
研究對象主要包括貓耳FM 的廣播劇用戶、廣播劇內容。文章選取目的性抽樣和方便抽樣的方式,受實際情況限制,在廣播劇微信粉絲群中選取了20 位不同年齡和職業(yè)且使用貓耳FM 收看廣播劇一年以上的用戶作為訪談對象,進行深度訪談。訪談提綱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問題:(1)你是怎么接觸到網絡廣播劇的?聽網絡廣播劇的原因有哪些?(2)你經常聽廣播劇嗎?平常會使用哪些App 聽廣播劇?(3)你通常會在哪種情境下聽廣播劇?你覺得廣播劇滿足了你的哪些需求?(4)你喜歡聽什么類型的廣播劇?廣播劇的哪些元素會影響你去選擇它呢?(5)你是否喜歡有畫外音解說的廣播劇?(6)你是否覺得廣播劇比電視劇有優(yōu)勢?(7)同一部小說改編成廣播劇或電視劇,你更愿意選擇哪個?原因是什么?
根據研究問題與訪談內容的特點,本文借鑒了扎根理論的資料分析方法,依照由下而上的生成邏輯,最終完成三級編碼,得出文章核心要點。表1 為編碼示例。

表1 “聲音景觀”下網絡廣播劇的用戶使用心理
4 研究發(fā)現
通過對訪談文本的整理和分析,從貓耳FM 用戶心理的角度,筆者發(fā)現,廣播劇的聲音屬性使它可以突破視覺的限制,聽覺空間的延伸性和聲音的塑形性給用戶帶來了無盡的想象空間和情感共鳴。此外,聽覺還可以分離公私空間,塑造新的文化群體。
4.1 伴隨媒介:突破視覺限制
與文字語言和視覺影像相比,聽覺語言的伴隨性非常突出,它解放了雙眼、雙手。如例(1)所說,不論是在開車途中還是在做家務的過程中,都可以隨時收聽廣播劇。保羅·萊文森指出:媒介互相競爭,爭奪人們的注意力,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存活,那要看它們是否有獨特的性能滿足人的需要[4]。視覺媒體具有非強制性,而聽覺媒體的強制性使得它的存活時間極為長久。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文字語言和視覺語言是一種選擇性語言,而聽覺語言則是一種強制性語言。這是聽覺傳播的巨大優(yōu)勢之一。
例(1):
我一般聽廣播的時間可能是在做家務、做飯的時候,這只用聽就可以了,不需要眼睛看,不耽誤我手頭兒的事兒。然而像電視劇就不行了,我不能一邊看電視一邊忙其他的。(訪談者張小姐)
用戶在使用貓耳FM 收聽廣播劇的時候,也可以同時忙別的事情。網絡廣播劇與生俱來的強制性使得它生命力頑強,又因為其便利的伴隨性得到用戶喜愛。
4.2 無盡想象:聽覺空間的延伸
網絡廣播劇所構建的“聲音景觀”可以延伸人的聽覺空間,激發(fā)無盡的想象力。區(qū)別于視覺化媒介內容,網絡廣播劇靠聲音傳遞內容,它似乎是無形的[5],而這種非視覺化的傳播又能夠刺激人們進行畫面創(chuàng)作和想象。
例(2):
廣播劇的精彩內容比電視劇多,題材還很全。而且廣播劇不會受到‘服化道’的限制,更符合自己的想象,我還是更喜歡廣播劇多一些。(訪談者李小姐)
在研究中,受訪者也提到了廣播劇“不夠具象,但卻能夠激發(fā)想象力”,如例(2)。廣播劇不包含任何的圖像內容,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它可以被不同年齡、不同生活背景和性格特征的人所接受,人們可以肆意地在頭腦中構筑個性化景象,不用被視覺符號所干擾。聲音沒有視覺角度的限制,大大拓展了廣播劇的想象空間。
但同時,網絡廣播劇所勾起的人們的想象力并不是毫無根據的想象,而是在精彩劇情和自身文化積累基礎上的合理發(fā)散。耳朵能夠聽到什么,采取什么聆聽方式,都離不開社會背景和歷史語境的“規(guī)訓”。廣播劇用戶在腦海中所構建的聲音圖景由其經驗背景作支撐,聲音所激發(fā)的想象力是有界的。
4.3 情緒影響:聲音的塑形
聽覺的背后是感性。廣播劇通過聲音的傳達放大了用戶的感受,人們不僅可以通過聽覺系統(tǒng)捕捉到聲音的發(fā)生,還可以通過內心去感受聲音。
例(3):
我覺得風聲、雨聲、汽車聲等,在劇中都起到了很好的輔助性的作用,這些都有助于我想象劇情中的畫面,給我打造了一個立體的空間,仿佛我就在情境里面。(訪談者郭小姐)
例(4):
“我的情緒會受廣播劇的影響,甚至比電視劇更深。如果配音演員的聲音夠出彩,我會跟著一起哭一起笑,忍不住地跟配音演員共情。”(訪談者林小姐)
用戶對于網絡廣播劇的喜愛,不僅表現在它可以激發(fā)自身的想象力,還在于它能夠通過聲音的塑形功能,還原視覺等多種感官體驗。網絡廣播劇聲音的塑形功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營造氛圍,二是影響用戶情緒。網絡廣播劇主要通過廣播聲音效果來營造傳播氛圍,如風聲、雨聲、汽車鳴笛聲等,如例(3)。此外,數字技術運用了擬音的方式,配音演員將情感變化融入聲音中去,用戶的情緒受到調動會直接參與聽覺互動的敘事,如例(4)。
數字時代,廣播劇給人們帶來的是沉浸式的體驗,每個聲調、音符的起承轉合都被聽眾盡收耳中。這種聲音的密切接觸實現了用戶與配音演員的“場域性情感”共鳴。
4.4 公私分離:社會空間再造
聲音還能幫助用戶再造空間,達到個人空間跟公共空間分離的理想狀態(tài)。如例(5),網絡廣播劇營造的具有流動性的聽覺空間則能夠幫助用戶將空間“私有化”,正如用戶大多都喜歡戴耳機在相對私密的空間里自己聽廣播劇,而不是選擇外放。
例(5):
“我一般喜歡戴著耳機聽廣播劇,感覺這樣不會受到其他聲音的干擾,能夠有一個相對私密的空間。而且,有些廣播劇的內容感覺被別人聽到也不太好,這是一個小眾愛好,不一定人人都能理解。”(訪談者林小姐)
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公共聲音空間也已成為一個越來越復雜的互動結構。一方面,公共的聲音空間可以繼續(xù)服務于個人所需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它不斷重塑聽覺社區(qū),在聽覺社區(qū)內個人的身份仍具有復雜性。聽覺文化空間既是虛擬的,又帶有社會性特征。如例(6),廣播劇用戶在線下很難集群,但是在網絡空間里卻打造了自己的社區(qū),這使得私密空間獨享的廣播劇帶有了社會性色彩。
例(6):
我加入了一些配音演員和一些廣播劇交流的粉絲群,我們擁有共同的興趣愛好,能理解彼此的想法。有我認為比較精彩的廣播劇也非常愿意在群里和大家分享。(訪談者許小姐)
5 總結與反思
借助網絡廣播劇的影響力,越來越多的人體會到聲音的魅力。但是網絡廣播劇仍有不足,用戶在收聽網絡廣播劇時還要注意分辨不良題材的廣播劇。
此外,本次研究在選擇樣本上略有不足,訪談對象均為女性,沒有采訪到男性用戶。且由于條件的限制,沒有采訪到廣播劇內容生產者、配音演員、喜馬拉雅FM 廣播劇的營銷者等,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