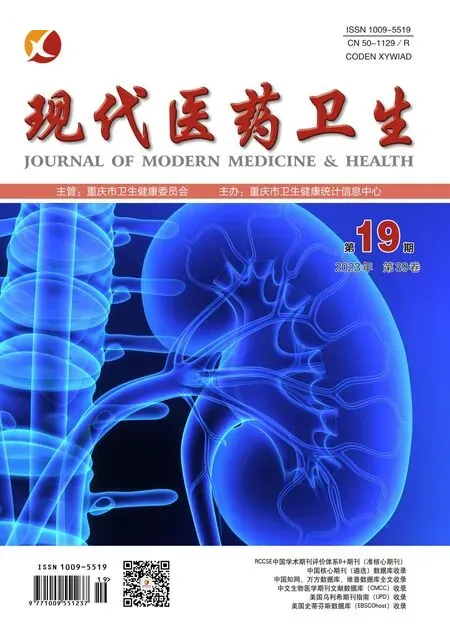腦性癱瘓兒童脊柱側彎的臨床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李承陳,溫迪光,李宣穎,楊 霞,周文智△
(1.電子科技大學附屬成都市婦女兒童中心醫院兒童康復科,四川 成都 610091;2.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消化內科,重慶 400010;3.成都市成華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57)
腦性癱瘓(腦癱)是一組持續存在的中樞性運動和姿勢發育障礙、活動受限癥候群,其是由于發育中的胎兒或嬰幼兒腦部非進行性損傷所致[1],主要表現為異常的運動模式和姿勢、運動失調及肌張力異常。痙攣型偏癱腦癱表現為一側上、下肢痙攣型癱瘓而對側上、下肢正常。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屬更多關注腦癱兒童體態問題。目前,關于腦癱兒童運動功能、步行能力的研究較多見,但關于腦癱兒童體態的研究報道較少見[2]。不良體態會影響腦癱兒童肌肉、關節和韌帶的正常發育,誘發軀體疼痛和機能退化,進而影響體質水平和運動能力,甚至帶來心理問題,降低其生活質量。兒童期異常體態屬于可矯正型的功能障礙,早發現、早預防、早教育、早矯正可改善甚至消除體態問題,是開展靶向性體態塑造教育的關鍵環節,對腦癱兒童的健康成長具有積極的作用[3-4]。本研究探究了腦癱兒童體態現狀及其與脊柱側彎發生的相關性,旨在為優化治療方案及腦癱兒童脊柱側彎早期防控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8月至2022年3月在電子科技大學附屬成都市婦女兒童中心醫院接受治療的痙攣型偏癱腦癱兒童128例作為病例組,同時在成都市成華區幼兒園、小學選取年齡、身高、性別相當的健康兒童128例作為對照組。納入標準:(1)符合第九屆全國小兒腦癱會議制訂的痙攣型偏癱腦癱診斷標準和臨床分型標準[5];(2)經粗大運動功能分級系統(GMFCS)評定為Ⅰ級或Ⅱ級;(3)年齡6~8歲;(4)能理解和執行口令;(5)在無輔助下可獨立行走大于10 m;(6)近6個月內未行手術及肉毒素注射治療。排除標準:(1)近6個月內接受過肉毒素注射治療;(2)偏癱側上肢未行外科矯正手術治療;(3)口服抗痙攣藥物治療;(4)認知功能障礙,不能配合評估;(5)不同意參與本研究;(6)并發其他運動系統疾病,影響肌肉肢體功能。研究對象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2組性別、年齡、身高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2組一般資料比較
1.2方法
1.2.1測量方法 脊柱側彎篩查及體態評估方法:采用韓國MZEN公司制作的Bodystyle身體姿態評估測試儀(Model.S-8.0)對研究對象正面、側面、背面進行體態及人體靜態身體姿態狀況評估。評估時,赤腳,裸露背部,兩腳并攏,自然放松站立,采用正面觀拍攝,對左右肩峰進行球形標記,系統識別并對左右側肩峰的高度差及傾斜度差進行測定分析。若高度差及傾斜度差大于2°,則確定為高低肩;若小于2°,則排除高低肩[6]。對左右髂嵴進行球形標記,采用正面觀拍攝,系統自動識別左右髂嵴的高度差及傾斜度。若高度差及傾斜度大于2°,則確定為骨盆側傾;若小于2°,則排除骨盆側傾。對左右髕骨左右距骨進行球形標記,采用正面觀拍攝,系統自動做出距骨的垂線、距骨中點與髕骨中點之間的延長線,測定兩線之間的角度和長度,結果表示為左O(X)/右O(X)的傾斜角度。若傾斜角度為3°~<5°,則判定為O型腿;若為-3°~<1°,則判定為X型腿。采用側面觀拍攝,系統做通過肩峰的矢狀面上的假想直線及通過耳垂與肩峰的直線,測定兩線偏差。若偏差大于2.5 cm,則確定探頸(頭前傾);若小于2.5 cm,則排除探頸(頭前傾)。采用側面觀拍攝,系統自動做髂后上棘的水平線,并做通過髂前上棘和髂后上棘的直線,測定兩線延長交叉后形成的內角度數,結果表示為向前/向后的傾斜角度。若傾斜角度大于15°,則確定為骨盆前傾;若小于15°,則排除骨盆前傾[7]。
由同一名治療師對研究對象進行生理因素檢查:采取仰臥位,骨盆水平位,下肢伸展,髖關節中立位。測量從髂前上棘到內踝的最短距離,或從股骨大轉子到外踝的距離,若雙下肢數值差大于或等于0.3 cm,則確定為長短腿,并記錄其差值。對病例組左右兩側肢體進行徒手肌力測試(MMT)分級,采用改良Ashworth量表(MAS)進行偏癱側上下肢肌張力評定分級。采用背面觀拍攝,進行Adams前屈試驗:赤腳,裸露背部,兩腳并攏,兩腿伸直自然放松站立,兩臂向前平伸手掌相合,慢慢向前彎腰至90°左右,同時雙手置于雙膝間,用健升牌脊柱側彎電子測量尺由上到下依次測量頸段C7到腰段L1的讀數。若讀數小于5°,則排除脊柱側彎;若大于或等于5°,則確定為脊柱側彎,同時記錄對應的脊柱節段[8]。
1.2.2調查分析 為了解脊柱側彎的影響因素,自行設計兒童體態側彎評估表。該表通過多輪專家審閱反復修訂成稿,記錄腦癱兒童臨床資料,主要內容為:(1)生理因素包括軀干左右兩側肌力是否差2倍以上,是否雙肢不等長,偏癱側肢體肌張力是否大于或等于2級;(2)其他體態因素包括是否存在高低肩、骨盆側傾、頭前傾、骨盆前傾、X/O型腿。分析上述因素在腦癱兒童繼發性脊柱側彎中的影響作用,分析腦癱兒童脊柱側彎的臨床特征。問卷經Bartlett球形度檢驗,KMO值為0.77,Cronbach′α系數為0.90,內部一致性信度較好。

2 結 果
2.12組體態情況及脊柱側彎發生率比較 2組高低肩、骨盆側傾、骨盆前傾、頭前傾、雙肢不等長、腿型異常及脊柱側彎發生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

表2 2組體態情況及脊柱側彎發生率比較[n(%)]
2.2腦癱兒童脊柱側彎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骨盆前傾、腿型異常、軀干左右兩側肌力差2倍以上、偏癱側肢體肌張力大于或等于2級、雙肢不等長是腦癱兒童脊柱側彎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3。

表3 腦癱兒童脊柱側彎單因素分析
2.3腦癱兒童脊柱側彎多因素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中的脊柱側彎危險因素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骨盆側傾、雙肢不等長、腿型異常、軀干左右兩側肌力差2倍以上、偏癱側肢體肌張力大于或等于2級是腦癱兒童脊柱側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4。

表4 腦癱兒童脊柱側彎多因素分析
3 討 論
本研究中,腦癱兒童存在不良體態,主要表現為高低肩、骨盆側傾、腿型異常,其中高低肩為偏癱側肩峰高于健側,肩胛骨偏癱側高于健側;骨盆側傾為健側高于偏癱側;腿型異常以偏癱側膝外翻為主。本研究結果顯示,病例組脊柱側彎率為78.12%,顯著高于對照組的15.62%。脊柱被稱為“人體第二生命線”,腦癱兒童正處于生長發育的黃金期,脊柱一旦側彎,會對凹側的內臟器官造成嚴重壓迫,從而影響正常的生長發育[9]。
本研究結果顯示,腦癱兒童脊柱側彎多為繼發性,骨盆側傾、雙肢不等長、腿型異常、軀干左右兩側肌力差2倍以上、偏癱側肢體肌張力大于或等于2級是腦癱兒童脊柱側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骨盆側傾、腿型異常、雙肢不等長使軀干生物力線偏斜,可能是造成腦癱兒童脊柱側彎的內在原因[10]。因此,腦癱兒童在早期注重兒童步行功能的同時,也應該注重兒童發育過程中下肢是否等長、腿型是否異常。如雙下肢不等長,應及時穿戴足弓墊,使站立行走時軀干有正常力線;如下肢存在腿型異常(膝關節外翻),應及時佩戴支具,進行腿型糾正訓練。本研究中,腦癱兒童脊柱側彎點多在上中胸段(T1~T8),在早期康復訓練時應注重腦癱兒童偏癱側胸段的肌力訓練、骨盆力量訓練和軀干核心力量訓練,盡量使肢體左右兩側肌力差距縮小,從而減輕脊柱側彎的嚴重度。相比于傳統脊柱側彎尺,本研究采用的脊柱側彎電子測量尺可反映整個脊柱(C7~L1)的側彎情況,從而能更準確地判斷脊柱側彎及發生節段,但其篩查靈敏度并不能達到100%,可能存在部分漏診情況,導致錯分偏倚[11]。此外,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如樣本量較小、觀察時間較短等,仍需要未來進行多中心、長周期的臨床試驗進行驗證。
綜上所述,腦癱兒童體態異常和脊柱側彎檢出率較高,骨盆側傾、偏癱側下肢腿型異常(X/O型腿)、雙下肢不等長、偏癱側肢體肌張力過高、偏癱側與健側肌力差距過大是腦癱兒童繼發性脊柱側彎的獨立危險因素,腦癱兒童進行早期康復治療時應關注上述體態及脊柱側彎問題,制定科學的綜合治療方案,從而降低腦癱兒童體態異常及脊柱側彎發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