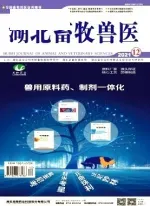葉蟬科昆蟲口器的超微形態研究進展
張雅婷
(安徽新華學院,合肥 230088)
葉蟬科(Cicodellidae)是半翅目(Hemiptera)頭喙亞目中最大的科,該科昆蟲具有典型的刺吸式口器,其中很多種類都可以傳播植物病毒。研究葉蟬科昆蟲口器的超微形態可以為該科昆蟲的系統發育提供形態學依據,也可以為防治葉蟬科昆蟲提供有效依據。有學者就葉蟬科部分種類的超微形態特征進行了研究,但總體看來,該方面的研究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通過對葉蟬科昆蟲口器的超微形態學研究可為葉蟬科昆蟲的形態學研究和系統學研究提供參考,為相關害蟲的防治提供依據。
1 葉蟬科昆蟲口器的分類
口器是昆蟲重要的取食器官[1,2],因昆蟲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口器會產生適應于不同寄主和組織的結構[3]。半翅目的刺吸式口器在寄主植物選擇、取食以及植物病毒傳播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4,5]。
口器的外部形態特征根據昆蟲的食性以及其不同的取食方式而發生改變,從而形成不同的口器類型。主要分為咀嚼式口器、刺吸式口器、虹吸式口器、舐吸式口器、銼吸式口器、刮吸式口器、捕吸式口器、刺舐式口器和嚼吸式口器9 種不同的口器類型[6]。
2 葉蟬科昆蟲口器的形態結構
葉蟬科昆蟲的口器從頭的腹面后方生出,向后置于體腹面,由上唇(Labrum)、下唇(Labium)和口針束(Stylet fascicle)3 部分組成,是典型的刺吸式口器,其上唇較短,呈三角錐形;下唇較長,呈圓柱形;口針束細長,由2 根上顎口針(Mandibular stylets)和2 根下顎口針(Maxillary stylets)組成,是葉蟬的取食器官,被包裹在下唇中,從下唇端部的開口伸出[7]。葉蟬科昆蟲的刺吸式口器特化為針狀結構,這樣既有利于口器在植物組織間穿刺,又可有效地避開植物表皮的防御性物質,從而吸取植物木質部或韌皮部中營養豐富的汁液[8]。葉蟬科昆蟲的口器上分布有大量的感器,在行為活動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順利完成其寄主的選擇、食物的定向、尋找和識別,從而進行相應的取食[9]。
Cobben[10]借助超微手段,對頭喙亞目的3 種蠟蟬、3 種沫蟬、1 種角蟬、1 種葉蟬和1 種蟬,從喙的結構和功能、口器的感器、口針的結構和功能、食性的選擇等方面系統地研究了半翅目昆蟲口器結構及其取食策略。Tavella 等[11]研究發現大葉蟬亞科(Cicadellinae)昆蟲的上、下顎口針長度明顯大于小葉蟬亞科(Typhlocybinae)昆蟲,符合它們在系統發生中的位置。Brozek 等[12]發現葉蟬科昆蟲的唾液道通常位于下顎口針的右側。Leopold 等[13]明確了玻璃翅葉蟬(Homalodisca coagulate)口器的超微形態特征并對其口針在植物組織中的穿刺方式進行了研究,推測口針束末端的小齒可能具有定位取食植物木質部的感器功能,且口針的穿刺發生在木質部胞內。Forbes 等[14]詳細地描述了二點葉蟬(Macrosteles fascifrons)上、下顎口針的結構。Backus 等[15]對二點葉蟬的感覺系統和取食行為進行了研究,在其口針的內部發現分布有12 根機械感器,在每個上、下顎口針各著生有3 根。
金麗[16]對葉蟬科昆蟲的5 個亞科中8 個屬8 種葉蟬昆蟲口器形態進行了比較,口器特征的差異可以明顯區分各亞科,也可用于屬級單元的鑒別。潘留幸[17]對頭喙亞目包括3 種蠟蟬、8 種葉蟬、1 種角蟬、1 種蟬和4 種沫蟬的昆蟲口器進行了形態學比較研究,發現口器在不同科、亞科、屬及種間均有明顯區別,并結合口器形態對頭喙亞目昆蟲的取食進行了探究。Zhang 等[18]在對假眼小綠葉蟬(Empoasca vitis)的研究中發現,其口器上味覺感器較多。姚甜甜等[19]發現小貫小綠葉蟬(Empoasca onukii)雌、雄成蟲口器上的感器較少,僅下唇的表面分布有毛形和錐形2 種感器,并且在下唇3、4 節上分布有大量網粒體。Zhao 等[20]詳細描述了條沙葉蟬(Psammotettix striatus)口器的形態特征、感器類型、分布特點和口針的連鎖結構等,發現在口器上的感器具有味覺和嗅覺等功能。Zhang 等[21]在對煙草嘎葉蟬(Alobaldia tobae)、電光葉蟬(Maiestas dorsalis)和印度折莖葉蟬(Stirellus indrus)成蟲的比較中發現,3 種葉蟬的上唇和下唇表面均分布有大量的網粒體,且在下唇均分布有毛形感器、錐形感器和腔錐形感器3種感器類型,并在印度折莖葉蟬的上唇表面發現分布有St I 型毛形感器,下唇背面分布有St III 型毛形感器,是在葉蟬亞科昆蟲口器研究中的首次發現。于凱等[22]發現在柳寬突葉蟬(Idiocerus salicis)和黑紋片角葉蟬(Koreocerus koreanus)成蟲的喙端僅分布有大量毛形感器和微毛。蔣佳[23]對小葉蟬亞科的3族8 種小葉蟬進行口器的形態比較得出,不同物種口器表面的精細結構具有一定的種間差異,表皮突起、感器的種類與長寬比在種內趨于一致。
綜合上述研究表明,葉蟬科昆蟲口器上的感器密度與空間分布較相似,但感器的類型、數量及分布位置在不同種間均有差異,其中雌雄間無明顯差異,無雌雄二型現象,在不同屬間的差異較小,在不同族間的差異較大(表1)。
3 葉蟬科昆蟲口器感器分類
口器的感器主要為化學感器,Zacharuk 等[24]對感器形態和功能進行分類:①毛形感器多孔的是嗅覺化學感器,單孔的是溫度機械感器,無孔的是機械、溫濕度感器,極少的是嗅覺化學感器;②刺形感器單孔的是溫度機械感器,無孔的是觸覺感器;③錐形感器單孔的可能是滲透壓感器,其他的與毛形感器一致;④腔錐形感器多孔的是嗅覺化學感器,無孔的是溫濕度感器;⑤瓶形感器的功能與腔錐形感器相同;⑥鐘形感器無孔的是機械感器;⑦板形感器多孔和單孔的可能是嗅覺或味覺化學感器;⑧柱形感器多孔的是味覺感器,無孔的是機械感器。
半翅目昆蟲口器的研究,最早見于植食性和口器形態的研究。研究者也會利用光學和掃描電鏡觀察半翅目昆蟲口器的超微形態結構[25-35]。葉蟬科昆蟲口器的感器在族級及以上的分類階元中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可應用于昆蟲的分類鑒定、生態學和生理學研究中。研究表明,半翅目昆蟲口器的節段、連鎖機制和感覺器官在不同的群體之間是不同的,并且這種差異對分析進食機制和評估系統發育關系很重要[36-43]。
4 小結
國內外學者從葉蟬科昆蟲的外部形態等方面入手,利用掃描電鏡技術對不同葉蟬科昆蟲口器的超微形態進行比較,研究葉蟬科昆蟲的口器結構與其功能的關系,探明葉蟬科昆蟲的口器演化與其寄主植物協同進化的關系,為防治葉蟬科昆蟲的發生及危害提供依據。
大部分葉蟬科昆蟲的種類在國內外的研究還處于盲點,所認識的葉蟬科昆蟲口器的超微形態知識有一定的局限性,阻礙了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因此,有必要盡快開展更多種類葉蟬科昆蟲口器的超微形態研究,以彌補葉蟬科昆蟲口器超微形態研究的空白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