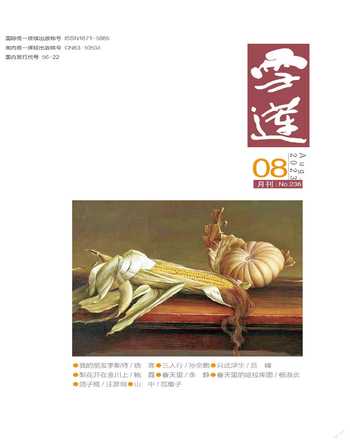春天里
【作者簡介】李靜,女,藏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青海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三十八屆高研班學員,出版散文集《今生有愛》,在《中國作家》《民族文學》《青海湖》等刊物發表作品。
一
當陽光從蔚藍深處傾瀉而下,時而又被如羽毛般游走的流云遮擋些許溫度時,春天便更接近于春天,微溫,微涼,四面風起。
清明之后,從西寧順著一條一直往西的公路走,山巔留下痕跡明顯的雪線,似乎每一座山頭都戴了耀眼的皇冠。天空蔚藍,遠處的山嶺如同一個高傲的、風姿綽約的公主俯視腳下民眾,又如氣勢磅礴的偉丈夫高聳入云。每翻過一個埡口,總會與白頭的神山不期而遇,它們在陽光下泛著晶瑩的光芒,似乎走到哪里,它們就在身旁。它們好像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守護神,用沉默莊嚴的姿態遮擋大風大雨,又將一條大江大河從高山、草甸處引向田間地頭,引向湖泊大海。
在湟源日月鄉遇見牧羊人,他趕著羊群從那條一直往西的公路路過,原本白色的羊毛被染成藍色,遠遠望過去就像是在干旱土地上行走的水珠。它們彳亍前行,在風里找尋食物,逐漸隱入遠處的蒿草中。羊在約翰·摩爾的著作中被稱為天空的孩子。說它們是從文明之前的險峻高山來到平原的。它們的顏色和形態,至今依然像是在天上一樣。它們沒有被賦予捍衛自己的能力,它們唯有的自衛方式便是溫馴與躲避。它們被置于造物序列的最低一級,命定與舍身聯在一起。它們以其悲烈的犧牲,維系著眾生的終極平衡,微弱而不息地生存在世界上。
我們在離天空更近的地方邂逅它們,看它們身著藍色的毛發走遙遠的距離穿過大片的蒿草地,聽到行走時發出“窸窸窣窣”聲音。似乎只是例行公事般遠足,不知終點在何處,也無須過問。牧羊人站在遠處,有著被罡風親吻過的古銅色膚色,他在一天時間里花去大量的時間打量遠處公路上行駛的車輛。他甚至希冀開車的人從車上下來撒一泡尿,跟他搭個訕。
南來北往的車輛難得停下來,也很少有人跑來和他搭訕。更多時候,牧羊人的視野中會出現一只蹦蹦跳跳的野兔,或者四五只蹦蹦跳跳的野兔出現在他的視野里。一時間,屬于他的寂靜世界便呈現出短暫的喧囂。野兔本就有一種令人驚異的適應環境的能力,據說它們在全球的分布比麻雀更為廣泛和普遍。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預言過野兔:“要是沒有兔子和鷓鴣,一個田野還成什么田野呢?它們是最簡單的土生土長的動物,與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質,和樹葉、和土地是最親密的聯盟。看到兔子和鷓鴣跑掉的時候,你不覺得它們是禽獸,它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颯颯的木葉一樣。不管發生怎么樣的革命,兔子和鷓鴣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長的人一樣。不能維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貧瘠無比的。”
看到那么多只敏捷穿行的兔子,很難不想象這片廣闊田野的繁榮。或許在天空中還有一只蒼鷹,正在虎視眈眈地注視著那些看上去敏捷又笨拙的兔子。許多時候,它們快速地俯沖下來,未觸及地面又迅疾飛起。然后再盤旋,再安靜,再俯沖,叼起一只驚恐的兔子展開雙翅掠過蒼茫大地,飛向遠處……但野兔一雙諦聽的比腦袋還長的耳朵,兩條飛奔的比軀干還長的后腿,以及傳統的北方村莊的顏色、魚一樣的寂啞無聲,這些因素賦予它們傳奇色彩和神秘氣氛,就如同這片土地上土生土長的牧羊人一般,行走,找尋食物,繁衍生息。
節氣里的清明萬物生長,皆清潔而明凈,已經有了足夠多的陽光和雨水,植物蠢蠢欲動,顯蓬勃生長之勢,但在高原上,在這個季節肆意活著的唯有風雪。
可是我們卻見到了那么多的野兔,蓬勃之勢如風雪之后的草木。
二
高原上的春天總是緩緩來遲,哪怕節氣已在時間的流轉中到了清明時節,但一場突如其來的風雪卻總是讓倒春寒的氛圍擴大了好幾倍。陌生人置身于那片雪原中的高大坂上,看到滿山滿洼的白雪,草木蕭瑟,不見牛羊。想象會不會有一匹狼跳出來和他對峙;或者兩匹狼,一只假寐,一只伺機攻擊;或者一群狼,頭狼仰著頭嚎叫,引來更多的狼圍觀。他想象自己是蒲松齡筆下的屠夫,幾經努力,突出重圍。
可是湟源日月鄉的田地里卓瑪們戴了鮮紅的頭巾整齊地一字排開。她們穿了厚實的衣服,戴著手套和口罩,和剪刀一樣的風做了分割。此時正是蕨麻收獲的季節,她們小心翼翼地掰開土塊,將嬰兒般嬌嫩的蕨麻從包裹的泥土中喚醒,再放到鐵制的容器中。都說蕨麻有健脾功效,可以輔助治療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因此蕨麻金貴,被稱為高原人生果。人生果的吃法多種多樣,但始終不及“雪山蓋被”。“雪山”即酸奶,酸甜涼爽,營養豐富,猶如草原深處高山之巔上的皚皚白雪,將精心烹煮過的蕨麻撒上白糖浸潤在酥油之中,數日后蕨麻軟糯,清香馥郁。如此,“雪山蓋被”就可以理解雪白絲滑的牦牛酸奶上覆蓋了清香四溢的軟糯蕨麻,最終冰雪和蕨麻融為一體,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美食。蕨麻亦食亦藥,在作為一道美食的同時也發揮它保健作用。炎炎夏日時,只消想一想“雪山蓋被”就會有滿口生津的感覺。

清明時節,蕨麻的主人匍匐在土地上,用身體丈量整塊田地的面積。從早晨到中午,鐵制容器中也只有足以覆蓋住底部的紅褐色蕨麻。可是蕨麻的主人依然從頭巾僅留的一條縫隙里流露出星月般明媚的光芒,她們由衷地說笑,時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旁邊有人提議讓她們唱個山歌,說山嶺里有了山歌就有了靈魂,起初她們不好意思,說這野曲怎么好意思在陌生人前面唱歌。陌生人說我去年已經來過,今年又來了,明年還來,后年還來,還算陌生人嗎?卓瑪嗤嗤地笑,依然不肯開口唱。
遠處有雉雞叫喚,拖得長長的尾音撕開鋪天蓋地的空曠,像裂帛。
“唱兩句吧,你看春天的雉雞都給出信號了。”陌生人說。
卓瑪羞澀,說你轉過身去。卓瑪用右手捂住耳朵,空靈、清澈的聲音順著空曠的田野和山的脊梁延展,然后在某處迂回,讓陌生人想起電影《塔洛》中的拉伊:唱啊唱拉伊,在那高高的山上,鳥兒一對對飛翔,我沒有飛翔的伴兒,你作我飛翔的伴侶吧;唱啊唱拉伊,在茫茫的大地上,知心的情侶一對對,我沒有知心的伴兒,姑娘你來陪伴我吧……
卓瑪的歌聲此起彼伏。
陌生人想唱:“姑娘啊姑娘,熟悉的森林陌生的百靈鳥,雖然相互陌生,聽你鳴叫就熟悉了;姑娘啊姑娘,熟悉的村落,陌生的人兒,哪有注定相識的,說上三句就熟悉了……”
可是陌生人噤若寒蟬,在這高天厚土之上,他的聲音如涂了重金屬般沙啞而不接地氣。他只能唱:“大豆花開哈的白套黑,青豆兒開下的紫葵,朋友不是我常見的客,一年能遇上幾回,吃一個你拾哈的蕨麻,明年了還來哩……”
卓瑪們聽到他的聲音嘻嘻哈哈地笑,陌生人倉惶轉身逃走。
遠處的田地里還有人影晃動,似乎未來要收獲的、沉重的大地——青稞田整整齊齊擺在遼闊的高原大地上,仿佛一塊看不見邊的耀眼金塊;風吹田地,青稞麥芒耳鬢廝磨,搖曳生情,它們竊竊私語;麥浪滾滾,田畦蜿蜒,田主人燃起篝火跳舞,他們飲下青稞釀成的美酒,他們醉倒在帳篷前的篝火旁……都已經在這個季節打好了伏筆。
倉惶離開的陌生人不忘在半山腰撿拾幾粒羊糞蛋,回去丟給花盆里手持盲杖的花兒們。他興奮地說:此去收獲頗豐。
三
屋子里充滿了柔和的光影,墻面上貼滿了獎狀,爐火旺盛,牛糞燃燒的火苗噼噼啪啪地將屋內的溫度維持在二十三度左右。主人又將一整塊餅狀的牛糞掰得四分五裂,并麻利地將牛糞丟盡爐灶里,他看著陌生人靦腆地笑:怕冷著你。
陌生人仿佛浸潤在一場吹面而來的楊柳風里,一切都在這暖色調的木制小屋里更加舒適,清晰。而高原上悠長冬天之后的春天還不肯順著節氣前來,它們似乎因為長途跋涉而氣喘吁吁,隔著窗簾喘著粗氣,砰砰砰地敲打著門窗。
小主人抓幾把麥草喂養西屋的羊兒,羊兒還未被剪去羊毛,看上去像是穿了一件件顏色陳舊的土色裙子,下擺在微風里擺來擺去;女主人熟練地擠著牛奶,隨著她兩只手不停地起伏,乳白奶汁敲打鐵制容器兩側的唰唰聲像極了一場酣暢淋漓的春雨落在青稞寬大的葉片上。
“奶茶喝,趁熱。”男主人的話語總是少之又少,像黃豆一粒一粒往外蹦。
“你也喝,趁熱。我們大家一起喝。”陌生人學著他的樣子。
“你喝,我們天天喝。”男主人說。
這是一種昏昏欲睡的談話。若再沒有進展,在溫暖爐火的攻勢之下,陌生人體內肯定會產生百無聊賴的感覺。
“不然一起喝酒。”陌生人說。
喝了酒的主人喋喋不休,于之前的那個他判若兩人。他悉數村莊的變遷,他左手插著腰站在火爐旁邊,臉色被高原風和酒精浸染得古老而遒勁,右手指著墻上的獎狀:“看見沒,這就是我的驕傲,我這尕娃爭氣,我走在村莊的水泥路上腰桿子很直,我在外勞作的時候一想起他娘倆,我這渾身就有使不完的勁。我羨慕文化人,你住到我們家我很高興,這是我爭取來的,我想著我的尕娃會受到文化人的影響……”
他打開窗戶,聽風聲把鳥雀的聲音帶進來,鳥雀的叫聲時而稀疏,時而密集。它們停留在窗外高大榆樹上如屋內的主人一般喋喋不休,似爭吵,又似辯解,似焦慮,又似歡喜。一群鳥抖動翅膀集體飛走,又一群鳥撲棱棱集體趕來,樹枝時而沉默又時而熱鬧。
他的臉似乎抽離現實,遺忘了自己,被風吹得四散零落。他依然喋喋不休:“你以為我喝醉了嗎?我清醒得很,我這骨子里啊……等一會兒我帶你去看星空,我們這里的星空才是真正的星空,你們城市固然好,但看星星肯定差一些,你好不容易來了一次,得滿足你的所有好奇心。你穿厚些。”
他帶著陌生人穿過兩旁盡是高大楊樹的巷道,他們黑點一樣渺小的身影填滿了整片空曠的高原。在他們之上是明亮而輕盈的天空,一輪上弦月被輕薄如羽毛的細小云朵襯托,星星像極了銀色的小雀斑,一粒粒鑲嵌在深色幕布般的遼闊天空中。陌生人的視野中也有數量較多的燈火顯現,那是當地居民莊廓中的燈火,這溫暖燈火令高原深處的黑暗露出更多的層次。
“春天來了,從這些星宿上就可以看出來,你看北斗七星出現在東北方向的夜空,它的斗柄指向東方。我尕娃喜歡天文,我和他學了一些天文知識,他說他以后上大學就選天文學,你說這天空有多大,我尕娃研究它們會不會很累?”
夜晚寧靜深邃,似乎有大量釋放出的眼和耳,它們不斷閃爍,從黑暗中生出更多新枝和末節,走入厚重的的蒼穹。鄉村夜晚的星空確實不同于城市之上充填著霧、嵐、煙氣、稀薄氣體的天空,這里清光皎皎,它們安靜而清晰地映射在仰望者的眼中。
回來路上他們都被風吹得清醒,望著彼此不好意思又滿心歡喜地笑。
“奶茶喝,趁熱。”坐在沙發上,男主人恢復了之前的樣子。窗外鳥雀已歸于寂靜,換成貓叫聲不絕于耳。
小主人在光下埋頭閱讀,女主人在光下拾掇青稞種子。
春天真的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