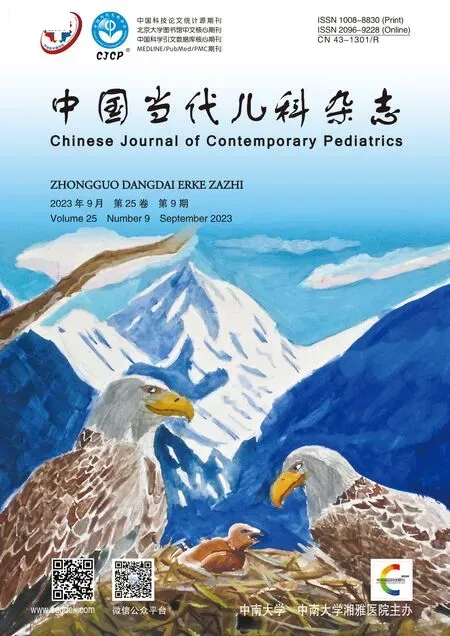兒童吉蘭-巴雷綜合征交感皮膚反應的特點分析
靳梅 劉靜 劉康 趙力搏 趙紫薇 孫素真
(河北省兒童醫(yī)院神經內科/河北省小兒癲癇與神經疾病重點實驗室,河北石家莊 050000)
吉蘭-巴雷綜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是引起兒童急性遲緩性麻痹最常見的原因[1],全球GBS的年發(fā)病率為(1~2)/10萬[2],我國約為0.698/10萬,其中兒童約為0.233/10萬[3]。根據(jù)臨床表現(xiàn)及輔助檢查可分為多種亞型,以急性炎性脫髓鞘性多發(fā)性神經病(acute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hy, AIDP)和急性運動軸突性神經病(acute motor axonal neuropathy, AMAN)為主要亞型,占GBS的70%~90%。兒童GBS的診斷及亞型分類比較困難,特別對于低齡兒童,更加依賴輔助檢查,故神經電生理檢測在兒童GBS的早期診斷、亞型分型及預后評估中意義重大。
研究表明,2/3的GBS患者伴有自主神經功能障礙(autonomic dysfunction, AD)[4],主要表現(xiàn)為心率增快、血壓升高及皮膚出汗異常等,而AD是GBS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甚至導致死亡等嚴重不良后果[5-6],因此我們應重視GBS患者中AD的監(jiān)測,早發(fā)現(xiàn)、早干預。交感皮膚反應(sympathetic skin response, SSR)技術是通過表面電極記錄皮膚發(fā)汗反應進而檢測交感神經小纖維的功能,是一種較為客觀反映自主神經功能的電生理指標[7],目前該技術已應用于多種神經系統(tǒng)疾病診斷、鑒別診斷及預后評估中,如糖尿病周圍神經病[8]、肌萎縮側索硬化[9]、多發(fā)性硬化[10]等。本研究通過總結兒童GBS SSR的變化特征,對比SSR與傳統(tǒng)神經傳導測定對GBS早期診斷的價值,分析SSR與AD及疾病嚴重程度的關系,進而評估其對GBS預后的預測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收集2018年10月—2022年11月在河北省兒童醫(yī)院神經內科就診的GBS或抽動障礙患兒的臨床資料。
GBS組納入標準:(1)年齡≥4歲且≤16歲;(2)符合美國國立神經疾病和卒中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中關于GBS的診斷標準[11]且Brighton分級為2級[12];(3)發(fā)病時間<2周;(4)至少進行2次神經電生理檢測(分別為發(fā)病2周內及4~8周);(5)具有全面且完善的臨床病歷記錄。排除標準:(1)其他導致周圍神經損傷的疾病,如急性起病的慢性炎性脫髓鞘性多發(fā)性神經根周圍神經病,以及遺傳性、代謝性、營養(yǎng)缺乏性及中毒性病因等;(2)合并其他中樞神經系統(tǒng)病變,如多發(fā)性硬化、視神經脊髓炎譜系疾病;(3)合并系統(tǒng)性自身免疫疾病,如甲狀腺功能減退、結締組織病等。
對照組納入標準:(1)年齡≥5歲且≤16歲;(2)平時身體健康,因“發(fā)作性肢體抖動或面部抽搐”就診需行肌電圖檢查,最后確診為抽動障礙者。排除標準:(1)有明顯肢體活動障礙者;(2)神經電生理檢測異常者;(3)頭顱影像學檢查異常者;(4)外周血自身免疫相關抗體檢測陽性者。
本研究通過我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審批號:20230172),并獲得所有患兒或其法定監(jiān)護人的書面知情同意。
1.2 臨床資料
收集GBS組患兒性別、年齡、前驅感染史、起病至疾病高峰時間(由于治療后無患兒病情加重,故疾病高峰時間即入院時間)、面神經麻痹或延髓性麻痹等神經系統(tǒng)癥狀、AD、機械通氣、治療經過(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及血漿置換)、肢體運動功能評分(Hughes評分量表[13],0分:健康;1分:輕微的癥狀和體征,不影響行走,可跑步;2分:無需輔助及支撐能獨立行走10 m以上,但是不能跑;3分:能在輔助支撐下行走10 m以上;4分:輪椅或臥床不起;5分:需要呼吸機輔助呼吸;6分:死亡)、腦脊液蛋白和細胞數(shù)測定。
1.3 GBS病程的界定
根據(jù)發(fā)病后臨床癥狀出現(xiàn)的時間對患兒進行分類[2],急性期為發(fā)病2周內;進展期在發(fā)病2~<4周;恢復期為發(fā)病4~8周。
1.4 SSR測定
采用日本光電肌電誘發(fā)電位儀(型號MEP-2306C)對患兒進行SSR檢測,選用表面盤狀電極,記錄電極置于掌心/足心,參考電極置于掌背/足背,于對側腕部正中神經或脛神經給予電刺激,刺激持續(xù)時間為0.2 ms,電刺激強度為30 mA,刺激間隔30 s,放大器濾波帶寬為0.5~2 000 Hz,靈敏度為0.1~1.0 mV/cm,分析時間為5 s,檢測指標包括起始潛伏期、波峰(N波)潛伏期及波谷(P波)潛伏期。異常判斷標準[10]:波形分化不良或各波潛伏期超過本實驗室對照組的97.5%。
1.5 常規(guī)神經傳導檢測
具體檢測項目包括:(1)運動神經(雙側正中神經、尺神經、脛神經、腓總神經)傳導的末端潛伏期、運動傳導速度、近端/遠端復合肌肉動作電位波幅;(2)感覺神經(雙側正中神經、尺神經、腓腸神經、腓淺神經)傳導的感覺神經動作電位波幅及感覺傳導速度;(3)F波出現(xiàn)率及最短潛伏期。上述指標異常情況均參考Hughes電生理診斷標準[14]進行判斷。
1.6 SSR、常規(guī)神經傳導單一和聯(lián)合應用的可靠性評估
以Brighton分級為診斷GBS的金標準[12],計算SSR、常規(guī)神經傳導單獨和聯(lián)合應用診斷GBS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準確度、與金標準的一致性。其中,靈敏度=真陽性/(真陽性+假陰性)×100%,特異度=真陰性/(真陰性+假陽性)×100%,陽性預測值=真陽性/(真陽性+假陽性)×100%,陰性預測值=真陰性/(真陰性+假陰性)×100%,準確度=(真陽性+真陰性)/樣本量×100%。采用Kappa值(κ值)判斷其與金標準的一致性,κ值越高表示一致性越好,一般認為κ值0.40~0.75為中、高度一致,≥0.75為一致性極好,≤0.40為一致性差[15]。
1.7 短期及長期預后評估
GBS起病1個月(短期)及起病6個月(長期)時采用Hughes評分量表進行評定[13],≤2分(即可以獨立行走)為預后良好,>2分為預后不良。
1.8 統(tǒng)計學分析
采用SPSS 18.0統(tǒng)計學軟件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tài)分布的以均數(shù)±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兩樣本t檢驗;非正態(tài)分布的以中位數(shù)(四分位數(shù)間距)[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計數(shù)資料以例數(shù)和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以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GBS組與對照組SSR結果比較
GBS組25例,年齡4~15歲;對照組30例,年齡5~15歲。兩組年齡、性別、體重指數(shù)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掌心及足心均可引出SSR波形,而GBS組急性期8例(32%)掌心及足心均未引出SSR波形,3例(12%)掌心及足心SSR潛伏期(包括起始、N波及P波)均延長,7例(28%)僅足心SSR潛伏期(包括起始、N波及P波)延長。GBS患兒急性期足心SSR起始潛伏期、N波潛伏期長于對照組(P<0.05),掌心SSR潛伏期(包括起始、N波及P波)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GBS組急性期SSR異常率(至少1個掌心或足心SSR異常)高于對照組[72%(18/25)vs 0(0/30),χ2=32.108,P<0.001]。GBS組進展期SSR表現(xiàn)為波形從未引出至潛伏期延長,或潛伏期逐漸縮短。GBS組恢復期SSR表現(xiàn)為潛伏期進一步縮短,直至潛伏期正常。見圖1。

圖1 GBS患兒SSR動態(tài)演變

表1 GBS組與對照組的基本資料及急性期SSR結果比較
25例GBS患兒中,19例(76%)存在前驅感染史,均為上呼吸道感染;6例(24%)需要機械通氣;17例(68%)伴有AD,其中竇性心動過速9例,高血壓2例,排尿障礙4例,皮膚出汗異常6例。18例SSR測定異常患兒中,13例(72%)伴有AD,5例(28%)不伴AD。4例(16%)伴有AD但SSR測定正常。
2.2 急性期SSR、常規(guī)神經傳導單一和聯(lián)合應用診斷GBS的可靠性評估結果
單一SSR、常規(guī)神經傳導早期診斷GBS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和準確度(κ值分別為0.74、0.66)與Brighton分級之間一致性較高。聯(lián)合檢測(SSR+常規(guī)神經傳導)早期診斷GBS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和準確度(κ值為0.85)與Brighton分級之間一致性極好,靈敏度、準確度相比單一SSR或常規(guī)神經傳導測定均有提高。見表2。

表2 SSR、常規(guī)神經傳導單一和聯(lián)合應用早期診斷GBS患兒的可靠性評估結果
GBS患兒恢復期SSR異常6例(24%),常規(guī)神經傳導異常17例(68%),較急性期SSR及常規(guī)神經傳導異常比較,12例患兒SSR恢復正常,新增1例常規(guī)神經傳導異常。
2.3 GBS患兒SSR測定與疾病嚴重程度、電生理亞型及預后的關系
SSR異常GBS患兒在疾病高峰、發(fā)病1個月及發(fā)病6個月時Hughes評分與SSR正常GBS患兒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21例AIDP患兒中,SSR異常16例(76%);4例AMAN患兒中,SSR異常2例(50%)。發(fā)病1個月時預后良好與不良分別為18例(72%)和7例(28%),其中預后不良的GBS患兒SSR測定全部異常,見表3。發(fā)病6個月時,25例(100%)GBS患兒全部預后良好。

表3 SSR正常與異常GBS患兒的臨床資料比較
3 討論
GBS是一類自身免疫介導的急性炎性周圍神經譜系疾病,臨床特征主要表現(xiàn)為肢體無力,伴或不伴感覺障礙,目前存在多種亞型,以AIDP和AMAN為主[16]。兒童GBS早期診斷相對困難,更加依賴輔助檢查,如神經電生理及腦脊液測定,但有時在疾病早期,電生理指標正常且腦脊液無蛋白-細胞分離時,積極尋找一種敏感且客觀的標志物,一是能更早期識別GBS,二是能準確預測GBS預后,是臨床實際工作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SSR是通過皮膚發(fā)汗反應檢測交感節(jié)后C類小纖維的功能,進而反映自主神經的功能狀態(tài)[17]。國內外有關SSR在成人GBS中的研究表明,SSR異常表現(xiàn)以波形消失為主,起始潛伏期延長伴或不伴波幅減低[18-19]。本研究中GBS患兒急性期SSR異常主要表現(xiàn)為波形消失或起始潛伏期延長,SSR異常率高于對照組,與以往研究報道[18-19]相一致。本研究納入的抽動障礙患兒均可引出SSR,波形分化良好,掌心及足心起始潛伏期中位數(shù)分別為1.21 s及1.69 s,與國內外研究報道的健康兒童SSR起始潛伏期平均值(掌心1.15~1.28 s;足心1.48~1.72 s)[20-21]大體相似。考慮到SSR波幅在機體重復連續(xù)刺激后會逐漸下降,且變異度較大[22-23],故本研究未將波幅納入分析。
約66.7% GBS患者合并AD,主要表現(xiàn)為心血管功能障礙(心率增快、高血壓或低血壓)、胃腸道功能障礙(腸梗阻、便秘)及皮膚出汗異常等[4],且GBS病死率為3%~10%,主要為心血管功能障礙或呼吸衰竭所致[11,24]。鑒于GBS患者合并AD的發(fā)病率及病死率的臨床風險較高,在GBS整個病程中識別AD意義重大。本研究中,68%GBS患兒合并AD,主要表現(xiàn)為心動過速或高血壓,與以往研究[4]一致;52%(13/25)GBS患兒同時存在AD合并SSR測定異常,20%(5/25)患兒僅表現(xiàn)為SSR測定異常而無AD的臨床表現(xiàn),即為亞臨床AD。因此,SSR測定異常提示臨床出現(xiàn)AD的風險較高,SSR可成為早期識別GBS患兒合并AD的電生理標志物。
常規(guī)神經傳導測定及腦脊液蛋白-細胞分離對早期診斷GBS至關重要[25]。本研究得出聯(lián)合檢測(SSR+常規(guī)神經傳導)早期診斷GBS的靈敏度及準確度相比單一SSR或常規(guī)神經傳導測定均有所提高,提示SSR對于早期輔助診斷GBS,尤其對于病程早期常規(guī)神經傳導測定正常的患兒來說有一定意義。同時,本研究通過動態(tài)觀察GBS患兒的SSR及常規(guī)神經傳導測定結果,得出恢復期SSR異常情況低于常規(guī)神經傳導,表明自主神經小纖維恢復早于感覺、運動神經大纖維,分析原因與神經纖維超微組織結構有關,自主神經由直徑小的薄髓神經纖維組成,而感覺、運動周圍神經由直徑大的有髓神經纖維組成,周圍神經髓鞘和軸索再生是一個自然修復過程,直徑大的神經纖維需要更長時間完成修復。因此,SSR也可作為一種客觀的電生理學標志物監(jiān)測疾病治療情況。
一項關于兒童GBS AD的隊列研究顯示,AD的存在與疾病嚴重程度及預后顯著相關[26]。本研究中,SSR異常GBS患兒疾病嚴重程度、短期預后與SSR正常GBS患兒比較雖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但6例行機械通氣的患兒SSR測定均異常,疾病較重(需機械通氣)的構成比較高(33% vs 0),且短期預后不良的GBS患兒SSR測定均異常。SSR測定與電生理亞型的相關性各學者研究結果不一致,有的學者指出SSR異常提示脫髓鞘病變[18],有的學者指出SSR異常與軸索病變相關[27]。本研究中AIDP患兒SSR異常比例(76%)較AMAN患兒(50%)偏高,因此SSR測定對GBS患兒的電生理分型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綜上所述,GBS患兒常合并AD,SSR技術可以早期輔助診斷GBS、監(jiān)測疾病治療情況,對于評估疾病嚴重程度及短期預后也有一定幫助。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