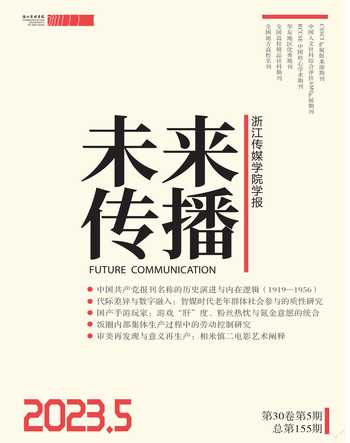視聽新媒體的“數字吸引力”美學建構與傳播
王珺
摘 要:以互聯網技術和新興傳播媒介為技術基礎的視聽新媒體,呈現出新一輪的數字影像美學建構與傳播變革。立足技術美學視域,視聽新媒體的“數字吸引力”主要體現在:優質影像與劣質影像構成的影像奇觀、多屏視窗產生的媒介展示效應與以用戶為中心營造的多重感知幻覺機制。視聽新媒體的“數字吸引力”傳播呈現出具身性、自反性、瞬時性與交易性,映射了“后電影”時代數字影像傳播借助媒介技術深入用戶感知結構的情感自覺、技術邏輯與消費動因。
關鍵詞:視聽新媒體;“數字吸引力”;媒介技術
中圖分類號:G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3)05-0052-07
視聽新媒體(audio-visual new media),是以互聯網技術和具有互動性的新興傳播媒介為技術基礎,以網絡視聽節目為主要內容形態、以網絡媒體和移動媒體為主傳播陣地的各類數字視頻影像。伴隨5G網絡的全面聯通、智能終端的快速發展、虛擬現實的技術加持、大數據云計算的深度開發,視聽新技術在內容生產、媒體建設、用戶體驗、融合服務等各方面不斷創新,持續賦能視聽新媒體行業高質量發展。媒介技術已成為視聽新媒體內容升級與形式創新的源動力與助推器。立足媒介技術,分析科技注入下的視聽新媒體的美學呈現和意義表達,把握視聽新媒體“技術+藝術”的傳播特質,透視視聽新媒體傳播背后的媒介消費,符合當下媒體生態發展的趨勢。本文在技術美學(the aesthetics of technology)視域下,引入新西蘭學者列昂·葛瑞維奇(Leon Gurevitch)“數字吸引力”(digital attraction)這一概念,從影像奇觀、媒介展示與用戶身體三方面分析視聽新媒體的“數字吸引力”美學建構與傳播。
一、“數字吸引力”概念溯源
湯姆·甘寧(Tom Gtunming,亦翻譯為湯姆·岡寧)于1986年發表了兩篇重要文章,提出了“吸引力電影”概念,分別是《吸引力電影:早期電影,它的觀眾和先鋒派》以及與安德烈·戈德羅合作撰寫的《早期的電影:對電影史的一次挑戰》。這兩篇文章奠定了“吸引力電影”的理論基礎,并引發電影理論界的一次“刷新”(reload)。甘寧采用“吸引力電影”來概括早期電影實踐,“我相信盧米埃爾和梅里愛(以及許多1906年之前的電影人)的影片所建立的與觀眾的關系有著共同的基礎,卻有別于1906年之后的敘事電影所建立的主要觀眾關系。我將把這種早期的電影觀念,稱為‘吸引力電影。”[1]同時指出,“吸引力電影是直接訴諸觀眾的注意力,通過令人興奮的奇觀——一個獨特的事件,無論虛構還是實錄,本身就很有趣——激起視覺上的好奇心,提供快感……強化了電影的新奇性……吸引力電影很少花費精力去創造具有心理動機或個性特征的人物。它利用虛構或非虛構的吸引力,將能量向外傾注于得到認可的觀眾,而不是向內著力于經典敘事中實質上以人物為基礎的情境。”[1](62)在他后續的研究中,又指出“吸引力電影”是“把注意力轉向展覽與顯示的電影”,以及“特別指涉著觀眾接受學的某種角度和方法。”[2]
新西蘭學者列昂·葛瑞維奇在甘寧的基礎上,提出了“數字吸引力”這一概念。“數字吸引力”是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等新興媒介技術的產物,“它涉及當代視聽文化中最根本的電影性問題”[3]。主要包括三方面的論述:一是認為“數字吸引力”是當下數字影像敘事與奇觀的再平衡,“當代數字效應則超越了簡單的確認。數字吸引力標志著敘事和吸引力之間的再平衡,使兩者并非在爭斗中此消彼長和(或)一方支配另一方。”[3](86)二是“數字吸引力”是一種融合了技術、文本、美學與經濟相互交織的復雜系統,并非是單一的媒介本體論。三是“數字吸引力”具有自我指涉性,成為一種強有力的促銷招數。“這種吸引力在美學上不是電影或廣告所獨有……將數字吸引力視為橫跨多種視聽經濟來實現促推價值。”[4]
綜上,從甘寧“吸引力電影”到葛瑞維奇的“數字吸引力”,可以看出吸引力是媒體藝術的底色與特質,吸引力不僅在主觀上塑造了觀眾的審美品位,而且在客觀上提出了求新、求變的媒體進化觀。本文借用“數字吸引力”的概念,沿用技術—藝術—文化的思考邏輯,將視聽新媒體置于媒介技術與媒介表征體系中加以審視,分析其美學建構與傳播。
二、視聽新媒體的“數字吸引力”建構
甘寧對“吸引力電影”的分析提供了理解“數字吸引力”要素的三個向度:一是影像內容的奇觀性,帶有“裸露癖”的“異國情調”。二是媒介展示性,“通過各種形式手段,使得影像突如其來,造成一種直接沖向觀眾的動態畫面……是一次展覽主義者的呈現。”[5]三是“吸引力電影”的研究核心是對電影觀眾接受學的本質討論,從傳統古典視覺的“愉悅美學”到“驚詫美學”的視覺機制轉向,強調了觀眾“身體”知覺與體驗的重要性。視聽新媒體是媒介傳播技術革新的產物,計算機網絡技術、虛擬現實技術、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視聽新媒體的媒體形態、視聽語言、美學表達產生迭代性影響,成為視聽新媒體藝術創作不斷創新的引擎。
(一)影像奇觀的吸引力
伴隨媒介技術的成熟,視聽新媒體開啟了“高新視頻”的探索之路。“發展‘高格式‘新概念的高新視頻業務將成為5G環境下的文化消費主流,‘高格式是指融合了4K/ 8K、3D、高幀率(HFR)、高動態范圍(HDR)、廣色域(WCG)、沉浸式聲音(immersive sound)等高新技術格式的影像內容。‘新概念是指具有新奇的影像語言和視覺體驗的創新應用場景,能夠引發觀眾興趣并促使其產生消費的概念。高新視頻是先進技術與應用場景的深度融合,將催生更多高新的視聽業態,為觀眾帶來全新的視聽體驗。”[6]利用數字技術創造的令人炫目的視覺特效(visual effects,簡稱VFX)已成為視聽新媒體創作的慣例。例如美國HBO電視臺出品的《權力的游戲》(Game of Thrones),堪稱視覺特效典范,該劇在6年間,先后獲得5次艾美獎視覺特效獎,以及美國視覺特效協會眾多獎項。劇中廣闊迷人的維斯特洛大陸、絕境長城、宏偉華麗的城堡以及精彩絕倫的戰爭場面,創造出震撼觀眾的視覺饕餮。視覺特效,一般不關注故事情節,而是將注意力放在鏡頭畫面中,旨在創造出生活中不存在的空間與視覺形象,提升視聽效果與質感,從而激發觀眾的視覺滿足感。同時,視覺特效絕非單純模仿,更為強調展現影像的復雜性,企圖重現人類視覺的靈活性,完成數字影像對觀眾持續吸引力的構建。例如,高幀率的特寫鏡頭,演員微表情被放大,演員的面孔成為觸發觀眾共情的開關,用制造近乎親密距離的方式邀請觀眾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縮小觀眾與人物的情感隔閡,形成非常有趣而獨特的數字吸引力。再如抖音推出的“變身漫畫”特效,只需輕輕一揮手就可以生成自己的實時漫畫形象,引來無數用戶爭相體驗。開發應用便利性的特效功能已成為短視頻平臺刺激用戶生產與消費短視頻的重要手段。
相較于視覺特效打造的“優質影像”(rich image),“劣質影像”(poor image)【“劣質影像”由德國藝術家黑特·史德耶爾(Hito Steyerl)在2009年發表的《為劣質影像辯護》( 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2009)中提出。文章對“劣質影像”展開文化思辨,認為“劣質影像”是對既定電影體制的背離,具備強烈的文化抵抗功能。】則成為視聽新媒體異質性的影像奇觀。以網絡視聽內容為主要形態的視聽新媒體是一種數據壓縮影像,它內在包含了成像、轉碼、封裝、存儲、傳輸等諸多環節。在編碼—解碼過程中,數字影像因為壓縮會對視頻畫質產生影響,退化為分辨率低、解析度差的劣質影像。同時,伴隨傳播時空與傳播終端的多元化,視頻化生存已成為移動時代日常生活媒介化的重要表達,這也是“劣質影像”產生的社會背景。視頻平臺也會向用戶提供多種像素版本,如流暢、高清、超清、藍光和4K等,以滿足用戶不同網絡流量的需求。與高規格、高逼真、高奇幻的“優質影像”不同,劣質影像以模糊不清、分辨率低激起用戶想看清楚的沖動,誘發用戶積極猜測影像內容。例如,短視頻、網絡視聽節目中插入的GIF文件,是由一組高度壓縮的圖像排列而成的無聲影像。由于傳輸需求,文件的分辨率較低,其質感和紋理依靠數字模擬完成,較低的幀數無法提供完整的敘事和多感官的視聽體驗,但因粗糙模糊的視聽語言、非專業的拍攝技法,呈現出紀實影像般的真實性,提供了一種曖昧的媒介經驗與吸引力,誘惑觀眾介入作品。
(二)媒介展示的吸引力
甘寧認為,“數字吸引力”是通過對視覺特性的操控以及直接地“展覽與顯示(display)”,激起觀眾視覺上的好奇心,提供視覺快感與驚詫體驗。媒介的“展示”行動構成一種原始吸引力。
隨著5G技術與智能終端的發展,“第二屏”、多屏互動成為視聽新媒體最常見的媒介使用方式。多屏視窗重塑了傳統屏幕的視覺機制,不再遵循透視,不再具有固定的視覺滅點,屏幕中的屏幕、畫面中的畫面構成新的媒介展示樣態與吸引力。用戶可以進行多任務操作,可以播放視頻,可以社交媒體,可以搜索信息,所有操作在同一屏幕內同步呈現,構成視窗的重疊與并置,繼而形成屏幕內多元復雜的信息流。用戶在不同認知活動間的切換,會產生來自于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下對多元信息流的捕捉與反應的控制快感與樂趣,產生不一樣的媒介體驗快感。
另外,各類視聽新媒體設備作為一種裝置形成吸引力。正如甘寧所言:“早期的觀眾去放映所,是去看被展示的機器……而不是去欣賞影片。”[1](62)從便攜式穿戴智能設備如虛擬眼鏡、手套、手環到位于客廳的智能電視終端,以及公共場所巨大的智能投屏等,這些裝置本身帶來了“戀物”式的吸引力。“觀眾對VR設備從180度到360度乃至720度的轉化能力的震驚,與百年前的觀眾一樣,都是對媒介機械性的震驚。”[7]
(三)媒介互動的吸引力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已從專門的技術轉化為文化的融合器,成為一種能調和所有藝術文化產物的形式。基于互聯網信息技術展開傳播的視聽新媒體,互動更是處于關鍵位置的核心功能。
與傳統視聽媒體所不同的是,視聽新媒體從起步就具備了互動屬性。視聽新媒體的互動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人機交互;二是社交互動。人機交互,指人與媒介的物理性互動,比如觸屏、滑屏、鼠標點擊等。此外,互動敘事成為視聽新媒體重要的數字敘事形態。在互動視頻、互動紀錄片、互動電影和互動電視劇中,用戶通過對角色言行的決策選擇來影響后續文本情節的走向,從而引發情節分岔與多重結局。“互動敘事允許用戶通過角色扮演、人機對話等方式參與敘事,改變敘事進程或結果,以增強他們的參與體驗。”[8]不同于電視機、廣播等線性封閉、功能單一的傳統媒介,視聽新媒體充分利用各種智能終端和計算機軟件,通過觸摸、視線追蹤、人工語音等途徑為用戶提供訪問、選擇、決策等服務,進而參與文本敘事,引發審美愉悅。“在新的交互敘事模式下切實地參與敘事,以協同敘事的方式共同建構故事世界。”[9]例如奧迪的微電影廣告,上演周杰倫與方文山的跨界互動秀,該互動視頻有兩個屏幕分別呈現,用戶在觀看時只需要拖動屏幕中間的中軸線就可以看到不同劇情。社交互動,包括用戶與文本互動、用戶與用戶互動。視聽新媒體在用戶與文本互動領域不斷進行創新,從最早的評論、留言、轉發,到點贊、彈幕、分享,再到當下的打賞、同框。以彈幕為例。相較于精英主義/權威專家的文藝批評,彈幕的即時評論開拓了另一番空間。致敬、諷刺、站隊、批評成為彈幕的主要內容,評論的內容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戶的出場與參與,也就是費斯克所說的“生產者式文本”,賦予用戶書寫的權利和自由。彈幕的即時性與交互性,也會激起用戶與用戶的二次互動,引發社交愉悅。
(四)媒介幻覺的吸引力
視聽藝術都是通過制造幻覺引發觀眾的好奇心。在數字技術、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支持下,視聽新媒體的創作拓展了以視覺為中心的電影式幻覺機制,提出多重感知的幻覺機制。通過各種媒介技術,視聽新媒體以多種方式加強用戶審美感官的聚合應用,除了視覺和聽覺的不斷升級,還將觸覺、嗅覺乃至運動感、力覺等感知全面納入審美活動視域。例如,VR技術并不是以視覺逼真作為單一維度,而是追求多種維度的逼真感知。立體音效、虛擬現實中觸覺的開發、帶有力量反饋的游戲操縱桿、虛擬設施中的震動座椅等都彰顯VR技術對于塑造多重感知機制的嘗試。有學者將VR技術表達為一種“同理心媒介”或“同理心機器”(empathy medium/machine),旨在說明VR技術填平了觀眾與銀幕之間的溝壑,建立用戶與他者的情感和肉身聯系。“這種以體驗者的全感機制與他者所思所感無間地浸融在一起的經驗,使我們得以重新認識自然和人類,以同理同情之心重建自我和他者、自我與世間萬物的關系。”[10]總體而言,在媒介技術的加持下視聽多媒體追求多重感知,強調多重感官的投入,極力詢喚用戶審美的主體性與自覺性。
三、視聽新媒體的“數字吸引力”傳播特質
“數字吸引力”是一種策略性的美學建構,利用媒介技術將視聽新媒體從傳統影視美學中解放出來,引發數字時代基于吸引力機制生成的美學經驗,呈現出視覺、心理、情感與消費維度的視聽經驗革新。與此同時,媒介技術也推動了視聽新媒體的傳播變革,不僅增大了視聽新媒體的時代影響力,也彰顯出“后電影”時代數字影像傳播的新特質。
(一)“數字吸引力”傳播的自反性
追溯電影史,影像奇觀從電影誕生就一直存在。相較于膠片時代的影像奇觀,數字影像的視覺特效更為無所不能。在“后電影”視域下,視聽新媒體的“數字吸引力”傳播涌現媒介技術的自反性特征,即:在營造奇觀的基礎上,又解構了幻覺機制,讓觀眾介入影像之中,成為影像空間中的行動者和體驗者,繼而重塑用戶與影像之間的互動關系。
現階段的視覺特效所營造的炫目特技,以及高分辨率、高幀率帶來的過載的視覺信息,使得視聽新媒體影像在解析度和速率上超越了自然感知的閾值,遠遠超出觀眾感觀機能的接收和反應速度。對于特效場面,觀眾并非直接感知,而是根據經驗大致推斷出影像的事實,作為假定的認知和敘事要素,繼而保證看懂影像。因此,觀影樂趣從敘事認同轉向逼真、沉浸的感官體驗。例如《愛,死亡和機器人》(第三季)(Love, Death & Robots,Season 3)中的壓軸之作《吉巴羅》,通過真人實景拍攝與后期CG渲染出瑰麗詭異、魔幻真實的視覺風格,其女妖夸張的舞蹈動作與繁復斑斕的金屬配飾涌現出現實生活無法觸及的詭譎之美,給觀眾帶來最直觀的視覺驚艷與聽覺震撼。全片無任何對話,因此除了強烈的視覺畫面,該片的聲音設計成為點睛之筆。全片在耳聾騎士視角下的聲音空間(呼吸聲、心跳聲)與整體環境的嘈雜聲(女妖的嘶吼聲、瀑布的水聲、打斗聲)之間不斷切換,呈現出360度環繞、直擊人心的聲音演繹,帶給觀眾無處躲藏的直面沖擊。
劣質影像的出現不僅暴露了自身的媒介物質形態,而且展現了影像技術架構和生成過程,讓觀眾直面數字影像背后的物質形態和數字技術。例如直播中由于信號不穩定產生的遲滯閃屏的畫面效果、監控設備拍攝的分辨率較低的畫面,以及視聽內容中作為特殊情節使用的低清、模糊影像等。這些模糊的影子或塊狀的像素團,讓觀眾看到影像像素的在場,繼而彌散了影像建構的主體,打破敘事幻覺與影像認同。“劣質影像對符號流通的適應及快速傳輸散播的流通方式使它成為真正大眾化生產的影像,而這種動態讀寫的傳播過程也讓劣質影像不斷確證自身。”[11]
桌面電影、互動電影、視頻游戲、直播等新興的視聽新媒體,讓觀眾以“參與”的方式進入影像世界,點擊、滑屏、人工語音等將虛擬影像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互連接。想象世界不斷被現實操作所打斷,形成一種全新的幻覺機制,即“詢喚并否認”。也就是,在傳統敘事影像中,影像的吸引力更多來自對于影像敘事詢喚產生的回應與認同,而當下建立在媒介技術支持上的視聽新媒體營造的“詢喚”,遭遇了由技術操作形成的對“詢喚”的“否認”與粉碎,映射出“數字吸引力”傳播的自反性。以桌面電影為例。“桌面電影是完全或大部分在電腦、手機等數字屏幕上展開的視聽敘事,使用各種程序、網站作為全部或部分敘事的載體。”[12]例如《網絡謎蹤》(Searching,2018)、《解除好友》系列(Unfriended),其敘事都是通過呈現操縱不同程序生成和改造的影像完成,真實展現了觀眾熟悉的媒介經驗。桌面電影從數字操控和動態讀取兩方面展示出其媒介自反性:一方面呈現數字媒介材質,另一方面展現數字媒介運行的過程,通過對媒介與媒介操作的再現與還原進行“自反性”的媒介化展現。
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在分析屏幕與身體的關系時指出,伴隨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身體發生了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身體和影像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全新的關系。在虛擬現實體驗中的觀眾需要在現實空間中發生動作,才能體驗到虛擬空間中的行動。即,用戶在虛擬世界中想“拈花一笑”,用戶就需要在真實的物理空間中同步發生“拈花”的動作。這種同步性,提供給用戶多重的感官和情感體驗,營造一種現場感與沉浸感。另一方面,“虛擬現實對于身體的禁錮達到了前所唯有的程度。”[13]簡單來說,用戶的身體被虛擬設備所“限制”,用戶需要連接設備(攜帶/穿戴設備),所以馬諾維奇將用戶的身體比喻成“鼠標”/“巨大的操縱桿”。由此,用戶在體驗虛擬現實技術營造的奇觀當下,又從多重意義上破壞了媒介技術構建的幻象,用戶在亦實亦虛、亦真亦假的認同機制間徘徊。
(二)“數字吸引力”傳播的具身性
伴隨智能終端、可穿戴設備的普及,媒介技術與人的身體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媒介的呈現內容和呈現方式默認為身體感知的延伸。正如葛瑞威奇所言,“數字吸引力”“標志這一種連續性的美學,其中的空間、技術邏輯、影像功能目的和吸引力構造都是一樣的:讓觀眾參與到影像中。”[4](373)
身體一直是美學關注的對象,同時也在媒介研究的歷史譜系中若隱若現。從柏拉圖的身心二分開始,身體一直被心/精神所抑制,認為是初級且“不具備可靠性”。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不斷解構二元論的身體認識,賦予身體更為廣泛的內涵。福柯認為“靈魂是身體的監獄”,身體是被規勸的對象;梅洛-龐蒂在《感知現象學》中進行了身體首要性的系統論證,認為身體是人類接觸、介入、認知世界的樞紐。身體不僅僅是審美的客體,更是審美的捕捉器,是一種可以主動與媒介進行交流、互動的中介。“身體在審美互動中表現出與其他傳播媒介完全不同的深度體驗感,感官的獨立激發和連鎖反應都空前強烈,整個感知系統進行著相應的重新整合和真實調動。”[14]身體在媒介研究中也經歷了由“離身”到“具身”的轉變。尤其伴隨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身體更是成為學界討論的重點。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的羅德尼·布魯克斯(Rodney Brooks)明確指出:“人工智能必須有身體的介入,這是一種具身化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15]
時至今日,視聽新媒體已經利用最新數字技術創造出不可思議的視聽作品,不僅帶給觀眾新奇意外又高度喚醒的審美體驗,而且以多種方式加強受眾審美感官的聚合應用和使用體驗。以VR、AR、MR為代表的虛擬現實技術以及可穿戴設備等智能應用,通過模擬和加強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感官體驗,讓視聽新媒體作品復原、延伸和強化人類身體最原始的感官體驗,激發出更多身體反應,強化用戶的主體性與自覺性,用身體來重新確定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例如觸屏、語音指令、手勢控制、動作指令等媒體互動行為,利用生理體驗激活心理感覺,從而對作品產生“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具身”(embodiment),可理解為“在投入到某活動時,人的身、心、物以及環境無分別地、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以致力于該活動的操持。具身既是我們的身體向周圍世界‘外化,也是周圍世界向我們身體的‘內化。” [16]
“具身”是將媒體嵌入人之中,強調媒體成為人的組成部分,成為身體的“幻肢”。VR技術,利用3D技術、立體顯示技術、跟蹤技術、力覺反饋等仿真技術,將視覺、聽覺、觸覺等置入虛擬空間中,模糊/消解現實與虛擬的界限,“身體”從現實世界“缺場”轉為虛擬空間中的“在場”,用戶的感知是基于角色與自身的具身性活動。VR影像藝術突破了影視藝術再現式、媒介化的傳播模式,賦予用戶參與權,成為解放用戶身體的文化實踐的手段。隨著5G技術的完善與商用化,VR智能設備的便攜化,以及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等技術的賦能,VR影像的“虛擬化身”知覺系統將進一步強化身體的在場與肉體的知覺,提供用戶身、心、物以及環境融為一體的具身傳播。
(三)“數字吸引力”傳播的瞬時性
甘寧認為“吸引力電影”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方式展現時間。“實際上,吸引力電影有一個基本的時間性,根植于展示活動中的在場/缺席(Presence/absence)的更替。在這種現實時態的緊張的形式里,吸引力以一種‘它在這里!快看的即時性得以展示。”[17]這種“在場/缺席”的更替模式下,懸置敘事時間的展現動作,就構成了吸引力瞬時性的奇觀時刻。“這一突如其來的感官驚奇時刻,并無任何推進敘事的作用,它所展現的僅僅是飄浮在懸疑故事線之外的斷裂的時間。”[18]
隨著移動技術的發展,視聽新媒體傳播呈現移動化與微化趨勢。以短視頻、微電影、微劇、微綜藝、微紀錄片為代表的“微”型媒體形態是在碎片化的時間、不斷轉換的空間與場景中完成傳播。以短視頻為例,短視頻的15秒時間設定,符合年輕用戶注意力最能集中的一個時長。15秒之內,為了讓用戶保持注意力,需要不斷用瞬時性的影像奇觀刺激用戶。短視頻呈現各種極具視覺誘惑和精神震驚的搞笑、夸張、雜耍的生活景觀,以一系列令人驚異的瞬間直接吸引用戶的感官、調動用戶的情緒。如,“丁真一笑”“孤勇者小學生”、萌寵瞬間等爆款視頻。短視頻用戶與吸引力電影的觀眾在觀看體驗和感受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驚奇好玩,尋求瞬間的刺激。同時,短視頻受限于時長,難以進行較為完整的故事敘事,大多為某一場景的真實記錄或擺拍,是一種對生活片段或者戲劇情境的呈現與再現。因此,短視頻傳播并不依賴敘事的魔力,更強調以驚奇、刺激的畫面直接吸引用戶,以一種精悍的瞬時景觀來留住用戶碎片化的時間。“相較于長視頻,短視頻很難有復雜的架構、縝密的思考與細致的描摹,但它更能夠隨機并準確抓住世界的‘瞬間……在短視頻的時代里,‘瞬間的記錄已經成為了大眾的慣常表達。”[19]
(四)“數字吸引力”傳播的交易性
列昂·葛瑞維奇指出“數字吸引力”具有“促推價值”,并提出“交易電影”(transaction film)這一概念,用來說明“數字吸引力”在當下數字影像生產與消費領域中的重要性。具體說來,“數字吸引力”傳播的交易性表現為:一是構成“數字吸引力”的影像成為營銷推廣的重要文本,承擔了向觀眾和融資商“兜售”影片的功能。這種情況常見于各類視聽內容的宣發物料。不論是《權力的游戲》(Game of Thrones)、《黑鏡》(Black Mirror)、《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等國外熱播網劇,還是國內熱播的網劇,如《河神》(2017)、《蒼蘭訣》(2022),其預告片基本都由視覺特效構成,用最炫目、最驚詫、最感官刺激的視覺特效推廣作品。還有展現技術迷思的互動視頻、VR視頻,以展現作品的科技感、未來感、體驗感為營銷內容,吸引觀眾消費與傳播。如“智慧化”“科技化”成為2022北京冬奧會傳播的關鍵詞。在央視頻平臺上,眾多視頻都是以媒介技術為看點介紹賽事,如“8K國際公用信號直播、7個8K機位、A6 轉播車”“VR看直播”“獵豹”【A6車是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的具備獨立三維聲監聽音控室的轉播車;獵豹為總臺自主研發的超高速4K軌道攝像機系統。】都是短視頻傳播的重中之重。二是“數字吸引力”可助推跨媒體傳播。典型案例便是各類視聽作品的二次創作。例如上文提到的《吉巴羅》,用炸裂 “數字吸引力”震撼了觀眾的雙眼和感官體驗,引起國內外視頻網站用戶廣泛地二次創作與傳播,如美妝效仿視頻、女妖舞蹈模仿視頻、影片揭秘視頻等等,形成了極為開放和多元的媒介傳播現象。
四、結 語
視聽新媒體不斷與科技前沿思維和成果聯姻,將用戶最大限度地介入敘事,身體與影像高度縫合,實現可見、可聽、可觸、可感的多重感官聚合的“數字吸引力”建構,成為新一輪數字影像感知傳播的核心。“數字吸引力”傳播彰顯的自反性、具身性與瞬時性,呈現出“后電影”時代數字影像借助數字技術深入用戶感知結構的情感自覺與技術邏輯。此外,視聽新媒體的“數字吸引力”傳播是一次媒介生產,也是一次媒介消費,成為視聽新媒體交易的助推引擎。“數字吸引力”傳播為視聽新媒體的文化內核和消費關系提供了基礎,形成一種重視用戶情感與互動的“體驗”式媒介消費范式。
參考文獻:
[1][美]湯姆·岡寧.吸引力電影:早期電影及其觀眾與先鋒派[J]范倍,譯.電影藝術, 2009(2):61-65.
[2][美]湯姆·甘寧.吸引力:它們是如何形成的[J]李二仕,梅峰,譯.電影藝術,2011(4):71-76.
[3][新西蘭]列昂·葛瑞威奇.互動電影:數字吸引力時代的影像術和“游戲效應”[J]孫紹誼,譯.電影藝術,2011(4):84-92.
[4]Leon,G.(2010).The cinemas of transactions:The exchangeable currency of the digital attraction.Television & New Media,11(5): 367–385.
[5][美]湯姆·岡寧.一種驚詫美學:早期電影和(不)輕信的觀眾[J]李二仕,譯.電影藝術,2012(6):107-115.
[6]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絡視聽節目管理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視聽新媒體發展報告(2020)[M]北京: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20:198-199.
[7]羅雯.被馴化的奇觀:VR電影的吸引力與敘事性[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0(8):45-52.
[8]惠東坡,盧莎.互動敘事:全媒體時代視聽話語實踐的新走向[J]新聞論壇,2019(3):13-15.
[9]周雯,徐小棠.沉浸感與360度全景視域:VR全景敘事探究[J]當代電影,2021(8):158-164.
[10]Chris,M.The birth of virtual reality as an art form.Retrieved June 17, 2016, from https://www.ted.com/talks/chris_milk_the_birth_of_virtual_reality_as_an_art_form.
[11]張凈雨.從斷裂到延展:逃逸與被征用的劣質影像[J]當代電影,2021(12):151-156.
[12]屠玥.桌面電影:一場心理學的實驗[J]當代電影,2019(6):30-34.
[13][俄]列夫·馬諾維奇.新媒體語言[M]車琳,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21:109.
[14]王源,李芊芊.智能傳播時代沉浸式媒介的審美體驗轉向[J]中國電視,2020(1):67-71.
[15]Rolf,P & Christian,S. (1999).Understanding intelligence.Cambridge,MA: MIT Press.
[16]芮必峰,孫爽.從離身到具身——媒介技術的生存論轉向[J]國際新聞界,2020(5):7-17.
[17][美]湯姆·甘寧.現在你看見了,現在你看不見了:吸引力電影的時間性[J]宣寧,譯.藝苑,2015(3):67-73.
[18]賴薈如.電影返古:作為吸引力電影的“桌面電影”[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1(5):15-23.
[19]劉永昶.生活的景觀與景觀的生活——論短視頻時代的影像化生存[J]新聞與寫作,2022(4):24-32.
[責任編輯:華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