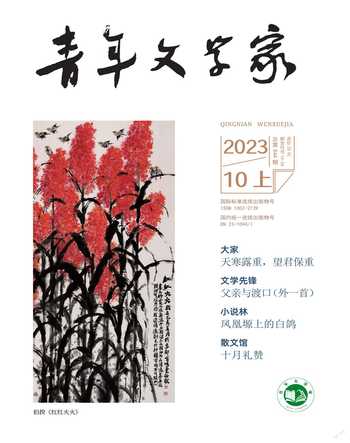家住古樹街
趙新平
我家住在縣城一條古樸而又偏僻的小街上,從東向西長千余米,街的東頭兒有一棵張家古槐樹,街的中段有一棵呂家古槐樹,街的西頭兒是兩棵皂角樹。這幾棵樹的樹齡均已上千年,歷經無數風雨,枝干粗壯,盤根錯節,虬枝繁茂。
站在街上,遠望古樹像一條條盤龍逶迤升騰,近觀似傘蓋遮蔽天日,想要看到樹木全貌,需要仰脖,還要屏住呼吸,但看到的是滄桑斑駁的灰褐色樹身、滿目瘡痍的枝干,還有重重疊疊的綠蔭。因為這些古樹和小街的地理位置,自小街上建了一所幼兒園、一所小學、一所中學后,使本應幽深恬靜的小街成了縣城里一條熱鬧的街道,整日里行人車流穿梭不息。
沿街店鋪林立,大多為早點鋪、理發館、燒烤店、雜貨鋪,我數了數,有三十多家店鋪。每天上學、放學時段,小街上的孩子嘰嘰喳喳如鳥群,一路吃著、喝著、走著、唱著、說笑著,像是趕廟會。
我的心里常感到愜意,生活在這樣的小街上,有風景看,也不會餓著,還要比別人多花點兒時間趕路,日子更加忙碌、充實,多好。小街本來有自己的名字—石磊街,但借得小街上的幾棵參天古樹,大家更愿意叫它—古樹街。
小街路面狹窄,會讓生活在縣城中心的人們以為購物、辦事都不方便,其實不然。生活在街上的人們走習慣了,多走幾步就是大街,隨便坐輛公交車、出租車,幾分鐘就能到鬧市區,想干啥都行,慢有慢的好處,多花點兒時間,歲月常在,啥事兒那么急啊!
在小街上生活,時間久了,與街坊鄰里、一磚一瓦間似乎萌生了一種難以割舍的聯系,是那種源自內心的真情實感。
現在,街上的住戶越來越多,家家門窗變得稠密,除了幾棵古樹,沒有河流田地,但季節的訊息絲毫不會錯過。春天來了,街東頭兒張家門口斜倚而生的古槐伸展枝葉,在樹梢頂端托起一團霧茸茸的綠意。古槐許是老了,長得慢,葉子小,開花也遲,一直到夏天才會悄悄地開出細密的黃色小花,散發著淡淡的清香,招來蜜蜂、小鳥日夜歡快地喧鬧。張家古槐距離學校遠點兒,過往的行人不是很多,無論散葉還是開花都顯得有些寂寞,卻不會有太多的陌生人在意。與張家古槐相比,位于小街中段的呂家古槐旁人來人往,最熱鬧,名氣最大,也最有靈氣。每年夏天,古槐樹開花的時候,天即使不下雨,樹葉上也會往下滴水,我是親眼見到的。
每次經過古槐,都會發現樹底下已落了一層薄薄的黃色花蕊,且都濕漉漉的,放慢腳步,從高空葉子上滴下的水珠會打在臉上、身上,抬頭仰望,蒼翠的古槐密不透風,感覺像在陰暗的叢林間穿行。
整個夏天,樹下始終坐著納涼的人們。我曾問過一個大爺,為啥樹會滴水?老人說,他也不知道。我記得,小時候貪玩兒,滿嘴里嚼過柳枝槐葉,不是苦就是澀。如今的呂家古槐,不僅護佑著小街,還給人們更多的心靈慰藉,使人們與古樹有了天然之趣。
再說小街西頭兒的兩棵雌雄異體的“夫妻”皂角樹。古時候,皂角樹因其果實皂莢能夠制皂,并供人洗衣、洗頭而得名。“夫妻”皂角樹雄樹不結籽,雌樹結籽。早幾年還能見著成熟后變成黑褐色的皂莢,人們用竹竿敲下皂莢,砸碎、泡水、過濾后,黏稠的液體便可當作洗衣液、洗發水,用其洗過的頭發黝黑發亮,綢緞般潤澤。如今,人們不再使用皂莢洗頭、洗衣物了,有的也許都不知皂莢為何物,皂莢也漸漸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但兩棵相依相伴的夫妻樹年年返青,年年枯黃,無法拒絕生命的顏色。
如今,縣城的高樓越來越多,人們追趕現代化的步伐也是越走越快,但因為幾棵千年老樹,使一條窄窄的小街滋生出了幾分沉寂的風骨,似一幅清絕的畫卷。
每天,熙熙攘攘的人群車流往來交錯,恍如夢境,讓人不免懷古,又不免思忖—原來,古老的歷史與現實是如此親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