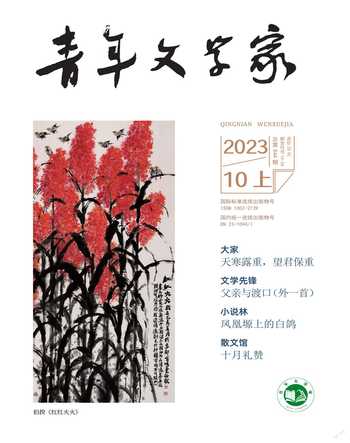父親的背影
王尊廣

倘若父親在世的話,今年正好九十大壽。可是,父親已離開我們二十多年了。
父親走的那年六十六歲。按我們家鄉的傳統習俗,人到了六十六歲是要慶祝一下子的,俗稱“過六十六”。為了讓父親高興,我們做子女的邀請了親朋好友,在飯店隆重地為父親過了六十六歲大壽。那天,父親看著晚輩都來給他敬酒,很高興,幾杯酒下肚臉色紅撲撲的。
在我們魯西南,盛傳著“躲六十六”的說法,有些人本來到六十六歲,但他們直接稱六十七歲。由此來說,人活著就是闖關奪隘,一生不知要經受多少關隘的磨礪。勝出者,無疑就是長壽者。從這方面說,我的父親在六十六歲時罹遇不幸,成了生命長路的失敗者。
父親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在上班途中曾看到了父親的背影,看他大步流星地走路,不知道他是去忙什么。就在那天中午,悲劇發生了—在我們村口的公路上,一個無德司機駕駛小汽車撞向了我的父親,父親不幸當場遇難。一切都無法挽回,我們作為父親的子女,只有以淚洗面,痛哭失聲。
父親不幸遇難,使全村人都倍感痛心。因為父親是全村公認的好人。在父親當村干部的那幾十年里,他不知犧牲了多少休息時間,對村民的各種要求總是不厭其煩地努力去做好。
對外面的事和他人的事,父親傾注了無限心血;對自己家里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總是過多地讓我娘去做。從讀初中,我就開始住校了。后來,我又參軍入伍,直到三十歲才回到了家鄉。記得我回到家后,為父親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理發。那天我下班后來到家,看到父親端坐在院子里一把椅子上,脖子上圍著一塊塑料布。見此情景,我趕緊支起車子,跑到屋里找到那把理發推子,又拿了一把塑料梳子,煞有介事地給父親理起發來,父親的頭發在我的手中慢慢變短。去當兵的時候,父親的頭發是黑的呀,并沒有幾根白的,可如今僅僅十多年過去,頭發竟然白多黑少。我知道,我們成家立業了,父親老了。我的眼前分明看見了幼年時期父親留給我的清晰記憶。
在我十歲那年,家里要多困難有多困難。吃的也不行,盡是些玉米面窩頭、玉米面餅子,一年到頭,難得見上一頓白面。那年臘月,母親帶著我的兩個弟弟去遼寧撫順我的姥姥家過年了。走之前一聽不讓我去,我十分不滿,我的哥哥去過,現在兩兄弟又去了,為啥不讓我去?那時候我是沒見過火車的,但我想象著火車拉著我的母親、弟弟一路向東北的樣子。那個冬天,我的棉襖外邊天天套著母親臨去東北前給我做的一件軍綠色的小褂,感覺像個軍人,心里美著呢!
最難的要數過年了,平時吃啥都行,過年總得吃點好的吧!現在年輕人講“儀式感”,在我們那時候無非就是過年整點兒年貨,炸丸子、蒸年饃、包餃子。肉是不用買的,再困難的生產隊年前都是要殺頭豬的,不管大人、小孩兒,一人分上一斤、兩斤的。家里沒錢的窘況我是知道的,看得出來那些日子父親的眉頭是緊鎖著的。家里只剩父親、哥哥,還有我了,年貨咋辦呀?父親每天出門了,我便蹲在門口望著他遠去的高大背景,直到看不見。我想,父親會有辦法的,年一定能過好。我記得很清楚,那天父親回來,臉上有了笑容,他不光借著了錢,還借來了十五斤白面。第二天,父親就開始蒸饃,雖然人家的年饃饃餡兒是用紅小豆、紅棗、甜地瓜做的,而我家的饃饃餡兒里只有地瓜和黃豆,但我們畢竟吃上了,而且過年時還吃上了白菜豬肉餡兒餃子。
而今,華發滿頭的我仍然時時想起我的父親。每每想起,眼前便浮現父親走出家門時的背影,可是,我再也看不到他回來的模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