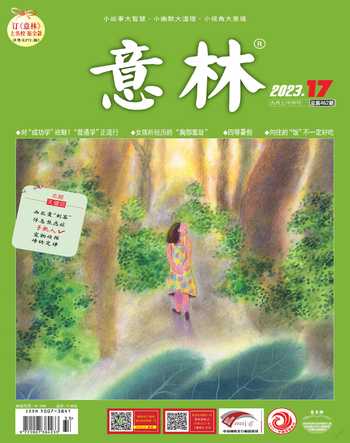烏 鴉
南在南方
天下烏鴉一般黑,幾近廢話,不黑能叫烏鴉?不過這句話說出來,不是好話。還有個成語愛屋及烏。看起來,烏鴉不是好鳥,可古人又說了,烏鴉有反哺之義,被稱為“孝鳥”,集大惡大孝于一身,真咄咄怪事。
白居易大概喜歡烏鴉:“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寫烏鴉沒媽了,整夜叫喚,是鳥里頭的曾子。曾子孝順,山上砍柴時忽然心痛,奔回家,原來家里來了客人,母親有點焦急,想著他在家里就好了,咬了一下手指,他就覺察到了。
我們管烏鴉叫老鴰,它們的聲音單一,哇哇。老鴰好像曉得人不待見它們,它們離人家遠,做窩也好,找吃的也罷,都在遠處,不像喜鵲的窩可以做在門前的樹上,它們叫喳喳的,也吵人,但不像人說鴉噪,惱怒的口氣。老鴰做窩像碗一樣,露天的,雖然也銜草,但也會銜些柔軟的東西鋪著。
蘇東坡在黃州,有一首詩寫:“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東坡先生情緒低落,可烏鴉見著人上墳的黃紙,要銜到窩里去,春天來了,得生蛋,孵小烏鴉了。
我小時候捉過小老鴰,羽毛油油的黑,嘴尖尖的,動不動啄一下我的手,啄住不放松不說,還要試著擰一下,爪子也厲害得很。祖父教我莫砍冬天的樹,莫打三春的鳥,一定要我把這只小老鴰送回窩里,那是老鴰的娃,娃不見了,老鴰著急嘛。
老鴰喜歡好大一群待在一起,黃昏時總要叫上一陣子,偶爾天黑之后,有一只哇哇叫著,像是一個晚歸的人,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喊門兒,如同曹操的“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等它不叫了,嗯,感覺是回家了,莫名地就有點高興。
我們那兒不說老鴰報兇,卻說喜鵲報喜。“哎呀,我說今兒喜鵲在門前叫了一早上,原來是要來稀客呀。”這話一說,賓主盡歡。
唐時烏鴉也報喜的:“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慚愧元郎誤歡喜。”還是白居易的詩,看見有一本書上的注釋說,烏頭白,馬生角,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可這里白居易說“我歸應待烏頭白”,大約是說“等我老了就回來”?
學者顧頡剛編了一本《吳歌甲集》,里頭有兒歌也是烏鴉報喜的:“老鴉啞啞叫,爹爹賺元寶,姆媽添弟弟,哥哥討嫂嫂,姊姊坐花轎。”歡喜極了。
天下烏鴉一般黑,據說有白脖子烏鴉,我沒見過,從前看《世說新語》有一則: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當時覺得奇怪,支道林是高僧,去見王子猷兄弟,王子猷就是那個著名的雪夜訪戴的主兒。別人問:“你看王氏兄弟怎么樣?”支道林說:“只見一群白脖子烏鴉,啞啞叫著。”這一則收在《輕詆》卷,有些口舌之爭。問題是,幾個穿白領子衣裳的浙江小伙子說浙江話,聽不懂,也不至于像鴉噪啊。
后來買了一本《老學庵筆記》,陸放翁提到這一則逸事時說,古所謂揖,舉手而已,今所謂喏,始于江左諸王,“啞啞”此為唱喏也。豁然開朗,原來王家開風氣之先哪。
我一直覺得烏鴉最好看的時候是雪天,所謂“江山一籠統”的時候,“萬徑人蹤滅”的時候,一群烏鴉飛來,落在雪地上,顧盼生姿,找點吃的。白是白,黑是黑,站在門里邊,大氣不出,看它們走來走去,想著東坡的一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等它們飛走了,踏雪去看,像是畫了一地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