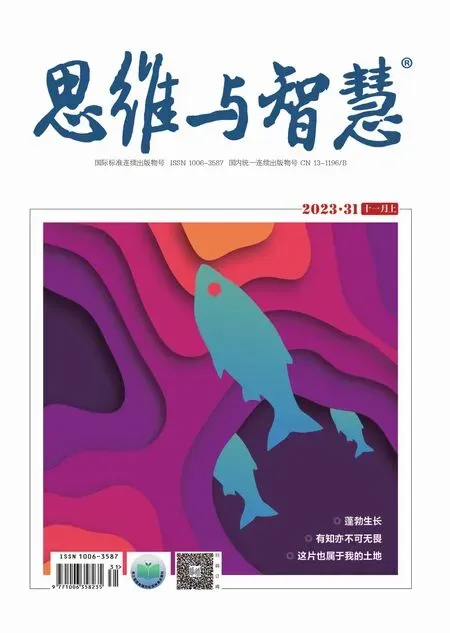人生開始的時間
◎ 甘正氣

和即將讀大二的侄子一起吃飯,大家都埋頭吃飯又不時看一下手機,稍顯沉悶。我忍不住問:“你有什么人生目標嗎,有沒有人生規劃?”他笑:“我的人生還沒開始呢!”
好像奇峰突起,霎時云橫秦嶺,這回答讓我大感突兀,我以探討的語氣問:“人生應該從出生就開始了吧?”
后來我想了想,或許我的看法有些武斷和偏頗。人生有各種不同的開始,出生只是其中一種。開始懂事,對人生的際遇開始有所感受、有所理解,可以算是一種;試著對自己人生的走向施加影響,開始努力把控自己的人生,想方設法改變人生的軌跡,又是一種。我猜,在侄子心中,只有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才是人生的開始。當然,也有人一輩子迷迷糊糊但又快快樂樂,在別人的安排與呵護下不用思考地過完一生,他有自己的人生,但又好像從沒有所謂“開始”。
我們那一代的鄉野少年,人生是開始得非常非常早的。
我曾經在棉花地里一蔸一蔸地移栽棉花的秧苗,一蔸一蔸地給剛移栽的棉花秧苗培土,彎著腰一蔸一蔸地給它們澆水,又曾在熹微的晨光中蹲在地里一小把一小把地扯雜草,也曾在烈日下站在地里一朵一朵地摘棉花,腰上系著一個像圍裙一樣的大包袱,邊走邊摘。摘棉花的我就像一頭馱著海綿又掉進海水的騾子,身上越來越重。
老家那里屬于洞庭湖平原,臨近大河,可是我們那個村卻只種棉花、油菜,有段時間也種苧麻,但就是沒種過水稻,不需要“搶收搶種”,所以我沒體驗過“雙搶”的滋味,據說那可以讓任何人都精疲力盡、累不欲生。“雙搶”期間的每一天都是一場混合著撲面的塵土、渾身上下的汗水與無處不在的瘙癢、酸痛到僵硬的雙臂、劃滿口子的雙手以及好像馬上就要斷了的腰背的長達十多個小時的噩夢,參加過的同學即使多年后都后怕不已。在我的想象中,“雙搶”是與時間激戰,“搶種”是為將來播種希望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搶收”是向稻田索要豐收的諾曼底登陸,“雙搶”期間那種度日如年的艱辛煎熬,又像是奧德修斯的十年歸,勞動強度之高根本不是種棉花、油菜可以比的。付出不同,所得也就迥異。我們那里只有可以用來做被子的棉花、用來炒菜的棉籽油,勉強可以解饞的只有黃瓜、西紅柿,而種稻谷的需要“雙搶”的那些村莊,則有米糖、年糕、糍粑。
我也曾和母親一起去鄰縣販運過甘蔗,還曾乘著父親和他的同事們駕駛的鐵板船向城陵磯運送過蘆葦。夜色中那長長的路,長長的坡,夏天里閃著粼粼波光的長長的河,港灣里密密麻麻的蚊子,還有那長長的一壟一壟望不到頭的棉花、苧麻,沒有什么詩意,難以勾起那些關于江流日夜、田園牧歌的想象,我只覺得枯燥。讀書好像是天底下最輕松、最簡單的事情,于是我從小喜歡讀書、上學,我穿戴整齊,挎起書包,勁頭十足、精神抖擻地一路去喊同學們上學,他們都還在呼呼大睡。魯迅是懷著離開百草園的悲傷前往三味書屋的,而我則開心地飛向學校,因為農村的草不是用來欣賞的,而除草又太過乏味。
因為愛讀書,我現在還在和文字纏綿著,纏斗著。那些不愛種地也不愛讀書的發小,很多當上了老板,他們的人生或許是從做學徒、幫工開始的。
魯迅看到他周圍人們的生活大概有三種:辛苦輾轉的,辛苦麻木的,還有辛苦恣睢的。現在則不同,多有幸福輾轉的,開心麻木的,還有痛快恣睢的。
看到家中開心麻木的小輩們,我為他們無憂無慮的生活感到開心,但是又忍不住想勸他們開始一種更有意義的人生,一種省察人生、追尋和創造價值的生活,他們會因為我的問話和啟發而投身文學、藝術和科學嗎?如果有了這樣的念頭,那就趁早開始,為了一種富有詩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