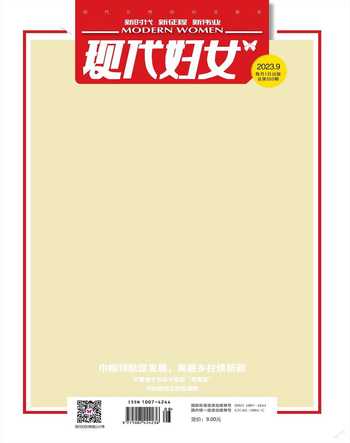《尋找林木森書店》:為孩子們點一盞書燈
湯素蘭

我第一次接觸到的課外書,是一本沒有封面封底、卷了角、書頁泛黃的舊書,書中的故事卻讓我印象深刻。書里講了后羿和嫦娥的故事,眉間尺為父報仇的故事,還有大禹治水、老子出關的故事。后來上了大學我才知道,我讀到的是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我第一次讀到這樣神奇的故事,第一次通過故事接觸到跟我周圍環境里完全不一樣的人,與其說我被故事所吸引,不如說這些故事讓我“震驚”。正是這種震驚,打開了我的閱讀之門。
閱讀給我帶來的好處是寫作文時用的好詞好句比一般的同學多,作文寫得比別的同學好。上中學的時候,老師把我的作文貼在學校的墻壁上,這是我作文的第一次“發表”。對于一個其他功課平平的女孩子來說,這種發表讓我獲得了成就感,而我的中學語文老師對我的獎勵是把他收藏的文學書籍,包括訂閱的《人民文學》雜志給我看。
那時候,我們縣文化館有一份自辦刊物。有一回,我的語文老師的文章發表在了這本刊物上,他很自豪地把刊物拿給我看。看到文章變成鉛字,印在書上,而且就是我老師的文章,我再一次被震驚到了。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學校分了文理科,我進了文科班,老師在文科班教室的黑板上方寫了“立壯志,躍馬文壇”7個大字。對于一個農村孩子來說,那時候能讀完高中,考上大學,獲得一個吃國家糧的機會就是全部的理想。可是,我每天看著那7個大字,慢慢地,心蠢蠢欲動,仿佛長出了翅膀,對自己的未來有了更多的想象……如果將來考上大學,我一定要讀中文系,如果我讀了中文系,我會不會也像老師那樣,寫的文章能變成鉛字,刊登在報刊上呢?
后來,我真的考上了大學中文系,在大學時代開始文學創作,有小小的作品發表在省級公開刊物上。
走上工作崗位之后,我有幸成為一名少兒圖書編輯。有一年,一個記者朋友從偏遠的林區采訪回來,跟我說那兒有一家林場學校,僅有1個老師和13名學生,學校連一本課外書也沒有。我想起了我的少年時代,我上初中的時候,我們班也只有13名學生,學校里也連一本課外書都沒有,我有限的幾本課外書是自己在村莊里搜尋別人家的閣樓得來的。而我如今在出版社工作,我的辦公室里堆滿了樣書。于是,我整理了幾十本書,打包寄給了那個林場學校。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經常給偏遠貧困地區的學校郵寄圖書。2017年開始,我將這項圖書捐贈活動經常化,命名為“素蘭書屋”。迄今為至,我已經捐建了28所“素蘭書屋”,捐贈圖書近10萬冊。在每一家“素蘭書屋”的捐建儀式上,我都會對孩子們重復這樣的話:“書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它能填平教育的溝壑,當你學會了閱讀,你就擁有了一只強健有力的雄鷹,而你就可以成為鷹背上的小鳥,去見識更廣闊的世界。”
雖然全社會都知道閱讀的重要性,但現實不容樂觀,我們看到身邊的實體書店紛紛倒閉,越來越多的人將時間花在刷視頻、看手機信息上。因為互聯網的普及,人們能得到即時的新聞和信息,仿佛無所不知,而人們的深度閱讀和獨立思考卻越來越欠缺。
大自然有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和冬藏。讀書也是一樣。一個人的閱讀習慣要從小養成。一個人只有在小時候就能品味到文字之美,能被書的神奇魔力所吸引,他長大后才會對閱讀著迷,才會選擇將讀書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因為閱讀對我們如此重要,作為一名兒童文學作家,我常想,我要如何才能引導孩子們愛上閱讀?我不是孩子們的家長和老師,不能對他們耳提面命,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寫一個神奇的童話故事,講一講讀書與書店的重要性,于是,就有了我的童話《尋找林木森書店》。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愛讀書的男孩、一只神秘的黑貓和一只木雕兔子,通過這3個人物,我寫了一家百年書店的消失與回歸。
童話從來都不是現實的可能,而是愿望的滿足。我覺得,在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應該有一家了不起的書店陪伴著他,為他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記憶。這家書店離孩子的家和學校都不太遠,古色古香,還有一個明顯的標志物——木雕兔子。孩子喜歡動物,一個幸運的孩子一定會遇上有魔力的動物,比如在《尋找林木森書店》里,男孩木里就遇到了一只黑貓,它將木里帶往了神奇的童話世界。
童話雖然是幻想出來的故事,但一切的幻想都應該有現實作為根基,這樣幻想才有生命,這樣的故事才會引起心靈的共鳴。在《尋找林木森書店》里,我還講了世界上兩家著名書店的故事。一家是倫敦的查令十字街84號馬克思與科恩舊書店,另一家是法國的莎士比亞書店。馬克思與科恩舊書店雖然已經不存在了,但這家書店和讀書人之間溫暖的故事,卻因為《查令十字街84號》這本書而永遠留存在全世界熱愛讀書的人們心中。莎士比亞書店1919年由美國姑娘西爾維亞·畢奇在幽靜的巴黎左岸劇院街開設,這家書店在當時成了美國文藝界大咖學者的文學沙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家書店關閉了。但在20世紀60年代,年邁的西爾維亞遇到了在巴黎開書店的美國青年喬治·惠特曼,于是,畢奇女士把莎士比亞書店的店名和保存下來的一些作家珍貴的手稿轉贈給了喬治·惠特曼,讓莎士比亞書店的傳奇得以延續。這家書店本身就在講述書的神奇——莎士比亞是英國作家,開書店的是美國人,而書店開在法國。
有一種文創設計叫“書燈”,攤開的書頁里面發出柔和的光,書香彌漫。望著書燈,我常會想起童年時代挑燈夜讀的情景。那時候還沒有電燈,我將注滿煤油的鏡燈點亮,掛在蚊帳里面的帳鉤上,一直讀到燈油燃盡,四周一片黑暗,我心里的燈卻亮了起來,那是智慧的燈。
我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在童年時代便與書為友,長大以后,走遍天下以書為侶,因為書里有人類靈魂全部的美麗。
(摘自《中國婦女報》)(責任編輯 王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