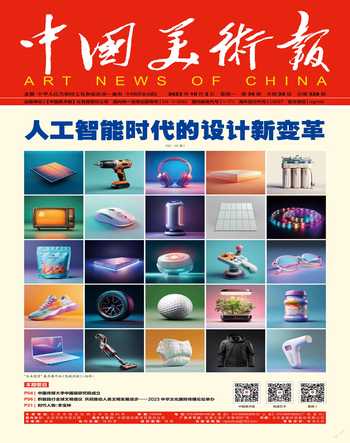意造:中國書法浪漫主義創新之路
陳緯
中國書法發展有幾個重要歷史節點,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態”。
唐代“尚法”書風如高峰擋住宋人書法發展的出路,宋人只能另辟蹊徑,突破唐人技法高度完備的樊籬,闖出一條“尚意”新路。與唐人“尚法”的主流相比,宋人書法更注重意趣的抒發和個人情感的宣泄,表現出一種任情適性的自由,更接近藝術的本質。
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宋四家”為代表,宋代“尚意”書法呈現崇尚新意、凸顯個性的時代風格,重內涵輕表象、重意趣輕法度,強調意在法前。蘇東坡說,“我書意造本無法”,又說其書“無意于佳乃佳”。傳說蘇東坡喜歡酒后寫字,任意揮灑,將創作與個人內心情趣表達高度統一。這種借筆墨表達情感的藝術主張提升為書法創作最高境界的思想,以深厚的文化修養滋蘊高度自我表現意識的書風,為后世提供了“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的實踐范本,成為中國書法審美風向標。
“意造大觀——宋代書法及影響特展”展出自北宋以降歷代書法名家的精品,從策劃理念和展覽結構安排上,呈現宋元明清各歷史時期的書法美學特征,勾勒中國書法浪漫主義創新之路的曲折發展進程。可以清晰看出,書法的創新發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宋代“尚意”美學的遺產,既尊重傳統規律,又追求個性和創新,成為中國書法的審美精神。
從展覽結構的安排上,分“貞珉萃英”“我書意造”“布濩流衍”三個板塊。在策展思路上,通過展品組織與展示,呈現三個命題:
一是杭州在宋代書法史中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宋四家”與杭州有著一定的歷史淵源。蘇軾曾兩度在杭州為官,時間合計五至六年,在杭州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是杭州最為著名的歷史代言人。黃庭堅與浙江有一定的歷史因緣,和蘇東坡亦師亦友,并稱“蘇黃”。他又是蘭溪女婿,早在唐代,他的祖籍為金華浦江。米芾在35歲的時候曾做過杭州從事,以后又去過湖州、紹興等地,留有許多墨跡碑刻。蔡襄晚年受朝廷排擠,到杭州任知州,這是他平生最后一任的官職,時間為一年,這次展出選了一件他于杭州任上所書《持書帖》。杭州無疑是“尚意”書風的發生地之一。
作為南宋故都,杭州遍及環西湖域內的兩宋遺存摩崖石刻碑拓數量龐大、內容豐富、題刻精美,最能體現杭州作為宋代書法文化中心的歷史地位。西湖風光宜人,蘇東坡曾說“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宋代文人墨客競相在這里的摩崖上留下字跡,大有“到此一游”之意。如蘇軾于杭州知州任上留下的《大麥嶺題名》、米芾任杭州從事時留下的《方圓庵記》《琴臺》、朱熹的《曇山題名》、賈似道的《龍泓洞題名》以及司馬光書《家人卦》《樂記》《中庸》等。這些碑刻不但表現宋人書法之美,同時也讓后人一窺字里行間的歷史信息。如抗金英雄韓世忠命12歲兒子韓彥直所書《翠微亭題名》,位于靈隱飛來峰冷泉溪上方的“翠微亭”,其名應來自岳飛遺詩《登池州翠微亭》句:“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讀這塊碑記,分明聽到韓世忠當年面對西湖,遠眺風波亭,發出無奈與悲傷的一聲浩嘆。
在“貞珉萃英”這一展覽板塊,除摩崖碑刻外,還有體現兩宋書法風雅蘊藉的“法帖”與“銘刻”。南宋朝廷與民間均刻帖成風,原南宋權臣韓侂胄令門客將家藏名書編次拓印成的著名法帖《群玉堂帖》,至今十已喪半,這次展出有卷四《懷素千字文》和卷六《蘇帖》。還有南宋拓本《紹興米帖》,系當時由皇家主持將米芾書跡刻成的法帖。
蘇軾書法石刻傳世擘窠大字以《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奎宸閣碑》《表忠觀碑》等最為著名。展出的《豐樂亭記》原為羅振玉舊藏,是南宋拓本。元豐元年(1078)原刻、南宋重刻的《表忠觀碑》由蘇軾奉敕撰文并書。蘇軾這兩碑楷體大字書寫嚴謹、情感飽滿,字大見方,楷中稍帶行書意,氣象雍容大度,是蘇軾“意造”書寫精神的直觀體現。
二是宋代“尚意”書風的緣起、特征與發展。
宋代“尚意”書風的形成,其思想武器即起源于唐代中期的禪宗。禪宗,吸收儒、道思想,實現三教合一。作為佛教的一個派別,發展至宋代已成為士大夫的宗教。禪宗思想影響著宋代文藝,面對唐以來技法完備的發展瓶頸,宋人“尚意”書風轉而追求“無法之法”“不工之工”,主張“我書意造”“信手自然”,與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觀念相一致。禪學與書法有著天然的互通之處,互為影響。自北宋以來,善書僧人代不乏人,直指人心、自然流露的禪僧書法,拓展了“尚意”書法的表現空間。
這次展出南宋張即之楷書《華嚴經》選頁和兩位禪宗高僧密庵咸杰、無學祖元的真跡。他們都與杭州徑山寺有歷史關聯,為此又在徑山寺設了一個分展區“澹然世界寬——宋元明清禪宗墨跡展”,展出自宋以來歷代高僧的禪宗書法。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存世代表作《自書詩卷》是這次展出的最大亮點。這是陸游80歲在紹興故里所寫的八首詩,都是寫他與村中父老交往及鄉村生活的題材,親切可愛。陸游書名為詩名所掩,作為“南宋四家”之一,其草書學唐代張旭,行書學五代楊凝式,書跡飄逸風流。從他這件晚年代表作來看,書體不計工拙,章法不拘成法,將“胸中磊落藏五岳”的思想境界運用于草書之中,正契合蘇軾“我書意造”的境界。
事物的發展總是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迂回過程。“尚意”書風到了南宋末年,人們對法度的輕視,導致南宋后期的書法走向頹廢沒落的邊緣,基本沒有出現有作為的書法家。物極必反,這時候,作為元代藝壇領袖的趙孟頫振臂一呼,高舉“復古”旗幟,主張宗法“二王”,回到書法“正脈”,矯正南宋末期頹敗書風的走向,意義非凡。展覽特別選擇趙氏深得“二王”精髓的代表作《洛神賦卷》,是這段書法發展歷史節點的一個觀照。
三是“尚意”書風對歷代書法美學思潮的影響。
元以來至明初,書法創作提倡“復古”,書必晉唐。到了明代前期,書法走向沉寂,不講創新,流行沒有個性、中規中矩的書風——“臺閣體”。溫州人姜立綱14歲便被選為朝廷的“中書舍人”,寫得一手標準楷書,技法嫻熟,無懈可擊,人稱“圣手”。這次展出他傳世唯一一件的草書作品《李太白夢游天姥吟留別》,用筆流暢自然,一氣呵成,無絲毫刻意雕琢之感,深得懷素神韻,使我們窺得這位“臺閣體”殿軍人物的另一面。
明代中期,一些書法家已不滿足毫無生氣的“臺閣體”書法,開始探索創新,遠從宋人“尚意”書風尋找突破口,以改變明初以來低靡單調的書法審美趣味,以祝允明、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書派”成為明代中期書法發展的主流。祝、文兩位是書壇領袖,陳道復、王寵等為中堅,還包括沈周、吳寬等前輩。他們都受黃庭堅、蘇東坡和米芾的影響,特別受黃庭堅影響最大。這次展覽都有他們的精品展出。
祝允明的最大貢獻是重新倡導北宋“尚意”書風,他整合黃庭堅草書與唐代“顛張醉素”的草書,創造出一種新式的草書樣式,并成為明代草書的典范,開創了明代浪漫主義書法的先河,同時引領后代書家推向高潮。
徐渭才華橫溢,一生命運多舛,是個狂人、妄人。當病理上的瘋狂轉化為藝術行為,會創造出常人所無法企及的高度,因此徐渭又稱“東方梵高”。他的狂草用筆狼藉,線條粗獷,馳騁奔騰;他將字的間架打散,服從整體作品效果。他的這種舍棄局部技巧美感價值,一切為了整體的視覺效果的“破壞性”特點,開啟和引領了晚明“尚態”書風,把中國書法創新引向了新的高峰。在他之后,人們對書法的審美有了新的認識境地,之后出現一大批燦如繁星的表現主義書法大師。
到了晚明,王陽明“心學”受到知識分子的追捧。書法創作強調感性,崇尚自然,書法家在創作中將思想、情感、理想等等投射到創作之中,非常接近陽明心學“知行合一”的主張。同時,物質生活的改變與書寫工具的革新給書法創作帶來新的面貌。晚明出現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萌芽,人們的居住環境擴大以及羊毫筆與生宣的大量使用,大大拓展書法創作的藝術表現空間,書法作品從案上走向墻上,出現了大尺幅的立軸作品。
這些原因都為明代晚期出現極具個性風格的書法大師群體創造了歷史條件。這批在中國書法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有徐渭、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八大山人……如此多的大師集中出現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可以說空前絕后。
在“布濩流衍”板塊展出作品的這批明清書法名家,都是受宋代“尚意”書風影響的藝術創新大師,個個自有特色風格,充滿浪漫主義的藝術色彩,在中國書法史上獨當一面。明之后,清初的“揚州八怪”以及整個有清一代至民國“碑帖結合”的創作思潮,追根溯源,都得益于追求個性、追求內涵、追求風格的“意造”精神,這條浪漫主義的創新之路,一直影響至今,成為書法藝術乃至整個中國傳統藝術創作的至高境界。
(作者系本次特展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