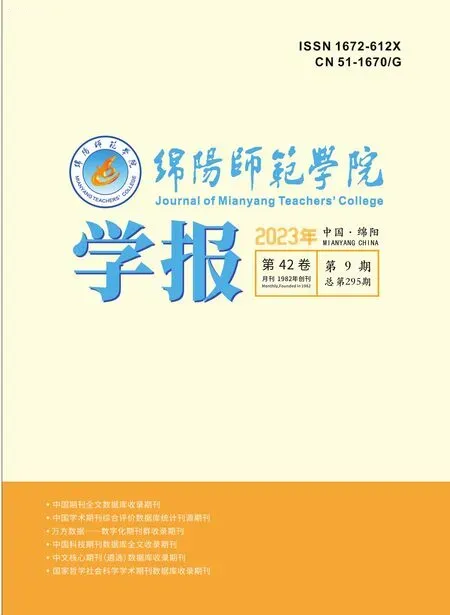戰爭紀實·民族主義·女性解放
——論廬隱的長篇小說《火焰》
楊昊霖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 610064)
提到廬隱,人們的第一印象便是“五四”時期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海濱故人》與感傷的女作家形象。作為最早一批覺醒的女學生和女作家,廬隱在“五四”時期初登文壇并大展身手。但隨著社會格局風云變幻與廬隱的再次戀情,大眾對廬隱私生活的關注反而超過對其文學作品的關注,學界對廬隱文學上的認識也基本延續了茅盾《廬隱論》中的看法:“廬隱,她是被‘五四’的怒潮從封建的氛圍中掀起來的,覺醒了的一個女性……廬隱她的‘發展’也是到了某一階段就停滯了;我們現在讀廬隱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著‘五四’時期的空氣,我們看見一些‘追求人生意義’的熱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們在書中苦悶地徘徊,我們又看見一些負荷著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的青年們在書中叫著‘自我發展’,可是他們的脆弱的心靈卻又動輒多所顧忌。”[1]不可否認,“哀傷的筆調”是廬隱創作的整體風格,但廬隱“在暑假中炎暑的天氣里,揮著汗寫成一部長篇戰事小說”[2]87,《火焰》卻完全摒棄了廬隱“哀傷的筆調”,書寫的重心也從“五四”脆弱青年的自敘抒情轉移到更具時代性與廣闊性的社會與戰爭,令人刮目相看。但是,這部別致的作品卻幾乎被學界所忽視,不僅研究者寥寥,即便有也是在文中一筆帶過,且評價不高。為什么會如此?如何評價這部被忽視多年的長篇創作?特別是當我們將《火焰》置于重新探究廬隱創作轉向的原因,還原廬隱更為真實的創作觀念和思想立場時,它有著怎樣的價值與意義呢?
一、基于戰爭紀實的自敘傳體的藝術想象
隨著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興起,“人的發現”成為越來越多新青年追求的人生主題。雖然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但對于剛接觸白話文創作與西方文學思潮不久的“五四”新青年來說,以記錄與表達自身的身世、經歷、思想、情感的方式來創作小說更契合他們的寫作理想,自敘傳小說遂成為眾多青年寫作的選擇。廬隱便是如此,她是“五四”時期首批覺醒的女作家之一,1921年憑借短篇小說《一個著作家》在文壇嶄露頭角。經過兩年的寫作與摸索,廬隱于1923年10月在《小說月報》連載長篇小說《海濱故人》。它不僅奠定了廬隱之后創作自傳體小說的色彩基調,也讓她摸索到最得心應手的寫作方式——自敘傳體。即使后來廬隱以書信、日記等形式創作,其文本內容也蘊含著她本人極其強烈的主觀情感和生命體驗。
《火焰》同樣是一部自敘傳體創作小說,與《海濱故人》有著類似的人物關系設定。小說圍繞著主人公陳宣與四位戰友的遭遇展開敘述,以第一人稱視角呈現出上等兵陳宣在“一·二八”淞滬戰爭中的生命體驗,通過刻畫陳宣五人在淞滬戰爭中的經歷,來激發讀者抗日救國的民族情感。面對全然陌生的題材,廬隱選擇其寫作生涯中最熟悉的自敘傳體模式進行創作完全在情理之中,且自敘傳體也為作者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提供了文體基礎。《火焰》的戰爭題材和自敘傳體的寫作方式要求廬隱描述陳宣的作戰體驗與戰斗細節,而戰爭與廬隱的日常生活經驗有著天壤之別。不過,廬隱雖沒有親自上戰場參與戰爭,缺乏士兵的第一視角的感受和體驗,但并非完全置身事外。戰爭開始時,廬隱居住在上海愚園坊20號,離閘北一帶的戰場也僅有十公里左右。淞滬戰爭爆發后,躲避戰難的大量民眾紛紛逃往租界尋求庇護。廬隱雖不能體驗戰場上真實的廝殺和槍林彈雨,卻耳聞了戰場上中國軍人英勇頑強的戰斗精神。她通過搜集大量時效性與真實性較強的新聞報道等材料,在《火焰》中盡力還原了一個十九路軍普通士兵陳宣所親歷的真實戰場,并通過陳宣在戰爭中的親身體驗,具體入微地描寫了戰斗的情形和中國軍人不屈的抗敵意志。如寫十九路軍對付日軍裝甲車的方法:“我們老早將手溜彈五六個,拴在一塊,把保險栓抽去,并用一條長長的鐵絲系住,一條鐵絲系上許多炸彈,兩旁安置上哨兵,敵人漸漸來得近了,我們把鐵絲一松;一陣拍拍轟轟的聲音,早見敵人的鐵甲車四分五裂的倒在地上。”[3]62同樣的細節描寫還有很多,如初戰告捷擊落日軍一架飛機、車夫胡阿毛載日軍沖入黃浦江、士兵用香煙盒做炸彈等等,力求將一個真實的“一·二八”淞滬戰爭情形呈現給大家。不僅如此,廬隱在戰爭紀實的基礎上展開藝術想象,讓陳宣參與到真實的歷史事件中。如日本轟炸商務印書館與東方圖書館一事,作家這樣寫道:
“呀!好大的火喲!……唉,商務書館遭了殃!”一個瘦個子的廣東兵,跑進來說……有幾頁殘稿,被風卷到戰壕近邊來……“唉,打仗就是一個大毀滅,為什么一些啞巴的書籍,也會遭這樣的打劫!”我們的連長憤慨地說。“書籍固然是啞巴,可是他維系著我們全民族的生命呢。當初日本人滅了朝鮮,第一禁止朝鮮人讀他本國的文字,這正是日本人斬草除根的狠毒手段,現在想依樣的加在我們身上。他們的野心我們很可以明白了。”黃排長說……北望東方圖書館也燃燒起來了[3]63-65。
在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被毀的紀實基礎上,作家虛構了陳宣等人的在場,通過想象紙頁飛到戰壕、眾人議論等細節,不僅增強了小說的可信度與代入感,也通過眾人的議論側面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陳宣在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中總被安排扮演一名旁觀者,并不是事件的主要參與者。對于較為宏大的歷史事件,廬隱是有所顧忌的。她作為戰場外的非親歷者,不敢牽涉太多真實的細節,越是宏大的歷史事件,細節越難用藝術想象填充,不慎的虛構有可能會因材料了解不足而使作品墮入虛假的深淵。于是廬隱讓陳宣參與到一些規模較小的歷史事件中,如《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料》中有一則新聞《班長奪取最新式之機關槍》:
又第二團班長陳友三,于二月十五日竹園墩之役,敵方有連珠槍射來,其勢頗異,前所未聞,料為敵之新式槍。當時第五連欲奪此槍,奮勇沖進,因而犧牲者不少。該班長深夜由側面蛇行斜繞,深入敵陣,自機槍手之側背,襲擊狙殺而奪獲之[4]345。
《火焰》中同樣也描寫了陳宣所在的第五連奪槍之事,但對此事稍加改動:
張權說:“你們聽敵人的炮聲槍聲……那末我們趁這個時候到敵人那里借幾桿六五槍,及一兩挺輕機關槍來,做紀念也好。只要有四五個人就行了,……老謝,我們去同連長說聲好不?”……攻擊的時間到了,秦連長率領了我們魚貫的出了掩蔽部……我們得了不少的子彈,還有六五步槍八桿,輕機關槍一挺,我們砍毀敵人的鐵絲網,托著輕機關槍和六五步槍,從從容容的回來了[3]200-206。
小說改寫了第五連奪槍失敗“犧牲者不少”的事實,而讓同屬第五連的士兵陳宣與連長等人完成了一次振奮人心的深夜奇襲。這次勝利不僅渲染了十九路軍抗日作戰的機智英勇,同時也傳達了積極昂揚的抗日愛國精神,激發了讀者抗擊外敵的民族主義情緒。廬隱為保持小說真實性,尊重宏大的戰爭紀實事件,選擇在較小的歷史事件中尋找虛構敘事的空間。作家將短訊信息擴充到幾千字的篇幅,充分發揮藝術想象虛構了陳宣等人深夜奪槍的作戰經歷,完整呈現了第五連戰士從籌備奪槍到勝利歸來的全過程,在戰爭紀實與個體虛構敘事之間找到平衡。
小說中對作戰細節的還原以及相關新聞材料的應用,在同時期以“一·二八”淞滬抗戰為題材的小說中獨一無二,從這些材料的運用來看,廬隱創作《火焰》時頗費了一番心血。第一次淞滬戰爭結束后,大批作家創作了相關題材的小說,如黃震遐的《大上海的毀滅》、鐵池翰的《齒輪》等,這些小說大都在1932年結束前出版,而廬隱并沒有趕時間出版,她在自傳中提到:“在暑假中炎暑的天氣里,揮著汗寫成一部長篇戰事小說,這本書本想出版的,不過我還要修改一次。”[2]87《火焰》的初稿完結于1932年的夏天,但據廬隱給《華安》雜志主編陸錫禎的信件①,《火焰》的寄出與發表是在1933年的夏天,而廬隱其他小說寫作與發表的間隔時間都不曾長達一年之久,這一年的修改時間也從側面證明了廬隱對此小說的謹慎與重視。廬隱基于戰爭紀實,以自敘傳體書寫士兵戰爭體驗的創作手法既不等同于力求真實的報告文學,也與上帝視角描寫戰爭全局的史詩不同。作家以戰爭紀實為基礎展開個人敘事的藝術想象,在虛構中保持宏大歷史的真實,這一寫作手法在同時代同題材作品中可謂獨樹一幟。
二、民族主義立場的矛盾建構
以戰爭紀實為基礎的自敘傳藝術想象的寫法是新穎的,但小說為何沒有獲得應有的反響呢?其主要原因在于陳宣這一人物形象的失策。眾所周知,自敘傳小說的主人公,很大程度上附著了作家本人的思想情感,而《火焰》中陳宣的許多言行舉止與思想情感有悖于角色身份且前后矛盾。雖不排除廬隱將小說修改時間拉得過長,導致作家的思想情感發生變化難以統一,但究其根本,是賦于人物形象上的作者自身的立場與價值觀產生了矛盾與沖突。
廬隱在經歷“九·一八”“一·二八”等一系列民族危機前,是一位世界主義者。世界主義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觀為主導的大同思想傳入中國,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普及在新青年中漸成流行趨勢。桑兵曾指出,“五四”新青年一代所接受的世界主義思想來源主要有三個:羅素的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以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5]。三種思想來源都多多少少影響了廬隱的世界主義思想,但嚴格來說她的立場更偏向于羅素的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廬隱作為“五四”中覺醒的作家,曾在北京國立女高師旁聽,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許多新文化陣營的代表人物也在女高師授課,廬隱因此接觸到新文化一派從國外帶回的新思潮、新學說。且羅素的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在當時也頗受國內青年喜愛,其1920—1921年的來華講學影響了一批青年。1920年廬隱曾在校《文藝會刊》上發表了議論文《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以“我”和“他”的界限為標準,將人類社會分為“家族主義時代”“軍國主義時代”和“世界主義時代”。廬隱在文中如是說道:“家族時代,以利一家一族為利己;軍國時代,以利一國為利己;世界主義,一旦流行,就必定要利人類,然后才能利己;若到這個時候,利己利他還有絲毫分別么?所以現在人說底利己,不外指家族觀念,鄉土觀念,國家觀念,實在是一種偏狹自私底見解,絕不是徹底底議論。”[6]9廬隱早期接受的世界主義思想從此扎根,并對她的人生和創作影響頗深。
世界主義思想也改變了廬隱對日本的看法。她曾于1922年和1930年兩度出游日本,第一次出游時訪問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戲劇家秋田雨雀,而第二次于1930年去日本時,中日關系已經相當緊張。早在1928年日軍出兵山東占領濟南時,廬隱便作了詩歌《弱者之呼聲》和議論文《雪恥之正當途徑》譴責日軍侵略者,并呼吁同胞團結對外,但廬隱并沒有排斥一切與日本相關的人與事。她在1930年的日本之旅中接觸到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廬隱在后來的游記中寫道:
總之我對于日本人從來沒有好感……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了。我就覺得我太沒出息——心眼兒太狹窄,日本人——在我們中國橫行的日本人,當然有些可恨,然而在東京我曾遇見過極和藹忠誠的日本人……他們對待一個異國人,實在是比我們更有理智更富有同情些[7]21。
開闊的國際視野讓廬隱明白,一個國家或者說一個民族,是由無數復雜且具體的個人構成,日本人不是一個抽象的群體,其中有侵略者也有無辜者,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
可是“一·二八”抗日戰爭爆發后,廬隱的民族主義情緒迅速高漲,兩種思想產生了激烈的沖突。首先要澄清的是,廬隱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并無關聯,廬隱生平很少涉及政治,她既不傾向于“左翼”團體,也不支持“民族主義文藝運動”。1933年丁玲被捕后,外界傳聞丁已遇難,廬隱便寫下雜文《丁玲之死》來憑吊同為女作家的丁玲,并在文中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唉,時代是到了恐怖,向左轉向右轉,都不安全,站在中間吧,也不妙,萬一左右夾攻起來,更是走投無路。唉,究竟那里是我們的出路?”[7]233可以說,廬隱的民族主義是一位不屬于任何政治派別的自由作家自發覺醒的思想。張中良也說過:“表現民族主義主題的作品,并不限于來自‘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陣營,也有大量作品出自左翼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傾向的作家以及民間寫作。”[8]而這種普遍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思想的覺醒,實際源自外敵入侵的壓力。民族主義是屬于歷史范疇的現代概念,有學者指出中國民族主義產生的動力:“把中國納入民族國家軌道上并相應地產生民族主義的歷史動力,是世界范圍的現代化過程。”[9]132中國的近現代史基本是被侵略欺壓的恥辱史,不同時期的民族主義有不同內涵,但反帝愛國一直是中國近現代史民族主義的重要主題,而在20世紀20至30年代,隨著日本不斷侵占中國領土并多次挑起戰爭,民族主義情緒的敵對目標更加清晰,反帝愛國逐漸變為反日愛國。
廬隱被民族主義激情推動而創作了《火焰》,其小說內容自然要建構民族主義戰爭的正義性和正當性,但廬隱不得不面臨自身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沖突:一方面,“一·二八”淞滬戰爭是中華民族的自衛反擊戰,反日愛國的立場不容置疑;另一方面,戰場上的敵人也是活生生的普通人,戰爭意味著死亡與反人性。廬隱不能拋棄原有的世界主義觀念,但又要構建小說的民族主義立場,于是陳宣的思想呈現出自相矛盾的局面:
唉,人類為什么一定要有戰爭!一個人的生命已經太短促了……但是我想起敵人無緣無故的侵占了我們的東三省,殺害了我們無辜的人民,焚燒我們工人血汗造成的建筑物……他們逼著我們走進戰爭的漩渦……戰爭之神,雖是露著可怕的獰笑,然而我們卻不能不在那可怕的獰笑里找出路![3]39-40
此時陳宣的內心獨白雖有掙扎,但通過列舉日軍犯下的種種罪行證明“一·二八”抗戰的正義性與正當性,堅定自身作戰的信心。可在隨后不久的戰斗中,陳宣的心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在和敵人肉搏時產生了憐憫之心:
有一個敵兵扭住我滾來滾去,結果滾到一個坑里去……我就勢騎在他的身上,咬緊牙根,用拳頭在他心口用力的捶。突然他噴出血來。我的手莫名其妙的軟了,我看見他眼角有兩顆晶瑩的淚滴。唉,我不能再眼看著他咽氣,連忙從坑里爬出來,我的神經錯亂了[3]86-87。
聽說日本槍決了六百名逃兵后,陳宣感慨道:“唉,我們的敵人,何嘗不是我們的朋友呢!只要毀滅了我們中間的障礙,原可以握著手,親切的互彈心弦中無私的交響曲。造物主創造了人類,何嘗希望人類互相屠殺呢?”[3]124廬隱在面對自身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沖突時,并沒有找到答案,也沒辦法處理這個矛盾。隨著后期戰爭的接連失利,陳宣的民族主義情緒愈演愈下,甚至產生了不知往何處去的想法:
我們急切的追逐那各式各樣的幻想。這是造物主特予我們人類的權利。只要我們從猛獸的漩渦中扎掙出來時,便不知不覺有了這種企求。但是為了人與人互相殘殺的事實繼續著;這種企求只是增加苦痛而已。因為我們所追逐的幻想,只要敵人一聲炮轟,便立刻消失了。這時候我們只有運用我們的四肢,極力的活動著,從毀滅中找出路。也許就是從毀滅中找歸宿。唉,生的希望,有時似完整,有時似破碎的,在不斷的向我這時的心靈攻擊,使我對于多罪惡的世界發生咒詛聲。我這時有一種愿望,假使這世界終有光明的一天,那末我們應當不再繼續演那人殺人的慘劇。不然我們應當把整個的世界毀滅。一些空洞的希望,騙人的幸福,都應當宣告死刑,使一代一代的人們,都在戰爭中扎掙,這是可恥的呀![3]192-193
陳宣所面對的混沌又迷茫的問題同樣也是人類歷史上永恒的難題,戰爭中生命的消逝與人類同情惻隱之心的矛盾該如何解決?廬隱沒有找到理想的答案,可在小說結局,她選擇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大筆一揮強行改變了陳宣的立場:“一股熱烈的血潮,不知不覺又從頹唐的心底涌起。我忘了一切的苦痛,我也不惋惜我變成殘廢;至少我在這世界上,是作了一件值得歌頌的犧牲。這種的犧牲,是有著偉大的光芒,永遠在我心頭閃著亮的呵!”[3]257雖然廬隱在小說結局升華到民族主義的大義主題,但如此強行建構的民族主義立場推翻了陳宣之前所有的思想掙扎與自我斗爭,使陳宣的人物形象徹底崩壞,陳宣的思想與他的行動和經歷完全脫鉤,成了無根之木,最終導致小說的藝術價值失衡。
三、啟蒙到救亡:曲線的女性解放
為何廬隱不惜損傷小說的藝術價值也要如此堅決地在文本中建構民族主義立場呢?“一·二八”抗戰的爆發無疑是最直接的外部原因。1931年夏,廬隱為討生活從杭州搬至上海,經劉大杰推薦去工部局女子中學教書,其丈夫李唯建經舒新城的介紹在中華書局任特約編輯,一家四口在上海愚園坊過著平靜安逸的生活。但好景不長,第一次淞滬戰爭爆發后,廬隱的生活受到多方面的影響。首先商務印書館遭到日軍空襲,廬隱在《小說月報》連載的長篇小說《象牙戒指》被迫中止,只刊載到第十七章,這對向來不留底稿的廬隱來說無疑是重大打擊。她在自傳中提到:“我寫一本十萬字的長篇,在《小說月報》已發表了十分之八九,其余的一部份,不幸因國難而遭焚。——如不然這本書在民國廿一年就可以和人們相見了,現在呢,這本書竟成了焦尾巴狗,不知那天才能把它續起來。”[2]87不止作品遭殃,廬隱身居離戰場不遠的租界,鋪天蓋地的戰時報道和緊張的戰爭氛圍對她的寫作也造成極大的沖擊。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一·二八”淞滬戰爭期間,廬隱只創作了一篇短篇小說《豆腐店的老板》,小說發表在1932年4月的《讀書雜志》。其后廬隱1932年6月15日在孫福熙主編的上海《中華日報·小貢獻》上登有一篇短文《自白》:“近來對于人生似乎有了新發現……開始寫一個長篇,題目還未曾定,但這次上海的炮聲確給了我一個大啟發,也許寫些蘊蓄于我心靈深處的悲嘆與欣喜!”[10]蘇雪林在悼念廬隱的文章中也說過:“廿一年暑假返上海……她那時正寫一本淞滬血戰故事,布滿蠅頭細字的原稿,一張張擺在寫字臺上,為了匆忙未及細閱。”[11]
從歷史背景看,廬隱創作《火焰》無疑是受到了1930年代民族情緒的感染,但是“一·二八”淞滬戰爭究竟給廬隱的創作觀念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廬隱的民族主義立場是跟隨時代情緒一時興起還是立場的根本轉變?要想回答這些問題,得先從廬隱創作《火焰》之前的寫作經歷說起。
茅盾曾形容廬隱的創作就像“‘五四’運動發展到某一階段,便停滯了”,在“‘五四’初期的‘學生會時代’,廬隱是一個活動分子。向‘文藝的園地’跨進第一步的時候,她是滿身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氣的,《海濱故人》集子里牽頭的七個短篇小說就表示了那時的廬隱很注意題材的社會意義。她在自身以外的廣大的社會生活中找題材”[1]。1925年,廬隱的第一任丈夫郭夢良患傷寒去世,此后幾年廬隱帶著女兒四處奔波,以教書、編輯為生。廬隱稱這一時期的作品渲染著更深的傷感,1927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靈海潮汐》。1928年,廬隱搜集一年來的作品編成散文小說集《曼麗》,她在自序中稱:“其中共有十九篇作品,大半都是最近四五個月出產的,是在我頹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閃爍著劫后的余焰,自然光芒微弱!”《曼麗》中曇花一現了諸如《房東》這樣的新題材,但大部分作品仍是廬隱悲哀自憐的延伸。隨后廬隱的好友石評梅與待她很好的大哥相繼去世,廬隱稱自己“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一場大病痊愈后,廬隱這一時期創作的中長篇小說《歸雁》《云鷗請書集》和《象牙戒指》的題材又回到自己友情和愛情的“小閣樓”。茅盾形容道:“廬隱她只在她那‘海濱故人’的小屋子門口探頭一望,就又縮回去了。以后,她就不曾再打定主意想要出來,她至多不過在門縫里張望一眼。”[1]雖然茅盾的評論帶有一定的政治立場,但他的描述基本與廬隱的創作經歷相符,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在1920年到1931年這十二年的寫作生涯中,廬隱的大多作品仍是其作為女性個體的自我表達,記錄著作家作為“五四”時期新女性真實經歷的困境。王富仁曾這樣評價廬隱:“廬隱在傳統的封建家庭里,沒有得到象冰心那樣多的父愛和母愛,這決定了她對封建傳統沒有那么多的留戀,對封建意識和傳統的審美意識沒有那么多的偏愛……她追求著自我的和女性的個性解放,又本能地驚懼于男性的個性解放,因為男性個性意識的片面增長恰恰會給得不到充分個性解放的婦女帶來嚴重的威脅。這種種復雜的意識,廬隱都坦露地表白了出來。”[12]
在創作《火焰》前,廬隱并不是沒有想要轉變寫作風格的意愿,但“五四啟蒙運動塑造了新一代女性的心靈,而新文化的個人主義話語,卻令她們無法完全表達自己”[13]。廬隱從小被家人厭惡、歧視,第一段婚姻嫁給有婦之夫郭夢良,第二段婚姻則是忍受社會輿論的壓力嫁給比她小9歲的李唯建。廬隱好友石評梅的兩次婚姻則都嫁給有婦之夫。正是因為經歷過現實中女性解放的種種挫折,廬隱才選擇堅持寫下女性的痛苦和悲哀,而這也是她作為新一代女性所遭受的真實的痛苦與悲哀。有文章指出:“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艱難處境,使得廬隱女性性別意識的表達顯得尤為難能可貴,尤其是她對‘五四’主流話語傳統的質疑與反思,對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體會和對女性現實出路的艱難求索。廬隱的敘事徹底打破了主流意識形態為婦女解放所編撰的一系列女性神話,代表了女性寫作之初女作家自我性別立場的尋找與確立,即以懷疑的目光審視并追尋女性的出路,深刻認識到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在男權秩序的現實社會里的生存困境和悲劇命運。”[14]廬隱作為“五四”覺醒的女作家,從創作伊始到去世前都在探索中國婦女解放的出路,這尤體現在她的雜文創作上,如《“女子成美會”希望于婦女》(1920年)、《中國的婦女運動問題》(1924年)、《婦女的平民教育》(1927年)、《婦女生活的改善》(1930年)、《小小的吶喊》(1932年)、《今后婦女的出路》(1933年)等文章,都表明廬隱從未放棄對女性解放的思考。
如果處在一個和平年代,實現女性解放無疑是有希望的,但處于一個戰爭頻發的年代,尤其是“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戰爭的破壞性和災難性讓廬隱意識到,如果要實現女性解放,必須先實現民族解放。值得注意的是,《豆腐店的老板》是廬隱在淞滬戰爭期間發表的短篇,小說以第三人稱講述了豆腐店老板在戰爭中的經歷,贊頌了普通百姓募捐物資的愛國精神。上海百姓自發募捐支援十九路軍的行為,讓廬隱看到了啟蒙的可能與希望。而從文本出發,《豆腐店的老板》與《火焰》兩部小說中罕見地幾乎沒有出現女性角色。《豆腐店的老板》中,女性只作為戰爭的遇難者出現,而《火焰》中,除戰爭中遇害的婦女外,只有兩個未出場的女性角色占了寥寥幾次筆墨:遠在家鄉的母親和未婚妻。二者形象只出現在信件和陳宣的回憶中。廬隱有意避開女性角色的描寫,正是因為在原始野蠻、廝殺拼力氣的戰爭中,女性永遠是被壓迫的受害者。曠新年指出:“中國現代的各種‘解放’,不論是個人解放、婦女解放,還是階級解放,都與民族解放的目標聯系在一起……個人并不是憑空地獲得解放,個人并不是被個人所解放,而是被國家從家族之中解放出來,砸碎家族的枷鎖,最終是為了將個人組織到國家的現代結構之中去。”[15]廬隱也在自傳中提到,自己寫完《象牙戒指》后,創作風格發生了大轉變:
在這個大轉變之后,我居然跳出了悲哀的苦海。我現在寫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換句話說,我的眼光轉了方向,我不單以個人的安危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我不只為我自己一階級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為一切階級的人鳴不平,我開始建筑我整個的理想[2]97-98。
廬隱的《一個情婦的日記》結尾,美娟面對愛而不得的仲謙所尋得的解決方法為“我要完成至上的愛,不只愛仲謙,更應當愛我的祖國!”[16]351932年之后,廬隱增加了針砭時弊的雜文創作,發表了大量尖銳諷刺的作品,如《災還不夠》《屈伸自如》《監守自盜》等等,積極參與時政時事。李唯建評價廬隱這一時期作品已“由酣恣多情的作風一變而為客觀的分析的寫實的了”[16]146。
四、結語
《火焰》是廬隱創作風格和思想立場的一次重要轉向,也是她決心走出“海濱故人小屋子”的標志之作。這部以戰爭紀實為基礎的自敘傳小說呼應了20世紀30年代激流洶涌的民族主義時代情緒,作品中多處表現戰爭紀實的細節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一·二八”淞滬戰爭后,廬隱強烈地意識到,民族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故文中構建的矛盾的民族主義立場正是廬隱曲線實現女性解放的策略選擇。誠然,《火焰》的藝術并不那么成熟,但并不乏許多同時代戰爭文學甚至后來許多戰爭小說都未包含的閃光點,如對戰爭和人性的反思等。因此,《火焰》在廬隱的創作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其在戰爭文學史和史料方面的價值,也有待被再次發掘與重估。
注釋:
① 信件由陸錫禎載于《華安》雜志1934年第8期,其內容為:“承蒙惠顧失迎,甚歉!茲由郵寄上拙作《火焰》十章,請查找妥為保存為感,蓋敝處無副稿也。其余六章稍遲當續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