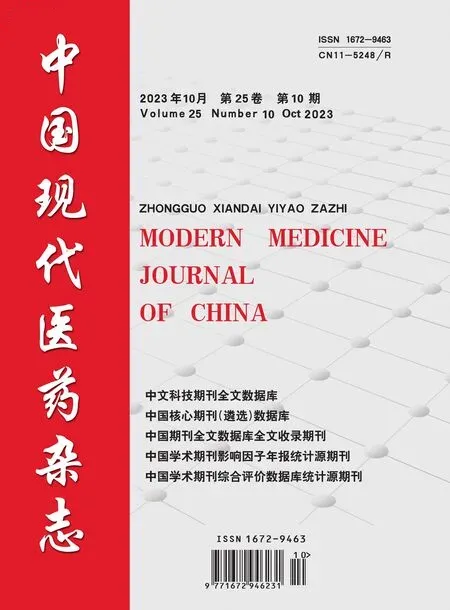單極射頻聯合膠原酶在腰椎間盤突出癥中的應用效果分析
魏尊 王勝利 朱慧娟
腰椎間盤突出癥是腰椎退行性改變的一種疾病,臨床較為常見,發病率較高[1,2]。出現腰椎間盤突出癥的患者常表現出腰腿疼痛、坐骨神經痛等癥狀,而出現以上癥狀是由于腰椎間盤出現異變及纖維環破裂而造成[3,4]。多數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剛開始則出現腰部疼痛,隨著病情的發展患者自身活動受限、腰腿疼痛,對日常生活及活動造成嚴重影響[5]。臨床常采用手術、推拿等方式治療,手術療效顯著,但創傷性較大,并發癥發生率較高,影響患者預后。推拿為保守治療,雖具療效,但其起效較慢。單極射頻通過射頻電極形成電場,通過正負極的快速轉變,升高組織溫度,產生能量,分解髓核細胞分子,抑制糖蛋白,緩解病情[6]。膠原酶能夠對膠原蛋白進行溶解,縮小突出物,降低突出物對神經根所產生的壓迫感[7]。本研究將兩種方式進行聯合應用,分析其在腰椎間盤突出癥中的應用效果。
1 材料與方法
1.1 一般材料選取2019 年6 月~2022 年6 月于我院進行腰椎間盤突出癥治療的86 例患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其分為對照組和研究組,各43 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突出物矢徑、突出位置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對比
納入標準:①符合中華醫學會骨科學分會等多個專家組對腰椎間盤突出癥的診斷標準[8];②患者出現不同程度的腰腿痛;③入組患者無手術禁忌證;④臨床病例資料齊全。
排除標準:①既往進行過相關腰椎類手術者;②合并嚴重的骨質疏松癥者;③存在嚴重的傳染性、血液性以及相關免疫性疾病者;④存在嚴重的精神障礙性疾病者;⑤臨床病例資料不全者。
1.2 治療方法對照組采用膠原酶治療。輔助患者取仰臥位,在患者腹下位置墊抱枕,使腰椎呈現后凸狀態,通過對患者腰椎病變部位進行影像學觀察并標記后行常規消毒。于棘突旁2cm 處進針,注射造影劑2mL,X 線觀察造影劑分布情況。注射2%利多卡因5mL,并在半小時內觀察全脊麻情況。將20mL 的生理鹽水分3 次快速注入,以松解黏連。隨后注入3mL 的膠原酶,注射后觀察40min,如患者未出現不適,則可以將穿刺針拔出,對穿刺點進行止血,無菌敷料覆蓋。
研究組采用單極射頻聯合膠原酶進行治療。單極射頻:取薄枕墊于患者骨盆前房位置,輔助患者取俯臥位,對發病部位進行消毒、檢查。依照患者病情確定進針點,從小關節內側緣入針,到達病變部位側隱窩后,調節針尖所在突出物位置,進行造影,置入射頻電極并進行固定,電極阻抗設置為150~250Ω。電刺激測試:電刺激參數設置10Hz、1.5mA,對患者進行低頻刺激,電刺激后觀察患者的肌肉震顫情況,如出現肌肉震顫則參數調整至無肌肉震顫。隨后緩慢升溫,進行反復治療。膠原酶治療同對照組。
1.3 指標檢測
1.3.1 手術相關指標 對兩組患者的手術時長、臥床天數、住院天數進行統計記錄。
1.3.2 疼痛因子、炎癥介質 在治療前1d 及治療結束后1d,于清晨7 時抽取患者空腹靜脈血5mL,離心機行上清分離,分離的血清-80℃保存。采用酶聯免疫(ELISA)法檢測血清前列腺素E2(PGE2)、環氧合酶-2(COX-2)、白細胞介素-17(IL-17)、C 反應蛋白(CRP)、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和神經肽P 物質(SP)水平。
1.3.3 腰椎關節活動度 治療前1d 及治療結束后1d,輔助患者向地面進行彎曲,盡可能用手指接觸腳趾,以測量腰椎前屈度;患者盡可能向后彎曲,手指向后腰方向發力,以測量腰椎后屈度。
1.3.4 腰椎功能 治療前1d 及治療結束后1d,采用日本骨科協會(JOA)評分量表[9]、Oswesthy 功能障礙指數(ODI)評分量表[10]對患者自身的腰椎功能進行評估。JOA 評分量表總分為0~30 分,病情程度<10 分為輕度、10~20 分為中度、21~30 分為重度,分值越高說明患者腰椎功能越差。ODI 評分量表中涵蓋了疼痛、行走、睡眠等10 項內容,評分為0~50分,分值越高說明患者的腰椎功能障礙越嚴重。
1.3.5 臨床療效 顯效:炎癥基本消失,腰椎功能顯著恢復,疼痛緩解>75%,疼痛發作頻率與時間減少>70%;有效:炎癥得到一定程度減輕,腰椎功能有效恢復,疼痛緩解≥50%,疼痛發作頻率與時間減少>40%;無效:患者各功能和指標未得到改善。
1.4 統計學方法使用SPSS 26.0 軟件分析研究數據。計量資料使用進行描述,組間比較行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表示,組間比較行χ2檢驗,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手術相關指標比較與對照組相比,研究組手術時長延長,但臥床天數、住院天數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手術相關指標比較()

表2 兩組手術相關指標比較()
2.2 兩組疼痛因子水平比較兩組治療前疼痛因子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與對照組相比,研究組PGE2、SP、COX-2 水平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疼痛因子水平比較()

表3 兩組疼痛因子水平比較()
2.3 兩組炎癥介質水平對比治療前兩組炎癥介質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與對照組相比,研究組IL-17、CRP、TNF-α 水平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炎癥介質水平情況對比()

表4 兩組炎癥介質水平情況對比()
2.4 兩組腰椎關節活動度對比兩組治療前腰椎關節活動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與對照組相比,研究組腰椎前屈度、腰椎后屈度水平均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腰椎關節活動度對比()

表5 兩組腰椎關節活動度對比()
2.5 兩組腰椎功能評分對比兩組治療前腰椎功能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與對照組相比,研究組JOA 評分、ODI 評分均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6 兩組腰椎功能評分對比()

表6 兩組腰椎功能評分對比()
2.6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治療后研究組臨床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7。
3 討論
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臨床較為常見的疾病之一,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其臨床癥狀較為嚴重,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11,12]。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發生機制較為復雜,并且隨著病情的不斷進展,患者出現疼痛的原因也各不相同[13]。臨床相關研究認為,腰椎間盤突出癥造成的疼痛程度與炎癥情況及機械刺激等具有緊密關聯。
研究指出,患者椎體位置常存在SP、神經肽Y(NPY)等相關神經肽,能調節機體神經系統,刺激肥大、巨噬及多形核細胞產生,釋放炎癥因子,加重炎癥反應[14]。PGE2為臨床常見疼痛因子,其水平升高或降低能造成疼痛閾值的降低、升高[15]。COX-2與疼痛程度也具有相關性,參與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發生發展,其水平升高影響PGE2水平[16]。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PGE2、SP、COX-2 水平低于對照組,提示單極射頻通過射頻電極形成電場,快速轉變正負極,升高患者相關組織溫度,產生能量,分解髓核細胞分子抑制產生的糖蛋白,減輕患者自身疼痛程度,緩解病情。通過手術將膠原酶注入椎間盤內,溶解膠原蛋白,縮小突出物,降低突出物對神經根的壓迫感,改善病情。表明兩者結合能顯著降低患者自身疼痛程度。
IL-17、CRP、TNF-α 為常見的炎性因子,參與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發生發展,炎癥可造成腰椎關節活動程度受限[17,18]。本研究結果證實,治療后,兩組的炎癥因子水平均降低,且研究組低于對照組,兩組腰椎活動度升高,且研究組高于對照組(P<0.05)。膠原酶溶解術是將膠原酶注射于患者的椎間盤及突出物內,對椎間盤內的膠原蛋白產生特異性水解作用,從而對存在于椎間盤髓核內的膠原蛋白進行選擇性溶解,對其突出的髓核組織也能夠產生溶解作用,以此降低患者疼痛程度,減輕炎癥反應,恢復患者腰椎關節活動度。單極射頻是利用靶點熱凝作用形成射頻電極電場,將射頻的正負極進行快速轉換,使組織溫度提升,產生能量,對髓核細胞分子產生分解作用,變性突出的髓核被分解,解除壓迫感。同時溫熱效應能夠緩解患者的疼痛,促進血液循環,減輕炎癥反應。該方法對患者產生的創傷性較小,可較好地改善腰椎關節活動度和腰椎功能。
JOA、ODI 評分是臨床進行腰椎功能評估的常用量表,能對患者當下的腰椎功能進行準確反饋,臨床信效度較高。臨床研究證實[19],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常采用手術及保守方案進行治療,單純手術具有較高的創傷性,而保守治療對較為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臨床效果不佳。所以,選擇具有安全性的治療方式對于腰椎間盤突出癥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通過兩種方法對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進行治療,結果顯示,研究組JOA、ODI 評分低于對照組,并且研究組臨床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由此表明,采用單極射頻聯合膠原酶對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進行治療,能顯著改善患者的腰椎功能。分析其原因可能為單極射頻治療過程中能在椎間盤內形成射頻熱凝電場,電極在一定范圍內可發揮重要作用,固縮膠原蛋白,降低椎間盤內產生的壓力,變性髓核并凝固,解除壓迫,通過抑制椎體內的致痛、炎癥因子,減輕神經痛覺感受,從而緩解患者腰椎功能[20]。故此,兩者聯合能夠達到較好地改善腰椎功能的作用。
綜上所述,采用單極射頻結合膠原酶對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進行治療,其臨床效果確切,能降低疼痛情況,顯著改善患者機體內所出現的炎癥情況,顯著提升患者腰椎關節活動度以及腰椎功能,改善病情,值得臨床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