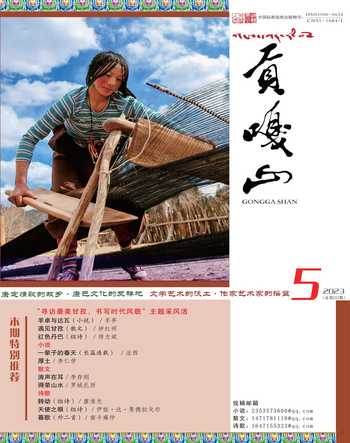羊卓與達瓦(小說)
羊亭
隨著地勢變化,隧道開始密集起來,光線忽明忽暗,仿佛白晝與黑夜急速轉(zhuǎn)換,讓人昏昏欲睡。羊卓調(diào)整了一下坐姿,雙膝抵住前方椅背,上身盡力向后靠,然后閉上雙眼,希望打個盹,車子就將駛向一片開闊地。但是光亮一閃而過,再次進入隧道,幽暗竟然長達十余公里。
車子又破又舊,故障不斷。他們從早上八點出發(fā),原計劃五六個小時車程,可一路走走停停,現(xiàn)在已是下午四點,羊卓心想,天黑之前能到就不錯了。前天晚上,父親興沖沖告訴羊卓,他總算找到一輛商務車,司機順道也去甘孜,不但享受包車服務,還只收客車一半車費。早上來接他們時,羊卓明白了為什么只收半價——這車子都快散架了,而且車上坐滿了人,他們好不容易才在最后一排擠下。隧道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車子異響也沒完沒了。羊卓睡不著,他很擔心,要么這條隧道沒有盡頭,要么車子再次出現(xiàn)故障,他們被困在幽暗里。
終于又看到微光,逐漸變大,逐漸清晰。車子駛出隧道,剎那間,光線強烈得如瀑布傾瀉,大家一時難以適應,都紛紛瞇縫著眼。幸好道路被緊緊夾在兩山之間,而山勢巍峨,像史詩中巨人聳立,不時遮擋些陽光,于是強光隨車速閃爍,才不至于讓人無法直視。
羊卓問父親:“已經(jīng)進入高原了嗎?”
父親沒動,輕輕“嗯”了一聲。上車沒多久他就暈車,中午飯也沒吃。
“什么時候才到草原?”
父親仍閉著眼,敷衍道:“應該快了。”
其實問父親多此一舉。父親也是頭一回來,車子到哪兒了,什么時候進入高原,他不但不知道,也沒有任何經(jīng)驗。
車子在盤山公路上艱難前行,不時發(fā)出咯吱聲響。車上有人問司機,這么個走法什么時候才到道孚。司機沒有回答,罵了句粗話便剎車下去,前前后后看了看,上來時滿臉陰云,大家也就沒好再問了。車子吭哧吭哧,像蝸牛爬行,排氣管突突冒著白煙。
上到一處觀景臺,司機停車,招呼大家去上廁所,他自己則又去檢查車子。上完廁所出來,羊卓聽到一陣歡呼。觀景臺那里擠滿游客,女人們搔首弄姿,男人們張開雙臂,相機、手機咔嚓咔嚓,記錄下一時美好。他們走后,地面騰起陣陣沙塵,隨風漫卷,久久未定。
羊卓朝前望去,原來他們不單是拍自己,還有雪山。遠山層層疊疊,巍然森然,有凜凜之氣,雪山便聳峙在最高處,夕照下閃閃發(fā)亮。雪山面前,云霧也只能仰視,臥在半腰,謙恭地做著陪襯。山頂上雪線分明,隨著日光流轉(zhuǎn),色彩也不停變幻,一會兒鎏金,一會兒橙黃,一會兒橘紅。羊卓完全被震撼了,他們居住在丘陵地區(qū),山丘倒是不少,卻從沒目睹這般雪山霧海。難怪這里世代相傳,每一座山都是一個神。神山,神靈,怎么稱呼都不為過。
上車后,大家七嘴八舌議論起來,有人說那是雅拉神山,也有人說是貢嘎山,他們對此地一無所知,卻裝作了如指掌。
又行駛了十來公里,車子突然停下來。司機嘗試了幾次,仍然沒有反應。他攤開雙手,無可奈何地說:“打不燃火,沒法走了。”
“那怎么辦?總不能把我們撂在這荒郊野外!”前排有人表達不滿,“你已經(jīng)耽誤了我們很長時間了。”
“只能看有沒有順風車。”司機點了支煙。
“我們不坐順風車,我們給了你車費,你就得把我們送到。”
“車子走不了了,我怎么送到?”
“退錢吧,對,退錢。”
“只能退一半,只有四五十公里就到了。”
天色漸漸暗下來。剛開始還有車經(jīng)過,大家急著招手,卻沒有車子停下來,后來車越來越少,大家也越來越焦慮。沒辦法,司機只得聯(lián)系車子,但最快也要三個小時才到。
父親說:“我們不去道孚了,我們直接去巴茸。去巴茸還有多遠?”
“不遠了,”司機朝一個方向指了指,“要是從那邊走直線,大約二十多公里。”
父親不愿再等了,他和羊卓取下行李,準備步行去巴茸。羊卓本有點抗拒,等三個小時就能坐車,卻要拿著大包小包走那么遠,但目擊周遭一切都那么新奇,即便走夜路,也會有一番美妙體驗,于是他和父親上路了。
不多時天就黑了。或許海拔越高,距離天穹越近,此地月光分外皎潔。父子倆走在草地里,青草上掛滿露水,猶如漫游茫茫銀海。星星也大而耀眼,天地間一片清透澄明。縱然草原廣袤無垠,眾神一樣將它悉擁入懷。每走一步,羊卓都覺得內(nèi)心在被洗滌。身處圣境腹地,實在沒有道理不由衷感到暢然歡喜,可父親卻一路唉聲嘆氣。暈車加上氧氣稀薄讓他疲憊不堪,像大病初愈后一樣虛弱。
母親去世后,衰老便找上了他。短短幾個月,剛過不惑之年,父親看上去卻比實際年齡長了十多歲。那些日子,他每天把自己關(guān)在臥室里足不出戶,用與世隔絕來思念母親。直到有一天,二叔突然托人從川西高原帶來一封信,他才步履蹣跚地走出房門,無限感慨地說:“除了他,我再也沒有其他親人了!”說這話時,信紙在他手中瑟瑟顫抖,他絲毫沒有顧及羊卓是什么感受。
那封信里,二叔先是對母親作了一番贊許,雖有些虛情假意,但看得出他已經(jīng)盡力了,并為她過早離開人世深感遺憾,讓父親節(jié)哀,然后才是重點。他說,如今他各種生意都做得風生水起,在巴茸——個藏族小村落,有幾百頭羊急需人手照料,思前想后,再沒誰比父親更讓他信任了。
父親已經(jīng)被羊卓甩在后面好遠。月光下,他變成一個小黑影,隱隱約約在那里蠕動。羊卓接著往前走,獨享這份美好與寧靜。當全身熱汗沁溢,衣裳被打濕,羊卓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四下空曠寂寥,心跳敲擊出咚咚聲響。足足過了一刻鐘,父親才氣喘吁吁地趕來。
他也往地上一坐:“我走不動了。”
“歇一會兒吧。”羊卓說。
“我們走了多久了?”
“有個把鐘頭了。”
“應該快到了,”他長長吐了口氣,“我已經(jīng)好多年沒這么走過了。”
羊卓沒有搭話。遠處傳來斑鳩咕咕叫喚,夜空有流星劃過。他想應該趕緊許個愿,但一時間又沒有什么愿望可許。
過了好久,父親仍然喘息不定,還不自覺地嗯嗯啊啊清嗓子。他自己顯然沒有意識到這點,兀自從口袋里掏出煙葉裹了支煙,剛抽一口便咳嗽起來,而且一發(fā)不止,那境況好像非把身上某個器官咳出來才肯罷休。
后來,父親終于緩過來了,卻并不把煙掐滅,而是讓它自己慢悠悠地燃下去。他說:“明天再走吧,我太累了。”
羊卓說:“也許要不了多久就到了。”
“你看這里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像有村子嗎?”
“我們不會走錯方向了吧?”
“天亮再走吧,不然我們越走越遠了。”
這樣也好,羊卓從行李包里拿出帆布鋪開,枕著雙臂就睡了,但一直迷迷糊糊沒有睡著。他想起他還很小時,夏日夜晚,母親總喜歡在外面鋪一床竹席,他們躺在上面,她有時唱歌,有時講白話,晚風拂過,無限清涼……
不過這里談不上清涼。他們雖有準備,卻未料草原之夜如此冷。羊卓加了幾次衣服,還是冷得發(fā)抖,一整夜都睡得很不安穩(wěn)。
不知是什么時辰了,遠近傳來各色鳥叫。月亮和星星不見了,天已微明。近旁,一只百靈鳥好奇地歪著腦袋打量羊卓,少頃,小家伙發(fā)現(xiàn)羊卓也正望著它,于是蹦跳兩下,迅速插入天空,發(fā)出一串婉轉(zhuǎn)的歌聲。父親也醒了,正支著胳膊艱難地伸腰,像一只巨鼠。
吃了些面包,他們繼續(xù)上路。天色漸漸放亮,開始有了熹微陽光。
父親在后面問:“有人家了?”
“是遠山。”
“我好像聞到煙火氣了。”
這回他說對了,他們又走了一程,山下確乎升起了裊裊炊煙。那些山看著近,他們卻又走了一個多鐘頭。快到中午,他們終于進村了。
正好有個中年男人走來,一聽父親說巴茸,他狐疑地皺了皺眉頭,顯得有些不太情愿。父親一再追問,他才一邊甕聲甕氣地說話,一邊用手比畫著環(huán)顧村莊。他一口漢話很不標準,但羊卓和父親都明白了他話中的意思:這里就是巴茸。
二叔遠沒羊卓想象中熱情,好像他根本沒有寫過那么一封信一樣。二叔草草和他們吃了頓飯,交代完父親要做什么事,就開著越野車走了,他說還有好多生意在等著他呢。看得出父親有很多話想和他說,但除了寒喧什么也沒有說上。車子引擎聲已消失很久,父親還站在門口,他有些失落地喃喃自語:“這個老二,生意真是越做越大了!”
就這樣,他們在巴茸安頓下來。
父親白日里一大早就趕著羊群深入水草豐茂處,晚上再浩浩蕩蕩地趕回來。開初有時羊卓也會跟他一起,但草原再怎么新奇,也經(jīng)不住時日消磨。何況他們常常一整天都悶不作聲——父親趕羊,羊卓看云。過了十來天,他便不再跟去了,父親也沒問他原因,好像本就該這樣才好。
羊卓開始無所事事地在村子里閑逛。雖然他們來這里已經(jīng)有些日子,但和村民們并無多少往來。他們遠看著羊卓,不知竊竊議論什么;小孩子則躲在暗處,雙眼漆黑發(fā)亮地瞪著他,仿佛他是一只怪物。
回家途中,羊卓遇見一個男孩,看上去年齡和他相仿。男孩站在路中央,臉蛋通紅,莫名透出幾分敵意:“嘿,你從哪兒來?”
羊卓沒有理他,準備從路邊側(cè)身過去,他卻一把抓住羊卓,氣勢洶洶地說:“不準過!”
“憑什么?”羊卓甩開他。
“就是不準過。”
他把語氣提得老高,不可理喻地張開雙手,擺出個“大”字,既蠻橫又霸道。
他們扭打在一起,不知從哪里跑來其他幾個小孩,吸溜著鼻涕站在一旁吶喊助陣。那男孩力氣很大,但不懂得巧用,也因他好勝心太強,過于小瞧羊卓,最后一個趔趄,被羊卓重重摔倒在地。
他爬起身,吐了口唾沫。羊卓以為他會因此惱羞成怒,不想他卻笑起來,一反蠻橫態(tài)度:“你也會摔跤?”
不等羊卓開口,他又說:“臂力真不錯!不對,你剛才不全是臂力。”
羊卓冷冷地說:“你搞錯了,我根本不會摔跤。”
“騙人。”
羊卓沒有騙他,但他既然不肯信,羊卓也懶得多費唇舌。
“你敢不敢什么時候再較量一回?”
他眼里充滿期待,可羊卓什么也不想說,只想快些回去。羊卓經(jīng)過他身旁時,他沒有再攔住,而是讓到了路邊,還頗為平和地問:“嘿!你叫什么名字?”
羊卓本不想告訴他,但他也不清楚當時出于何種考慮,他說:“我叫羊卓。”
“羊卓?聽上去像個藏族名字啊!”男孩說,“我叫達瓦,意思是月亮。”
第二天清晨,羊卓還沒起床,外屋傳來敲門聲,還不時有人叫他名字。父親早已出去,屋里陳設與以前家里別無兩樣,每天早上醒來時,他都感到一陣彷徨,不知究竟身在何處。外面喊聲陌生、唐突,連發(fā)音都顯得生澀。打開房門,正是頭天那個達瓦。
一看到他羊卓就覺得胸口發(fā)悶,好在他沒有一開口就提摔跤,而是和羊卓相熟已久般,大聲問道:“你怎么現(xiàn)在才起來?”
羊卓什么也沒有說,折身回到屋里。他也跟了進來,起先還毫無拘束地東瞧西看,嘴里不停地說著什么,后來,他望著墻上母親的遺像,立刻就安靜下來了。
他看了好半天,才遲疑不決地問:“她是你親人?”
“我母親。”羊卓說,“半年前,她得肝病去世了。”
“天哪,她還那么年輕!”達瓦驚訝道,“我常聽老人講,年紀輕輕就過世的人是因為得罪了魔鬼。”
他說的大概是實話,他們總喜歡把死亡或厄運同魔鬼扯上關(guān)系,但聽了卻叫人很不舒服。正當羊卓盤算要怎么向他下逐客令時,他從胸口衣服里掏出一串念珠,捧在手心遞給羊卓:
“這是雪頓節(jié)一位上師送給我阿爸的,他后來給我了,我把它送你。它會像菩薩一樣庇佑你們。”
這突然讓羊卓感到手足無措——接下,有點奪人所好的意味;不接,他伸出的雙手就那樣等待著。最后是他硬塞給羊卓的。羊卓覺得很不好意思:“給我了你怎么辦?”
“沒事,”達瓦樂呵呵地說,“我可以再求一串。我認識納木寺的丹增上師,每次去他都給我許多好吃的,有一回吃多了芒果,弄得我舌頭又癢又麻。他是個非常好玩的老頭兒,好像總在笑一樣,其實是牙齒掉光了。”說著,他癟嘴模仿起來。
過了一會兒,達瓦又問:“對了,你去過后面的森林沒有?”
羊卓搖搖頭:“后面不都是山?”
“你不曉得山背后有一片森林?”達瓦興致勃勃地說,“也好,我可以帶你去見識一下。草叢里有很多畫眉的巢,說不定我們還可以捉幾只小畫眉回來。我以前就養(yǎng)過畫眉,還有老鷹,但都被阿爸放生了。”
他們上了彎彎曲曲的小路,不多時便已到達半山腰,山上生長著叢叢荊棘和雜草。達瓦走在前面,不停地對羊卓說森林的奇妙,好像他平日的所有樂趣都和森林有關(guān)。這讓羊卓平添了幾分期待。
羊卓問:“森林里有沒有狼?”
“狼?”達瓦非常吃驚,“你在說什么夢話?我們這里早就沒有狼了,不僅沒有狼,連野兔、獐子、野豬這些都沒有了。”
說話間,他們已經(jīng)到了。說是森林,其實不過是一片大點的林子,一眼就能望盡前方邊際。達瓦拉著羊卓的手,一陣小跑沖進林里。他們小心翼翼地翻開每一個蓬松的草叢,尋找畫眉的巢,但一個也沒有找到。達瓦非常失望,拿根棍子朝幾棵狗尾草撒氣。羊卓恍惚聽到了嘩嘩水聲,四下張望,卻不清楚聲音從何處傳來。
“是瀑布。”達瓦說。
達瓦領(lǐng)著羊卓穿過林中一座小丘,瀑布便在眼前了。水流從十多米高的峭壁垂落下來,陽光照在水潭上,形成一道小小彩虹,氣勢并不宏大,一切卻生動美麗至極。羊卓在瀑布之下,頓時覺得心腸被沖刷得干干凈凈,胸中能容下所有哀苦與喜樂。
達瓦仿佛還在為沒有找到畫眉鳥巢悶悶不樂,心不在焉地和羊卓在水潭邊坐下,將雙腳伸進水里。
“旺姆姐姐!”達瓦突然喊道。這時,羊卓看到一個女孩從林子里朝這邊走來。
達瓦早已站起身。女孩走近了,他驚喜地問:“你怎么在這里?”
那個叫旺姆的女孩說:“我剛?cè)ド掷锊赡⒐搅恕!彼种刑嶂鴹l簍筐,裝了滿滿一筐蘑菇。
“這是羊卓,”達瓦指著羊卓,“我的好朋友。”說完,他又向羊卓道,“她是我旺姆姐姐。”
大概覺得羊卓是個生人,旺姆害羞地笑了笑。羊卓還沒來得及起身向她打招呼,她已經(jīng)走了。
達瓦重新坐下來,顯得異常興奮。他向旺姆走遠的背影張望良久,然后問羊卓:“你覺得旺姆姐姐相貌如何?”
老實說,剛才羊卓并沒看清楚,但又不好掃他的興,于是點頭說“自然不錯”。
達瓦對羊卓的回答非常滿意,也跟著不停點頭。過了一會兒,他又神神秘秘地說:“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但你不能和別人講。”他補充道,“我可拿你當朋友才告訴你的,這話我從沒對人講過。”
既然達瓦都這么說了,羊卓也就再沒必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說“這話就是爛在肚子里我也不和人講。”
“我喜歡旺姆,”羊卓注意到達瓦沒有加姐姐兩個字,“等長大了,我一定要娶她。”
羊卓也對達瓦說了他的秘密。譬如那個被他稱作父親的人并非他的生父,他是因為愛慕母親的美貌才接納了他,不過對母親倒真心實意地好;還有他和父親終日沉默相對,說不定哪天就會爆發(fā)一場戰(zhàn)爭,也可能他正暗中籌劃要怎么擺脫這個沒有血緣關(guān)系的兒子……
之后,羊卓和達瓦沒事就常常去瀑布那里。他們還比試過摔跤,但達瓦已經(jīng)領(lǐng)會了其中要訣,所以羊卓再也沒有贏過他,他也終于相信羊卓確實沒有學過。有時羊卓也會獨自一人去。在水潭邊找一塊干凈的石頭躺下,讓白色瀑布充盈整個視野,耳邊只有風聲和水聲。
一個午后,在那里羊卓又見到了旺姆。她還是和上次一樣,提著柳條簍筐,只是筐里沒有幾朵蘑菇。她也不像上次那樣害羞了,而是來到瀑布下面,柔聲細語地和羊卓說話。
“怎么只有你一個人?”她說,“達瓦呢?”
羊卓說:“今天我就想一個人來,達瓦有時像個嘰嘰喳喳的小鳥。”
旺姆無聲地笑了,好像害怕弄出聲響會驚擾了誰。她也把腳伸到水里,安靜得如同遠方的白云。他們離得很近,這回羊卓才好好把她看清楚,不禁在心中贊嘆達瓦小小年紀居然有不俗的眼光。她坐了很久,但他們話卻說得極少。后來她說她要走了,得去森林的另一邊看看,那里也有河流經(jīng)過,土地濕潤,是片長蘑菇的地方。
旺姆剛走達瓦就來了。他喘著粗氣,臉紅得厲害。他走到羊卓面前,什么話也不說就撲了上來。羊卓以為他又要玩摔跤,可他一點不給羊卓還力的機會,直到羊卓被推進水潭,才明白他絲毫沒有玩的意思,而是硬生生地在搏斗。好在羊卓懂水性,但周身上下都濕透了。
羊卓爬上岸,沖達瓦吼:“你發(fā)什么瘋?”
達瓦也朝羊卓吼道:“你太無恥了!你明明曉得我喜歡她,還和我搶!”
羊卓明白了達瓦的意思,感到好笑又無奈:“我們什么也沒有,只隨便說了兩句話。”
“誰信你,騙子!你們這些人心里都住著魔鬼!”
他們誰也沒再理誰,雙方都覺得各自有理。羊卓發(fā)現(xiàn)衣服的顏色有些不對——明明是白色,現(xiàn)在卻成了暗紅。一看水潭,里面的水也變得暗紅,紅褐色的瀑布奔流而下,洶涌如血。日光下,彩虹變得離奇,一股異樣的氣味在四下彌漫開來。
這時,幾個喇嘛走過來,最前頭那個已經(jīng)老得不成樣子,滑稽地癟著無牙的嘴,眉宇間卻無比莊重。他們走到達瓦跟前,紛紛匍匐在地,虔誠地用額頭輕叩綠草茵茵的地面……
若干年前,上一世活佛圓寂時,丹增喇嘛已得到兆示:在這天的瀑布下面,神跡將會顯現(xiàn),轉(zhuǎn)世靈童也將在這里被找到。于是,瀑布和彩虹顏色的變化被視為吉祥的征兆。
——自此,達瓦成了納木寺的活佛。
過了段時日,二叔回來把羊都賣掉了。他說他在上游的一家化工廠出了些問題,需要大量資金。他把零頭中的零頭分給了父親,有點施舍的意味,然后說:“巴茸沒有我的生意了。你們要是想留在這里,房子我就不賣了。”說完他就走了,一如既往地匆忙。
他走后,父親說:“羊還沒長大呢,怎么就能賣!”從此便一病不起。生病讓他變得嘮叨起來,成天說自己肺里爛了個洞、時日無多這樣的話。他也漸漸開始依賴羊卓了,老淚縱橫地握著羊卓的手:“羊卓,我的孩子,”有些話他好像羞于啟齒,但最終還是說了出來,“現(xiàn)在,你是我唯一的親人了。”
一天,納木寺的活佛突然出現(xiàn)在家門口。沒隔多長時間,昔日的達瓦已出落成一個十足的僧侶,讓人心生敬畏。
達瓦說:“聽旺姆姐姐說你阿爸病了,可好些了嗎?”
羊卓說還是老樣子,然后請他進了屋。
活佛為父親摸頂賜福,并作了長長的祈禱,還留下念珠和一包草藥——每個步驟他都做得有條不紊。
送達瓦離去時,達瓦對羊卓說:“上回的事真是抱歉。我都知道了,全怪我無理取鬧。”
“活佛……”羊卓支吾著不知說什么好。
“要是你愿意,還是叫我達瓦吧。”過了一會兒,達瓦問羊卓,“我們還是不是朋友?”
羊卓肯定地點了點頭,然后他們都笑了。
達瓦又說:“再去看看瀑布如何?”
“好。”
他們走過荊棘叢生的山間小路,像鳥一般飛向蔥郁的密林深處,去尋找那安謐祥和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