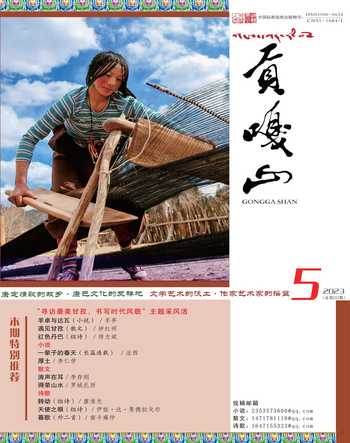又見(jiàn)合歡樹(shù)(外一篇)
陳秀梅

在雅礱江大河邊的山區(qū),合歡樹(shù)是常見(jiàn)的一種樹(shù)。比較奇特的是,合歡樹(shù)很少長(zhǎng)在荒山野嶺,它們更樂(lè)意長(zhǎng)在有人出沒(méi)的地方,如公路旁,莊稼地的土坎邊。在我的印象里,合歡樹(shù)都不是特意栽種的,它們好像天然就長(zhǎng)在土里,純屬野生。
這種樹(shù)與人走得特別近,也很容易被人視而不見(jiàn)。沒(méi)有人去給合歡樹(shù)鋤草,施肥。它們親近人卻不依賴人。它們唯一依賴的是腳下的土地和頭頂?shù)年?yáng)光雨露。
合歡樹(shù)葉纖細(xì)如羽毛,但它一樣綠蔭如傘;它的花絲粉紅,清香襲人,花形如扇,毛茸茸的,每一朵都如女子耳朵上的吊墜,微風(fēng)拂過(guò),搖曳生姿。
這棵合歡樹(shù)長(zhǎng)在別人家的土地里,它的主人是我的發(fā)小。我每次從外縣回鄉(xiāng),總要到這棵樹(shù)下走走,渴望與發(fā)小偶遇,可是每次都帶著失望而歸。偶遇是一件多么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
這棵合歡樹(shù)已經(jīng)長(zhǎng)得很大,主干粗壯了許多,樹(shù)冠呈圓形,在冬天也能遮住偏西的陽(yáng)光,村里的婦女,喜歡三五成群地在樹(shù)下盤膝而坐,做些諸如繡花,做鞋墊一類的手工活。只有我喜歡盯著合歡樹(shù)出神。
那時(shí),正值六月,合歡樹(shù)開(kāi)闊的樹(shù)冠,枝葉紛披,粉花散如絲,團(tuán)若云。我跟發(fā)小經(jīng)常爬上樹(shù)梢的枝杈間,驚奇于晝夜里小葉片的展開(kāi)閉合,忍不住摘下好多枝,編成花環(huán),戴在頭上。
我跟她都不是調(diào)皮的孩子,所以我們基本上沒(méi)有過(guò)什么壯舉,放學(xué)路上一起聊得最多的就是電視節(jié)目,那時(shí)候我們晚上追劇,第二天放學(xué)路上,一邊走一邊講劇,我落下了哪集她給我講,她落了哪段我給她講。那時(shí),我們聽(tīng)遲志強(qiáng)、邰正宵的歌,喜歡看《射雕英雄傳》《少年張三豐》《新七俠五義》……不停地哼唱《千年等一回》,因?yàn)樵诜艑W(xué)路上講劇、唱歌耽誤了回家的時(shí)間,母親常常是拿著又長(zhǎng)又細(xì)的桑條到半路來(lái)“接我”。
不顧身上紫色的條痕,每個(gè)周末我們依然聚在合歡樹(shù)下玩“跳房”或者踢毽子。“跳房”時(shí),我們先在樹(shù)下選塊平地,找一根樹(shù)棍或一塊尖利的石塊,在地上畫上“房”。“房”以方格為主,總體呈長(zhǎng)方形,共八個(gè)格子,長(zhǎng)四寬二,相當(dāng)于兩列。
我們先找一塊厚薄適中的石片,人站在兩個(gè)格子的其中一邊,先將石片丟在第一個(gè)格子內(nèi),跳的人全神貫注,單腿蹦跳,將石片輕輕踢進(jìn)第二個(gè)格子內(nèi)。這樣依次一格一格跳下去,直至將石片踢過(guò)全部格子。中途累了,我們就在合歡樹(shù)下促膝詳談,當(dāng)作休息。
進(jìn)入下一輪,我們?cè)賹⑹瑏G在第二個(gè)格子內(nèi),再?gòu)牡诙€(gè)格子踢進(jìn)第三個(gè)格子,依次跳下去,最先把格子跳完的就算取勝。跳完全部格子后,就取得了蓋“房子”的資格。蓋“房子”要求跳的人背向“房子”,將石片從頭頂向“房子”拋過(guò)去,石片落在哪一格,哪一格即為勝者的“房子”。如果石片壓線了,或者出線了,則算失敗。不知不覺(jué),太陽(yáng)偏西,父母喊回家吃晚飯的聲音,透過(guò)合歡樹(shù)葉的縫隙傳了過(guò)來(lái),我們才依依不舍地作別。
回到家,我才發(fā)現(xiàn)膠鞋右腳大拇指的地方已經(jīng)破裂,腳指頭從膠鞋里鉆了出來(lái),鞋幫也破了洞。第二天,發(fā)小一見(jiàn)我這狼狽的樣子,總是咧嘴笑開(kāi)了,彎彎的眉眼,上翹的嘴角,帶出右臉頰那個(gè)深深的酒窩。
又到周末,父母是不再允許我們“跳房”了。我們只有滿世界尋著能做毽子的材料。最受我們青睞的是火麻,火麻樹(shù)兩三米高,樹(shù)形像一把傘,樹(shù)葉似爪,上面長(zhǎng)著細(xì)細(xì)的絨毛。我們摘下它的葉子,用細(xì)繩從中間穿過(guò),扎在一起變成了“毽子”。白楊樹(shù)葉和廢棄塑料袋都是我們做毽子的材料。那時(shí)明媚的陽(yáng)光異常溫柔,肆意地灑在合歡樹(shù)的枝丫上,樹(shù)下又成了我們斗“毽子功”的戰(zhàn)場(chǎng)。
后來(lái),因發(fā)小的家庭突遭變故,接著她便輟學(xué)了。我也去了外地讀書,后來(lái)的假期,我去找過(guò)她幾次。她總是在灶臺(tái)邊忙碌著,那是一個(gè)土灶臺(tái),用土磚壘砌,糊上黃泥石灰。她愛(ài)干凈,灶臺(tái)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拾掇得清清爽爽,鍋碗瓢勺、油鹽醬醋各歸其位。接著她挑出兩個(gè)大點(diǎn)的土豆切成細(xì)細(xì)的絲,輕車熟路地放到鍋里翻炒,再做出一些潔白綿軟的饅頭,她說(shuō)現(xiàn)在迷上了織毛衣,還經(jīng)常去那棵合歡樹(shù)下邊織邊打發(fā)時(shí)間。
再后來(lái),等我假期回家去找發(fā)小,發(fā)現(xiàn)她的房子大門緊閉,鎖孔隱隱透出斑駁的銹跡,臺(tái)階上長(zhǎng)了一層綠色的青苔,庭院安靜。村里人告訴我,發(fā)小早已遠(yuǎn)嫁。那天,我回到我們的合歡樹(shù)下,閉眼能清晰地聽(tīng)到風(fēng)過(guò)合歡樹(shù)葉的沙沙聲,一陣落寞襲來(lái)。
“春色不知人獨(dú)自,庭前開(kāi)遍合歡花。”時(shí)光如河,合歡猶在,穿過(guò)合歡牽綴的舊時(shí)光,我仿佛看到發(fā)小在自己的角落,長(zhǎng)成了一株合歡樹(shù),那溫暖的笑,那雙勤勞的手,將生活過(guò)得有滋有味,美好合歡,生生不息。
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是一個(gè)瘦小卻精神矍鑠的老頭,頭上永遠(yuǎn)包著青布帕子,嘴里叼著旱煙袋,他一“吧嗒”,冒出一股輕煙,蘭花煙的味道就從很遠(yuǎn)的地方傳來(lái)。
外公喜歡抽煙、喝酒,已經(jīng)達(dá)到嗜煙嗜酒的程度。在那個(gè)過(guò)濾嘴香煙還沒(méi)普及的年代,外公的煙都是自己種的。
那年春天,他在房子的旁邊開(kāi)辟出一小塊地,四周用大大小小的石頭壘起個(gè)小園來(lái)。鋤頭刨開(kāi)土,揀出小石子,平整好肥土,就開(kāi)始育煙苗了。我望著外公手心里比天須米還小的煙種子,問(wèn)外公:“這么小的種子,能長(zhǎng)大嗎?能變成你嘴里的蘭花煙嗎?”外公不厭其煩地回答我的一通問(wèn)題,現(xiàn)在想來(lái),外公說(shuō)的大概就是只要是種子,只要種下,只要努力發(fā)芽、生長(zhǎng)、開(kāi)花,總會(huì)成熟。以至于后來(lái),我都相信,每一粒種子種下,都是一個(gè)希望,總有結(jié)果的時(shí)候。
蘭花煙被外公在小園里種得一片片的,他每天堅(jiān)持澆水,果不其然,在他的精心照料下,蘭花煙發(fā)芽、長(zhǎng)大。雖然蘭花煙的個(gè)頭不是很高,但是它橢圓細(xì)密的葉片吸引了我,忍不住伸手摸上去,墨綠色的葉子黏黏的。
陽(yáng)光和雨露是植物最好的催化劑。葉子依然圍著毛茸茸的蘭花稈四散展開(kāi),葉柄與稈的結(jié)合處,開(kāi)出狀如小鈴鐺、指甲蓋般大小的黃色小花來(lái),一朵朵向著太陽(yáng)。
外公一如既往地給它們澆水,施肥,發(fā)現(xiàn)根部的葉片黃了,便立即揪下,放在陰涼通風(fēng)處晾干,揉碎后的煙沫被他迫不及待地裝入煙袋,盤腿坐在一棵桑樹(shù)下吸起來(lái),一圈圈裊裊的煙霧和解了他弓身煙地的辛勞。等立秋過(guò)后,外公收下所有的蘭花煙葉自制成了旱煙。他每次抽完一鍋旱煙,便將煙灰隨意磕在鞋幫上,開(kāi)始給我講起故事來(lái)。
外公還喜喝酒。酒是文化,喝酒可助興,喝酒能解憂。但是,樂(lè)呵呵的外公喝酒,可能只是一種與生俱來(lái)的愛(ài)好。那時(shí)候的酒器沒(méi)有現(xiàn)在齊全,一個(gè)葫蘆就是外公的酒罐,無(wú)論上山放牛羊,還是下地干活,外公的腰間總帶著它,讓我想到游乎四海,自由快樂(lè)的濟(jì)公。那時(shí)酒的種類沒(méi)有現(xiàn)在豐富,外公的酒罐里裝著散裝白酒。放牛羊累了,找一塊大青石坐下,拿出酒罐放在嘴邊輕輕抿幾口,酒液滑過(guò)外公的喉嚨,他的一皺眉,一眨眼,都讓我覺(jué)得喝酒是讓他快樂(lè)的事情。所以外公每次酩酊,坐在二樓隔板上對(duì)著外婆和小姨發(fā)酒瘋,她們偶爾會(huì)遷怒于我,在她們眼里.外公最疼愛(ài)的孫女都不勸外公少喝,真是白疼,只有我知道,喝酒才能讓外公真正地快樂(lè)。
每逢村子里紅白喜事,有酒儀式才能完成,正如《左傳》里說(shuō)的“酒以成禮”。在這種場(chǎng)合,外公也是必醉的。有一次,村里一戶人家有喜事,小姨在家左等右等不見(jiàn)外公帶著我回來(lái),隨即找到這戶人家,只見(jiàn)外公早已喝得酩酊大醉,懷里還緊緊摟著熟睡的我。
還有一次,村里有戶人家辦喪事,外公照例醉得不省人事,一到家,他顫巍巍地從懷里掏出一個(gè)黃皮紙團(tuán)遞給我。打開(kāi)紙團(tuán),雖然熱騰騰的霧氣早已散盡,但油光锃亮的兩塊肉正散發(fā)出誘人的香氣。
根據(jù)村里傳統(tǒng),無(wú)論紅白喜事,都會(huì)弄“三盤九碗”來(lái)招待賓客,答謝四鄰,在那個(gè)生活艱難的年代也不例外。待到開(kāi)席,每桌都會(huì)上一道“硬菜”——“墩子”(紅燒大肉),那時(shí)物資匱乏,每份“墩子”都是算好的,一塊不多,一塊不少,每人兩塊,外公等其他人把自己的分子夾走,便找來(lái)一張黃皮紙,把剩下的兩塊夾起來(lái)包上,揣在懷里,給我?guī)Щ貋?lái)。
外公帶我上山放牛,教我認(rèn)識(shí)黃峰、黃芩、川芎、當(dāng)歸……那些草藥,有的長(zhǎng)著狹小的針葉,有的是闊大的葉片,有的開(kāi)著五色漂亮的花朵。外公把草藥挖回來(lái),洗凈放人瓶子泡酒。我最喜歡看他的藥酒瓶,里面總有一些花瓣舒展,漂浮在酒面上。有時(shí)候走累了,外公讓我在巖石底下休息,我便蒙上自己的耳朵,對(duì)著泡灰里的小窩大聲吼起來(lái),不一會(huì)兒,爬出一只不知名的小蟲(chóng),這樣一直可以玩到外公采藥回來(lái)。以青山綠水為鄰,以花草蟲(chóng)魚(yú)為伴,便是那時(shí)我初識(shí)自然的寫照了吧。
外公信奉“男帶魁罡,女帶文昌”的這一類男女,必有出息。他總說(shuō)我命帶“文昌”,堅(jiān)信我是必有“出息”的。7歲那年,我上小學(xué),外公用積攢下來(lái)的35塊錢,為我交了第一學(xué)期的學(xué)費(fèi)。外公寄予我的厚望,就是好好讀書,將來(lái)“有出息”。現(xiàn)在想來(lái),外公所說(shuō)的“有出息”,可能就是擺脫父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yùn)吧!
后來(lái)外公生病,被大姨接到縣城治病、休養(yǎng)。第二年春天,外公離世。就是這個(gè)慈祥的老頭兒,在疾病中艱難地走完了60年的人生。
“那些死去的人/停留在夜空/為你點(diǎn)起了燈;有人說(shuō)一次告別/天上就會(huì)有顆星又熄滅/離人揮霍著眼淚。”不知道人死后,會(huì)不會(huì)幻化成星星,但是外公的靈魂一定是有光亮的,在那個(gè)叫作“天堂”的地方,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