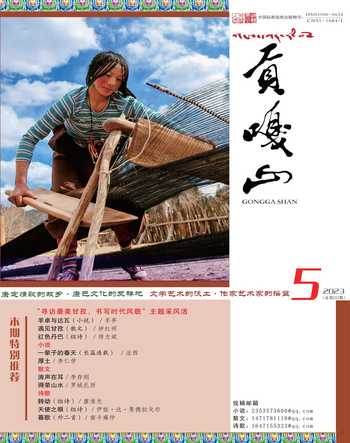三進九龍
龐驚濤
這是我第三次去九龍。
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九龍是陌生的。它因轄區九個皆有“龍”字的村寨而得名。它和香港九龍區同名,但是卻沒有香港九龍區享有一樣的知名度。一切皆因地理空間所限,足以抵消大多數人進入和探尋的熱情。
雖然明知在途艱辛、到達不易,但對我這樣一個貪圖美景的人而言,九龍自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它的寧靜、曠遠,它的靜守深閨,它的清塵洗肺,甚至它的不事逢迎,都成為我最終選擇單向奔赴的理由。
以新都橋為界,更深廣龐博的高原向右,而自成一家、遺世獨立的九龍向左。不用借助于無人機,只須在地圖上稍作留心,便會注意到九龍西向靠近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地方,有一片面積不小的無人區。因此,九龍是四川當然而極為稀見的極地、邊地小縣城。其稀見正在于,既在藏羌彝走廊的核心位置,又保持了極大的獨立性;既有其他走廊區域共有的雪山景觀,又有特屬于九龍層次豐富的雪山群;既融入了極地的生物多樣性體系,又在這樣的生物多樣性體系里,保持了最大的全面性和私有性。這樣的地理存在,對九龍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極有價值的隱喻,它會在短時間內被人忽略,但必然會在人們的幡然醒悟之后,長時間地被追捧。
在這個短時間與長時間的轉換過程中,的確還需要人,在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上,為九龍走出深閨助力添薪。
記得第一次去九龍的時候,正值俄色花開滿甲根壩河谷地帶的季節,它們散點分布在河谷、淺丘、村舍和道路之間,和藏寨外墻的色彩組合混搭,便成就了這高原上獨有的美。我少見多怪,誤將俄色花認成了梨花,當即向九龍縣文旅局局長李世陽提出,以這樣的梨花規模和立體化景觀,完全可以打造一個“梨花節”了。李世陽告訴我說,這不是梨花,是高原特有的俄色花。因樹冠高大豐茂、花開純白色,所以極像梨花。
但我還是堅持搞一個俄色花節,并和李世陽討論了怎么打造、如何傳播、怎樣品牌化堅守等具體方法和思路。這是對九龍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思路的第一次萌發。我明白,由于種種原因,我這樣過客式的思路和觀念萌發,只可能胎死腹中,而不可能很快變現。人作為這種地理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的核心因素,一定不是一個泛化的概念,它必須具體到一個操盤手,或者一個文化傳播主體。這個操盤手或者文化傳播主體,不僅需要天時地利等因素的配合,更多的時候,還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撐。更為重要的還在于,甲根壩所在的區域行政規劃上屬于康定,而不屬于九龍。雖然九龍的部分鄉鎮也有散點生長的俄色花,但規模和氣勢的確不能和甲根壩媲美。
用俄色花來承載九龍的地理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確實難了一些,也更牽強了一些。于是,位于九龍縣魁多鎮里伍村的天鄉藏茶,便這樣進入了我的視野。
這是我第二次到九龍,雖然并不一定承載九龍地理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的使命。
雅礱江高半山,海拔2500米以上,7萬多株100年以上的老茶樹……這些九龍獨有的茶語言,一旦進入我的理解和闡釋神經,便會產生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這種反應會催生和撩撥起我那個看上去早已忘得一干二凈,實際上深埋在心中的使命感:天鄉茶清純,回甘的口感和化之難去的獨特味道,既能讓我這樣的老茶客得到一次意外的驚喜,也能讓更多的愛茶人得到滿足感。
眼前山繞帶,杯中茶化詩。
一杯茶,或許更有機會成為九龍地理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的載體。
半日行走里伍村,最愛靜下來的那半個多小時。一個鐵架和塑料速成的茶舍,要是改成竹石和茅草搭建的茶寮,會更切合天鄉如天仙的意境。但即便如此,茶的底色是古典而柔軟的,它消解了一切的物象闌人、情緒闌入和堅硬闌人。煙嵐四圍,霞光溫柔,雨雪的意象在不緊不慢的聊天中明明滅滅,和四代制茶家族傳人的一番晤對,讓我堅信,如果一定要找一個物質載體來完成九龍地理空間的推揚和口碑傳說,那么就沒有比茶更適合的了。
回到成都后,我將這樣的想法和李世陽、魁多鎮領導、制茶傳人等關鍵人的多番溝通交流,說到人的因素,如果沒有操盤手和文化傳播主體,那么作為群體的、團隊的合力一定可以承載這樣的使命。我試圖將這樣具有民族特色的普米記憶上升為整個漢族與藏羌彝走廊所有民族共同的時代記憶和文化記憶。茶馬古道見證的這段歷史,理應在這個時代承載嶄新的文化使命,就像鐵觀音之于福建、普洱之于云南一樣,天鄉之于九龍,實在是天經地義的。
如今三進九龍。天鄉茶當然在繼續釋放它獨有的茶性和香氣,但九龍地理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的使命,并沒有落到它的名分上來,它占據了天時和地利等優勢,卻未必在人和上得到最有力量感的機緣。
已是仲夏時節,進入九龍的體感卻是清涼,甚至有一些微寒。車速80碼,不急不緩之間,清晰看見河谷奔流浩蕩的水和高大的樹,想象假如這樣的場景換在成都近郊,必是成人的水中麻將和孩童的水中嬉鬧聲,交織的繁盛熱烈景象。一切因為到達不易而被政變,那么在物質載體承載不起或者沒有機緣承載的情況下,觀念載體能否成為九龍地理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的救贖?
在河谷和大樹之外,后來我又看到了依傍河谷和大樹生長的草甸之間,那些蘑菇一般一夜之間“生長”出來的帳篷。它們貌似毫無章法,實則井井有條地安扎在河谷地帶,游人自帶飲食和寢具,就為了享受這樣一方遺世獨立的極地美景。
在李世陽的補充介紹里,證明了我的某種猜想是成立的:對那些追求極地野外奢侈體驗的小眾游客而言,這樣的河谷,的確不應該被世俗的麻將侵擾,被尚未建構起觀念意識和精神享受的孩童所占據,的確也是因小失大。
一個超越于物質載體之上的觀念載體就這樣萌發:假如花與茶作為物質載體,皆不能承載九龍地理空間推揚和口碑傳說的使命的話,那么作為觀念載體的“極地野奢”,便是九龍突圍最大的可能。其“人和”因素,不是操盤手和團體的主人視角形成的,而是從帳篷客、自駕客的客體視角形成的。大多數時候,客體視角比主體視角,更能經得起時間和空間的檢驗。
在這個觀念載體里,無論伍須海,還是獵塔湖,或者華丘村、猛董,都是“秘境九龍,極地野奢”觀念先行的整體。圍繞這個整體,九龍要主動吸引,爭取追求野奢、自由的定制客群,與追求時尚、輕奢、浪漫、安靜的中產等新生代客群。當然,帳篷不是隨便搭的,規劃和調控必須發揮作用、形成力量。
在我的想象里,當五顏六色的“小蘑菇”開滿九龍的雪峰與河谷之間時,“不以山海為遠”的九龍,就能從龐博神秘的高原、極地突圍而出。假如約瑟夫·洛克重回九龍,我想,他也會為九龍的“極地野奢”由衷認可。
1929年,美國探險家、旅行家約瑟夫·洛克,以美國《國家地理》特約撰稿人的身份進入九龍,立即被其遺世獨立的美景所吸引。作為第一個走進這片秘境之地的外國人,洛克的九龍之行堪稱奢靡,除了被當地宗教首領接待安排住在最好的住房里之外,洛克隨行的豪華馬隊,也為他帶來了隨時可以安營扎寨的帳篷和折疊床,還有便于他就餐和寫作的椅子、桌子,桌子上面當然還有優雅迷人的桌布和昂貴的瓷具。為了便于他隨時記錄一路景觀和植物標本,笨重而稀罕的照相機,也是馬車隊帶來的奢侈品。此外,供他閑暇時享受用的電池供電留聲機,更是九龍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天外來物”。行走極地,享受野奢,洛克既是20世紀九龍海外地理空間推揚的第一人,也毫不爭議地成為今天九龍“極地野奢”口碑傳播的代言人。
在洛克走進九龍即將抵近100周年這個時間關口,作為觀念載體的“秘境九龍,極地野奢”的自然形成,莫不是洛克早就形成,而未來得及對外宣揚的想法?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花與茶之后,“極地野奢”能承載得起九龍并幫助九龍完成這次突圍嗎?
從九龍離開往成都趕的時候,我內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種不舍和眷懷。或許,從這一刻起,我和九龍便從此建立起了一種雙向奔赴的關系。誰說大地無情呢?只要那個“我”有情了,大地的“情”才會綿密厚實,淵海而來。
此刻,我竟然如此期待第四次進入九龍,不是以某種使命而去,而是單純地因為想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