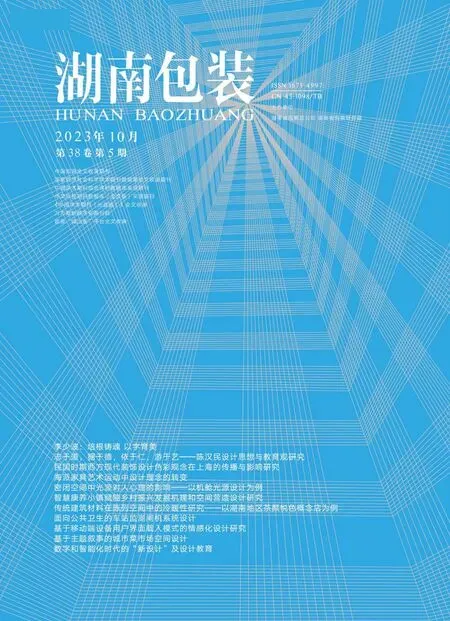對傳統民居建筑材料色彩特征的研究
——以云南牙龍村壯族民居為例
沈佩佩 龔怡婷 馬琪
(云南藝術學院設計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城鎮化建設加快推進,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傳統鄉村建設正在廣泛開展。傳統民居建筑作為歷史村落文化見證重要部分,建筑色彩也可以直觀體現出當地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具有極高的精神價值和使用價值。如今越來越多新建的傳統民居在建筑形式、建筑色彩與建筑材料上都存在較大的同質性,并且逐漸城市化,村子里的新舊建筑相互交織,不同色彩的建筑相互滲透,傳統民居建筑的色彩構建方式與其獨特的色彩特征正在悄然流逝[1]。
1 牙龍村民居建筑概況
牙龍村位于云南省文山壯族自治州東北部、廣南縣東南部的八寶鎮,北接板蚌鄉,西鄰本縣南屏鎮,東靠富寧縣,是云南通往兩廣及沿海地區的交通要道。少數民族人口占這里總人口的79.5%,具有豐富的多民族文化內涵,其中壯族占總人口的54%,是中國壯族文化發育較早的地區之一。
牙龍村距今100 多年前,早期的民居建筑多為泥沙磚和石頭堆砌,建筑材料采用八寶河里泥沙制作而成磚,通常依山筑建。1980 年之后,由于農耕、植作緣故,逐漸搬離到山腳下,民居建筑演變為以磚墻為主,兼顧少量石頭堆砌,建筑外立面材料改為磚墻、碎石等混合形式。民居建筑新建發展至今,逐漸受城市化建筑風格影響,在村中一處新建房屋建筑中發現,其建筑外立面開始采用涂料涂刷表面,與村中其余傳統民居建筑色彩構建形成鮮明對比。
由于村中勞動人口單向流入城市務工,造成村中多處建筑閑置和廢棄,傳統民居建筑長期無人居住和缺乏保護造成其建筑結構破壞、外墻顏色退化的問題。與此同時,人們以城市現代簡約的建筑形式作為追求,新建建筑與當地傳統民居建筑開始顯現出較大區別,村中傳統民居色彩特征及構建方式逐漸面臨危機。
2 牙龍村民居建筑色彩影響因素
2.1 自然環境因素
牙龍村坐落于八寶鎮內,其中村落沿河分布,橫穿整個八寶鎮,河流是村落選址的重要因素之一。牙龍村的土壤屬于黃壤,大多來源于鎮內八寶河河底堆積的泥沙,而最原始的民居建筑材料是河里的泥沙土,也是直接影響村落民居建筑色彩的重要因素。其氣候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冬比春城昆明暖,夏比春城昆明涼,常年溫差相對較小,溫度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人的心理需求與視覺感受,從而使人在不同的溫度條件下尋找到與心理平衡的建筑和色彩質感[2]。
2.2 人文環境因素
牙龍村依靠河流生存,孕育著獨特的農耕文化,早期農耕呈現自給自足狀態,為了滿足生存需求,傳統民居建筑的原材料大多來源于河流內沉淀的泥沙,既利于日常農耕習作,又利于地域文化的傳承。
村內人口以壯族為主,還有少量漢族、苗族、彝族、瑤族等,在其影響之下,不同的民俗文化產生碰撞,以壯族民俗為主的壯文化也得以共存,成為影響牙龍村傳統民居建筑的獨特因素,對傳統民居建筑的色彩構建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利于形成其獨特的色彩特征。
2.3 旅游資源因素
牙龍村所在的八寶鎮在2005 年榮獲“云南省生態鄉鎮”稱號,牙龍村背靠八寶鎮,享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優勢,地形復雜多樣,境內自然、人文景觀,水資源較豐富,著名的三臘瀑布景區更是處在其中。同時,八寶鎮用清澈蕩漾的八寶河承載著一代又一代的稻作文化和農耕文化,養育著肥沃的兩岸良田,良好的自然環境為農作物的生長保駕護航,遠近聞名的“八寶貢米”種植基地也設在此地,其稻田景觀有著極高的旅游開發價值。豐富的旅游資源對傳統民居建筑色彩構建十分有利,形成獨特的建筑色彩特征,更能夠吸引外來游客的觀光體驗,形成牙龍村的特色旅游項目。
3 牙龍村民居建筑色彩提取與分析
牙龍村調研對象分為歷史建筑和新建建筑,對建筑的建筑外觀、室內布局、家具材質、街道環境、植物水體等進行實地測色[3]。
牙龍村民居建筑色彩提取會用到3 種色彩提取方式:第一種,對于面積較大、表面光滑、易于對照觀察的建筑材料可用CBCC《中國建筑色卡國家標準》1 026 色卡來進行色彩比對,獲取最接近的色彩數據信息;第二種,對于景觀色彩和大片區域的建筑色彩可以使用照相機進行實地拍照,將照片放進PS 軟件內進行色彩識別與提取,從而獲取色彩數據信息,并對建筑整體形象與村落整體環境進行記錄;第三種,對于復雜造型某一點的建筑色彩,可以用便攜式測色儀作為采集色彩數據的工具,用儀器對準相對平整的區域按下測量鍵,直接進行色彩數據提取[4]。
3.1 建筑外觀
建筑外觀包括屋頂、墻面、地面。牙龍村傳統民居的色彩受當時經濟條件與技術條件的制約,主要由建筑原材料的固有色決定。新建建筑則是1980 年以后建造的,科技與建造技術的發展使建筑材料有了更多的選擇。
傳統民居建筑屋頂由當地制作的瓦片輔以木制結構的房梁為主,屋頂形制為懸山頂,色彩為瓦片的青灰色和木材的暖黃色。新建建筑的屋頂由磚瓦水泥砌筑,簡陋屋棚頂面由鋼架塑料覆蓋,屋頂形制似平面無較大起伏,色彩以水泥的青灰色和塑料的藍色為主。
墻面是建筑的維護結構,也是建筑外觀占比最大的部分,能直觀地展現色彩特征與建造技藝,不同地區傳統民居墻體的色彩是給人的第一視覺感受[5]。建筑材料采用八寶河內沉淀泥沙,泥沙土墻的覆蓋率占比80%,以暖黃色為主要色彩體系,黃色(4.4Y/8/4)、黃紅(10YR/8/4.4)為主要的色彩。磚墻、石墻的覆蓋率占比20%,灰色(N6.25、8.8B/6.5/1.8)為主,多在與地面接觸的位置,對泥沙土墻起加固作用。石頭之間用三合土進行粘合,呈現出棕黃色(0.6Y/7/4),泥沙墻與石頭墻基形成對比,從色彩上給人以穩重的直觀效果。
新建建筑采用現代建筑材料,以當地燒制的紅磚、青磚以及墻面貼磚為主要墻體材料,用水泥進行粘合加固,墻體磚縫輔以白石灰進行防潮處理,以紅棕色(0.6YR/5/4.8)、棕黃色(0.6Y/7/4)、青灰色(7.5B/4.5/1.6)為主。主要表現為紅色調,輔之以青灰色凋、中低明度、低色彩飽和度的建筑色彩特征。
傳統民居建筑地面材料以當地泥沙土為主,與地面水平鋪制,色彩為泥沙土的黃褐色。新建建筑的地面材料由沙石水泥平鋪,色彩以水泥的青灰色為主。
3.2 室內家具
牙龍村傳統民居以干欄式木質結構為主,多為二層建筑,一層層高較為低矮,用作家畜飼養、日常做飯;二層比一層稍高,用作日常居住、待客。新建建筑以鋼筋混凝土結構為主,多為二至四層的建筑,層高一致,一層用作日常做飯、待客,二層及以上用作日常居住。新舊建筑室內家具種類相似,家具包括門、窗戶、欄桿、樓梯、桌椅、日常用具等。
傳統民居建筑家具材料就地取材,用附近的竹子、木材、石材等進行制作,色彩多以材料固有色或后期加工色為主。制作室內大型構架使用石材與木質材料較多,如使用石材的階梯、燒火灶臺(使用白色石灰抹面),使用木材的房梁、柱子、二層平臺、門、窗戶等,色彩以石材的灰色(2.5PB/7/1)、石灰變色后的灰白色(2.5B/9/1)和木材的棕色(5.6YR/6.5/4)為主。制作室內小型家具使用竹編材料較多,如室內隔斷、桌椅、床、簸箕、籃筐等,當地居民進行竹編制作前,會先把竹子的青色外皮去掉,使其色彩以竹子內部的黃色(4.4Y/8/4)為主,與木制家具的色彩一致。隨著時間的流逝,家具的頻繁使用則會加深它們的色彩,使其呈現的色彩逐漸偏向褐色(2.5YR/4/1.8)。
新建建筑的家具以現代流行的鋼材、玻璃、瓷磚等新型材料為主,具有易采買、安裝便捷、經久耐用的優點,色彩復雜多樣,體現不同居民的色彩喜好與偏向,與傳統民居的色彩特征差異較大。室內家具種類齊全,有鋼架欄桿、玻璃窗戶、瓷磚或水泥地面、不同的電器、軟裝家具等,色彩種類多并以個人偏好為主。
3.3 村落環境
新建建筑地勢平緩位于村落入口處,建筑密度較大,傳統民居建筑地勢稍高位于新建建筑的上方,建筑密度較小,新舊建筑區域劃分明顯。
傳統民居建筑背靠群山,環境質樸清幽,黃色(2.5YR/4/1.8)的泥土路、青灰色(1.3PB/7.5/2)的路邊石頭矮墻、綠色(8.1GY/4.5/3.6)的植物、藍綠色(6.3PB/8/3.6、7.5GY/8/2.4)的自然河溝與瀑布湖泊交相輝映。村落中保存完好的傳統民居建筑較少,大多因遷移、年輕人外出務工等因素逐漸損毀。因此,建筑樣式與傳統民居建筑形成鮮明對比,在村落中百年沉淀的色彩體系逐漸減少,也沒有能夠得到傳承與保護。
由于城市化的飛速發展,傳播速度明顯提升,牙龍村的新建建筑環境偏向城市化,街巷空間自然元素減少,被灰色(N6.25)的水泥鋪路、紅色(7.5R/5.5/3.2)的磚墻與不同色彩的貼磚外墻所代替。街巷綠色(8.1GY/4.5/3.6)的綠植量少、種類單一,多以爬墻綠植或是家院里的零散果樹、小型盆栽為主,村口處有大片農田和連綿起伏的山脈。建筑形式與室內家具色彩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的特征,導致村莊中傳統色彩特征面臨衰退甚至逐漸消失的現狀[6]。
通過調研對牙龍村民居建筑色彩數據提取后,用《中國建筑色卡國家標準》電子版數據庫軟件進行符合檢驗,將不同部分的色彩因子根據檢測標準進行數據對比分析,并將結果以表格的形式進行色彩數據對比記錄,使其色彩特征更加清晰(表1)。對得出的現有色彩數據和牙龍村民居建筑色彩形成因素、地域特征進行綜合分析,為未來該地區的傳統民居建筑材料色彩的保護與傳承做出相應的色彩數據參考。

表1 牙龍村傳統建筑與新建建筑的色彩數據對比
4 牙龍村傳統民居色彩應用策略
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隨著對建筑需求的不斷改變,建筑材料更迭速度快,各種類型的建筑材料相繼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下,建筑涂料也日益豐富,許多傳統民居建筑形式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現代化生活,傳統記憶與現代需求的結合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新命題。在眾多風格的民居建筑中,傳統形式與現代化需求陷入無盡的矛盾[7]。因此,從建筑色彩體系的方向尋求傳承,人們一提到徽派建筑,粉墻黛瓦的印象就能立刻出現在腦海里,徽派民居建筑的色彩保護得較為完整,研究其建筑色彩運用策略,并將研究結果(表2)以借鑒的形式注入牙龍村的民居建筑材料色彩體系構建中。

表2 牙龍村與徽州民居建筑對比
4.1 提高傳統民居色彩認知
牙龍村的傳統民居色彩具體包括建筑材料的原真色彩、村落周圍的環境色彩以及它的地域性色彩。地域性村落建筑色彩風貌是受地理環境、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影響而形成的,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8]。徽派建筑的新舊建筑色彩能夠做到如此統一,是當地居民對徽文化強烈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現今,牙龍村外出務工人員多為青壯年,在外務工的閱歷使他們與留守村民的文化認知、審美各不相同,造就出傳統建筑與現代建筑交織混合的場面。發展旅游業,發揮當地的文化特色與自然風光優勢,吸引外出務工村民返鄉創業就業,讓牙龍村村民打造自己的家園與事業。通過舉辦各類特色民俗活動進行文化宣傳,加強村民的地域文化認知,讓當地新一代的村民認識到本民族文化的特色與內涵,主動承擔起傳承歷史文化的重任并以此為榮。通過對傳統建筑色彩、建筑材料與建筑工藝的講解,使村民更深層地了解當地傳統建筑歷史,提高村民對傳統民居的色彩與審美認知,使其在新建筑的色彩選擇上主動趨向于傳統民居色彩。
4.2 明確傳統民居色彩復雜性
牙龍村新建筑的加入對于傳統民居建筑色彩體系構建造成一定的沖擊,新舊民居色彩不統一,建筑材料也較為混雜,對于傳統民居色彩體系的構建需要考慮色彩的復雜性原則[9]。徽派建筑的民居色彩統一性強,傳統民居建筑與現代簡約的建筑形式并存,做到新舊建筑合理劃分地塊,避免新舊建筑形式交叉造成建筑風格混亂的現象。
因此,牙龍村在新建建筑中必須充分考慮其建筑材料色彩的復雜性,通過對原材料的收集高度還原傳統民居的建筑色彩體系,對新建建筑的色彩彈性控制和剛性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明確新舊建筑的發展區域與方向,分區域進行建筑色彩體系與建筑形式的管理,對建筑的選址、新建、翻修進行登記備案,在施工過程中進行定期視察與適當監督,保證建筑色彩與形式的一致性。
4.3 制定傳統民居建材直取策略
新建的徽派建筑選址大多是在傳統民居建筑氛圍濃厚的地方,有大量的建筑材料與完備的施工工藝,廢棄的房屋院落也可以進行再利用或者原址再建,極大程度地保留建筑色彩體系。牙龍村傳統民居的建筑材料保存量較多,有人居住的建筑保存較為完整,建材損壞程度較輕;無人居住的建筑年久失修,建材損壞與腐蝕程度較大。
對于牙龍村內保存較為完好的建筑原材料、外墻面裙堆砌的石頭、墻身的泥沙石土墻等材料色彩體系,在新建建筑的過程中可以采取直接選取的方式進行運用。在建筑材料的選用上,需要考慮到材料的腐蝕性與變色性,加入現代保護措施[10]。對于村落內損壞較為嚴重的建筑原材料可以選擇分段式利用,新建建筑里面積較小的部分或者邊角縫處可以進行適當填補[11]。上述措施使牙龍村傳統民居既保留了傳統的色彩體系,又使傳統建筑材料得以保護與再利用,整個村落在整體風貌上得以最大程度的保護和傳承。
4.4 參考傳統民居色彩相近色
牙龍村的傳統民居建筑歷經風霜沉淀,色彩呈現上與原材料色彩有著一定的誤差,有的原材料在復原難度上也較大。新建徽派傳統民居中色彩以黑、白、灰為主色調,部分建筑放棄了磚瓦材料,以鋼筋混凝土為主,窗戶大多改用相同色調、經久耐用的鋁合金或鋼材。
牙龍村未來的民居建筑如果想傳承村落本色并與其保持一致,在建筑色彩的選用上,可以參考原真色并采用與其相近色材料的方式作為參考運用。保留傳統民居建筑的主色調,適當加入相近色的現代建筑材料,對建筑的主體色彩進行協調設計。在新建筑的建設過程中還需要考慮到現代人的審美,在確保主色調不變的情況下,建筑室內配色上可以適當展現色彩的層次感,加強飽和度的對比,使傳統建筑的質樸與新裝飾風格巧妙結合,構建牙龍村獨特的地域民居色彩體系。
5 結論
傳統村落建筑色彩的研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且影響傳統民居建筑色彩構建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區別于其他地區而言,牙龍村傳統民居建筑色彩的形成得益于其建筑外觀、室內陳設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與人文底蘊,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文山壯族自治州的傳統民居風貌。從自然地理環境與壯族文化氛圍兩方面深入挖掘影響牙龍村壯族民居建筑色彩體系的形成因素,并對傳統民居建筑進行實地調研與色彩數據的提取分析,得出該村落傳統民居色彩呈現出強烈的地域特色;同時與徽派傳統民居建筑色彩特征進行對比研究,總結牙龍村傳統民居色彩體系的構建要素,應綜合考慮其地域性與色彩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