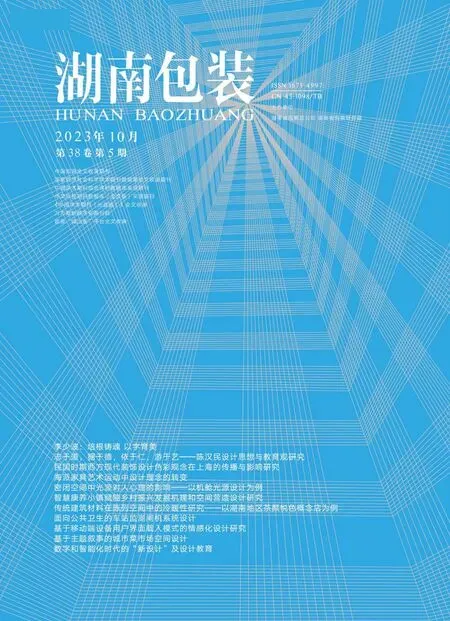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適應性再利用設計探究
蔣寧馨 章天 王靜雪 黃志紅
(北京城市學院,北京 101309)
由于21 世紀以來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第三產業的迅速崛起,中國城市化發展進入到了新征程。但與此同時,城市中許多既有建筑的功能及面貌已不再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廢棄的既有建筑不僅影響城市形象、破壞城市環境,還造成區域活力的喪失。城市記憶的消逝已經飽受詬病,大規模的拆建亦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城市高速代謝的背景下,推動老舊既有建筑的持續更新,具有增強地區活力、振興城市經濟和協同物質遺產與精神文明共同發展的重要意義。
1 既有建筑的概念
既有建筑泛指迄今存在著的一切建筑[1]。在時間維度上,既有建筑可分為建造時間較短的新建筑與建造時間較長的舊建筑;在人文維度上,既有建筑可分為一般性建筑與具有一定歷史價值的建筑。在設計更新及保護修復的討論范疇中,既有建筑一般指現存且仍具備一定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或生態價值的舊建筑,其不僅包括各類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的保護性建筑,也包括一些價值有限、但在適宜設計策略下可避免拆毀的、仍能發揮其剩余價值為社會服務的建筑[2]。
2 既有建筑適應性再利用的必要性
當城市快速向新時代轉進時,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諸多已喪失功能價值的民用及工業建筑占領了大片城市土地面積。面對此種情況,許多城市直接對大量舊既有建筑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即直接全部拆除。然而,舊既有建筑是一座城市歷史發展的象征,是一座城市里寶貴的文化資源,承載著人們的鄉愁記憶。在大量舊既有建筑被拆除的過程中,城市中的人文情懷和文明脈絡也隨之消失。
2020 年11 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王蒙徽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的署名文章中指出,過去“大量建設、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等城市開發建設方式已難以為繼,需逐步轉向以提升城市品質為主的存量提質改造[3];2021 年8 月,住建部發布《關于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中防止大拆大建問題的通知》,提倡分類審慎處置既有建筑,推行小規模、漸進式有機更新和微改造。對歷史價值不強的非保護性既有建筑來說,它們承載了一定的城市文脈,又具備一定的改造自由度。對這類既有建筑的改造,既是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實踐,又是對舊文化與新藝術的結合。在對既有建筑適應性改造的過程當中,人們通過自己的勞動產品繼承文化,保護自己,并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實現緊密的關系聯結,最后在繼承與創新的矛盾中找到平衡,為傳統文化的轉型提供了多樣性[4]。
3 既有建筑適應性再利用的趨勢
針對舊既有建筑進行適應性再利用的思考與實踐起源于西方。1979 年,《巴拉憲章》提出“改造性再利用”概念并指出為建筑遺產找到恰當的用途[5]。1985 年左右,發達國家(如美國)既有建筑更新已經占據建筑總工程半數[1]。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既有建筑的改造再利用在歐美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改造的建筑類型也逐漸豐富[6]。中國在20 世紀80 年代逐步開啟了對既有建筑改造的探索,21 世紀以來,伴隨著城市建設的實際需求,既有建筑改造在中國進入了新時期,改造模式呈現多元化與時尚化,地方特色也成為改造項目的重點表達方向。如今,既有建筑適應性再利用的范圍正不斷擴大,大量非保護性的既有建筑進入到了再利用的范圍,更新的重點逐步轉向綠色環保、經濟循環以及文化價值等層面。對既有建筑的適應性再利用正成為中國城市發展中的核心重點。
4 既有建筑適應性再利用的策略
既有建筑的適應性再利用設計不是在白紙上天馬行空,而是需要與建筑本身、場地條件、區域文脈等要素建立關系,以此來解決新舊矛盾,升華內在價值。在更新過程中,核心需求并非作出多少改變,而是要強調新與舊的適配性,以此為新舊體量建立對話,在延續歷史文脈的背景下使既有建筑為當代所用。通過對國內外的相關更新案例進行分析,總結出以下幾點策略。
4.1 修舊如舊
目前既有建筑中具備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大多采用修復模式,以傳承文化遺產,還原歷史本色。梁思成先生講“修舊如舊”的修復原則,即完全沿用原建筑使用的材料、顏色、結構;完全按照原建筑的制作手法,可以用手工的絕不用機器代替[7]。應用修舊如舊法則的既有建筑在設計上減少新加入的體量,在材料上盡量選擇原材料,不讓建筑感覺脫胎換骨。例如重新修繕的上海音樂廳,在文保區域堅持最小干預,用特殊工藝無損清潔與修復外立面,用手工藝復原羅馬式裝飾柱、大廳穹頂等,讓這座始建于1930 年的建筑再現輝煌(圖1)。

圖1 上海音樂廳文保區。
4.2 新舊對比
非歷史保護性既有建筑在更新時多采用改造、擴建等模式,對建筑中擴張和加建的部分一般不采用復原和仿制等技術,而是要與之前的舊建筑形成新舊對比。運用新材料、新技術,補新以新,以新舊之間的沖突碰撞創造建筑的歷史層次感,讓人們在建筑的“舊”之中感受到時代的“新”。例如北京“1959 時間里”文創產業園區,在更新原有廠房建筑時,建筑的主入口處使用U 型玻璃與原紅磚材質進行對比(圖2),突出了新舊層次。

圖2 北京“1959 時間里”文創產業園區。
4.3 新舊包容
新舊體塊之間的互相包容包括兩個方向:其一是將舊體量置入新外殼,為既有建筑賦予全新的外觀效果,并與周圍現代化的建筑相呼應。新加建的外層體量通過加蓋、外掛和包裹等方式,減少對原建筑的破壞,并覆蓋原建筑可能存在的物理缺陷。此外,加建的新部分有時也為建筑提供一定的輔助功能,如增加檐廊、控制光照和調節溫度等。2005 年改造完成的巴塞羅那圣卡特琳娜市場就通過在原建筑上增加一層充滿藝術氣息的彩色大波浪屋頂來激發新的觸媒效應;杭州XPACE 灣區數字公園在舊廠房建筑上加入全新的參數化設計立面,用預制鋁垂直百葉窗排列出了優雅曼妙的視覺效果(圖3)。

圖3 杭州XPACE 灣區數字公園改造前后。
其二是將新體量置入舊外殼,在保留原貌的舊既有建筑內植入新質空間。在資金有限的條件下,實用價值成為了舊建筑首要考慮的因素。通過隱新于舊的方式,強調建筑內部的空間更新,為建筑注入新的功能與活力。或在原有的大空間內置入新的小空間,為舊建筑保留原貌的同時增添空間的趣味。
4.4 新舊調和
由于時代背景,舊既有建筑大多單一且封閉,缺少當代空間所需的靈活性。基于此,部分既有建筑的更新需求源于對原功能的拓展與擴充。在新舊體塊銜接時,為表達對舊建筑的敬意,新體塊在造型、材質、色彩和體量上采取與舊體塊接近的設計,以尋求新舊之間的平衡。具有90 多年歷史的日本京都市京瓷美術館在更新時由于現代化展覽需求,在舊建筑后方加建了一個新館,新館的玻璃纖維增強水泥立面,在遠看時與主館的磚瓦立面色調統一(圖4),靠近后才顯示出不同的肌理,在視覺上避免了喧賓奪主的效果。

圖4 京都市京瓷美術館。
5 龍泉國鏡藥廠適應性再利用設計實踐
5.1 項目背景
龍泉市是浙江省麗水市代管縣級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浙閩贛邊境。項目基址位于浙江省龍泉市劍池街道原國境藥業地塊,占地約1 200 m2,擬將原工廠片區打造成為集商業、展覽、餐飲及配套公共服務空間為一體的城市文化客廳。
龍泉是歷史悠久、人文璀璨的劍瓷名城,是中國青瓷之都和寶劍之邦、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文化先進市。龍泉因劍得名,龍泉寶劍始創于春秋戰國時期,以“堅韌鋒利、剛柔并寓、寒光逼人、紋飾巧致”四大特色而被譽為“天下第一劍”。龍泉憑瓷生輝,龍泉青瓷始于三國兩晉,盛于宋元,龍泉“哥窯”與著名的官窯、汝窯、定窯、鈞窯并稱宋代五大名窯,入選“人類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龍泉青瓷、龍泉寶劍、青田石雕合稱“麗水三寶”,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位于基址北側的龍泉溪就曾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必不可少的流段,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與歷史意義(圖5)。

圖5 場地分析圖。
隨著藥廠的遷址,場地內的既有建筑處于閑置狀態,部分建筑存在安全隱患,樓體面貌也與周圍環境大相徑庭。結合對上位規劃、場地特征及城市需求的綜合考量,設計擬將區域打造成集商業、展覽、餐飲及配套公共服務空間為一體的城市文化客廳,以喚醒場地內的建筑(圖6)。

圖6 場地原貌照片及軸測圖。
基址位于甌江南側,而甌江支流漫延流至各方,曾為文化與經濟的傳遞立下了不朽的功勞;如今甌江依舊流淌,雖然不再是經濟運輸的主力,卻仍是文化特色傳承與延續的代表。龍泉青瓷中以冰裂紋最具代表性,恰巧龍泉也能夠煅煉出同樣是冰裂紋樣的寶劍,層疊多支的冰裂紋樣像是溪水分流般展現了豐富的美感。因此,最大地保留了基址的建筑特色,提取了甌江漫延的理念,與劍瓷共有的冰裂紋樣進行結合,意在讓既有建筑、青瓷寶劍的歷史文脈傳承至今,并不斷發揚與進步,希望基址建筑特色及歷史文脈如溪水支流與冰裂紋一般豐富圓滿,不斷延續。
5.2 既有建筑的保護與文脈傳承
既有建筑既是城市記憶的載體,也是城市文化的傳播窗口。作為場地內標志性的建筑,水塔的存在猶如場地記憶的關鍵幀(29-6#建筑),是設計項目的保留重點。水塔大多建造在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用于儲水和配水的高聳結構,曾為居民蓄水與送水發揮重要作用。設計為水塔冠以“城市放大鏡”的主題,通過水塔凝望與見證整座城市的發展,感受龍泉整座城市的文化特色與精神內涵。方案最大限度地保留水塔的完整性,通過在水塔頂部增加360°環繞玻璃墻,將其打造為頗具特色的城市觀景臺。人們通過內部的旋轉樓梯登上水塔頂部,利用固定望遠鏡俯瞰整座城市(圖7)。在夜間,利用塔身與地面的關系設計燈光秀等演出,通過青瓷、寶劍制作方法等視頻和燈光秀展示,將幾個建筑物之間聯系起來,交相輝映。周圍設計具有形式感的座椅,以供游客歇息和觀演。設計旨在紀念已經喪失功能性的水塔曾經為這片區域的發展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完整的水塔屹立不倒,也是該區域歷史文脈的延續。

圖7 水塔日景、夜景效果圖。
此外,浙江民居很講究與自然的共處和與環境的融合,因此在對其余民居進行更新時,光與景被借用到空間中。例如在木屋書店(29-5#建筑)的設計中,屋頂借鑒傳統民居“四水歸堂”的形式新增了采光天窗的設計,傳統園林借景、框景和添景等造景手法也被植入其中,以體現傳統文化的延續。
5.3 既有建筑面貌的再利用
建筑的立面形象決定著人們對其的初始印象,它也是觀眾體驗建筑最直觀的方式[6]。建筑的風貌受所在地自然環境和人文歷史等因素的影響,保留原本建筑的面貌與質感,也是保留建筑的本質特征與文化情感。因此,既有建筑面貌的更新是一個因地制宜的設計過程。
此次設計范圍內面積最大的建筑是一棟木結構民居(29-5#建筑),依據木材肌理所具有的柔和與親切之感[8],計劃將其改造為清新幽雅、氣韻質樸的木屋書店。設計中保留了浙江民居粉墻黛瓦的外觀特色,使其與周邊環境相融。作為中式傳統建筑的一種,木結構建筑強調空間的和諧、有序以及木結構之間功能與美觀的平衡[9],因此室內的木質梁柱予以最大限度地留存(圖8),僅依托燈帶體現結構層次,傳達韻律之美。

圖8 木屋書店效果圖。
在場地北側有一處單層民居(29-1 及29-2#建筑),兩處建筑因體量較小被合并。依據其空間形態及沿街性質,改造方向定為咖啡店。為了保留建筑的原始面貌并體現咖啡店的時尚氣息,設計中以大面積的玻璃窗強化商業空間的通透感,并在舊建筑體內植入一個新的玻璃盒子作為咖啡店的入口及點單區域(圖9),以此低調地處理新舊之間的碰撞。在空間中,顧客可以感受玻璃、鋼鐵等現代材料與舊有墻體外殼之間的歷史關系;在空間外,建筑得以保留其原始記憶,不與周邊環境產生沖突。

圖9 咖啡店效果圖及軸測圖。
5.4 有機更新中的功能性適應
空間是人們生活、活動的一種客觀存在,它由特定的長寬高所限定,但空間內部是具有可塑性的[4]。既有建筑的更新中往往伴隨功能的變換,在對既有建筑的改造中,需注重對原空間的重構與整合,加入必要的現代化設施,并優化交通流線,提升空間利用率,使舊建筑符合新需求。同時,通過對較大面積空間的重組與劃分,能夠為空間提供更多元化的可能。例如對木屋書店(29-5#建筑)的設計中,空間在橫向上被劃分出陳列區、飲品區、觀景閱讀區、閱讀區和下沉冥想區,縱向上劃分出一個半層平臺空間,是安靜的閱讀區。不同的休閑功能被整合于同一個雅致樸素風格的建筑內,不同區域之間互相滲透而不產生打擾(圖10)。

圖10 龍泉木屋書店效果圖。
除前述的改造建筑外,場地內的多層民居(29-4#建筑)被融合于零售及體驗空間,并成為龍泉寶劍與龍泉青瓷的展示窗口(圖11);紅磚民居(29-3#建筑)則成為兒童活動中心,滿足全齡段市民的休閑需求(圖12)。改造后的既有建筑各司其職,它們的功能綜合到一起時,共同組成了城市居民的會客廳和城市文化的傳播口(圖13—14)。

圖11 龍泉文化體驗店效果圖。

圖12 兒童活動中心效果圖。

圖13 項目中既有建筑功能分析圖。

圖14 項目中既有建筑區域功能分布圖。
6 結語
簡·雅各布斯[10]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提到,“老舊建筑的合理存在是對新城市綜合面貌的保護,是城市發展狀態下的必然選擇”。既有建筑見證了社會的歷史發展,并以其獨特的語言記敘著城市的情感與回憶。對既有建筑價值的重識與發掘呼應了當代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推進著城市的良性進化。在城市的永續發展與更新之中,還需加快形成整體性的保護與更新框架,深入推進計算機等技術在既有建筑保護和更新中的運用[11],以更先進的手段活化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相信那些經過精心設計而重獲新生的既有建筑也將像一座座記錄人類文明的紀念碑那樣在未來的城市中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