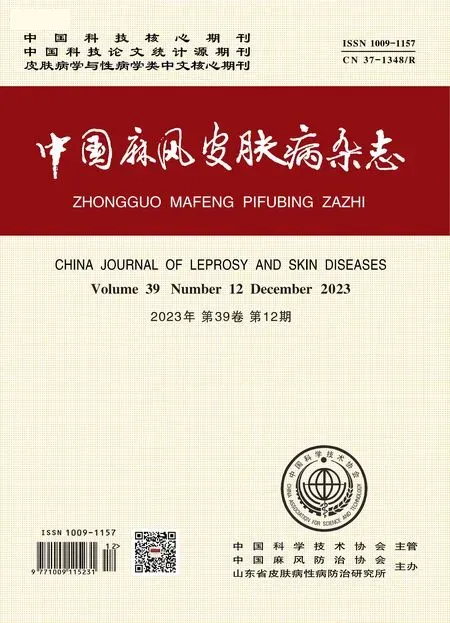利妥昔單抗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伴血液危象一例
龍博泉 楊 嵐 馬萍萍 賴惠君 竇舒慧 蔡川川 郭紅衛 李 定
1廣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皮膚科,廣東湛江,524003;2廣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皮膚科,廣東湛江,524000;3廣東醫科大學,廣東湛江,524003
臨床資料患者,女,41歲。因顏面部紅斑、四肢關節痛2個月來診,2021年1月4日收住入院。2個月前,面部、枕顳部、頜頸部及上胸部無明顯誘因陸續出現暗紅色水腫性紅斑,自覺輕微癢痛,無破潰滲出。同時,肩關節與雙手指關節出現疼痛、腫脹,活動受限,伴不規則低熱(38.5℃左右),于當地醫院診治未見好轉,來我院皮膚科就診,門診查血常規、尿常規、抗核抗體系列發現異常,考慮診斷為“系統性紅斑狼瘡”,收住入院。患者平素睡眠欠佳。既往體健,否認藥物過敏史,否認家族遺傳病史。
體格檢查:體溫38.8℃,脈搏86次/分,呼吸20次/分,血壓95/60 mmHg。一般狀況良好,心肺腹部未見異常。皮膚科檢查:鼻梁、面頰、顳部、頜頸部、枕部、上胸部可見散在直徑約1~3 cm的暗紅色水腫性斑疹、斑片,邊界清晰,伴少許脫屑,無壞死、滲出(圖1)。手指甲周紅斑,多個手指關節輕度腫脹,雙肩關節輕度壓痛,局部無明顯潮紅。

圖1 鼻梁、面頰等部位見暗紅色水腫性斑疹、斑片 圖2 2a、2b:表皮輕度角化過度,基底細胞液化變性,見數處色素失禁,真皮全層血管和附屬器周圍見多量漿細胞和淋巴組織細胞浸潤(2a:HE,×40;2b:HE,×200)
實驗室檢查:2021年1月2日門診查尿蛋白(±);血常規WBC 2.81×109/L,RBC 3.67×1012/L,HGB 112.00 g/L,PLT 109.00×109/L;肝腎功能:ALT 42.70 U/L,AST 59.50 U/L,Urea 2.30 mmol/L,Scr 54.00 μmol/L,TP 86.50 g/L,ALB 45.50 g/L;抗ANA系列:抗ANA(+),抗dsDNA(+),抗Sm(++),抗SS-A/R060(++),抗SS-A/R052(++),抗SnRNP(++),抗P0(+)。
2021年1月5日入院后檢查:血常規WBC 1.27×109/L,RBC 2.99×1012/L,HGB 92.00g/L,PLT 82.00×109/L;肝腎功能:ALT 57.10 U/L,AST 86.70 U/L,LDH 596.20 U/L,Urea 3.67 mol/L,Scr 48.00 μmol/L,GLU 5.87 mmol/L;補體C3 0.57 g/L,補體C4 0.17 g/L;IgG 129.57 IU/mL(0~30 IU/mL);抗ANA系列結果同門診,尿蛋白定量(行經,1月11日) 529.00 mg/24 h,術前八項、心電圖、胸部CT未見明顯異常。
右頸側皮損組織病理示:表皮輕度角化過度,基底細胞液化變性,見數處色素失禁,真皮淺層血管和附屬器周圍見多量漿細胞和淋巴組織細胞浸潤(圖2)。
診斷:系統性紅斑狼瘡。
診療過程:入院次日,給予靜脈滴注甲潑尼龍40 mg/d,患者持續中高熱,體溫最高達39.6℃,發熱期間多次行血培養檢測顯示陰性,入院后血常規中白細胞、血小板持續下降。2021年1月6日起,連續3日給予靜脈滴注甲潑尼龍120 mg/d,體溫逐漸下降至正常,皮疹炎癥減輕,關節疼痛緩解。2021年1月8日,血常規:WBC 1.15×109/L,HGB 86.00 g/L,PLT 69.00×109/L,提示血象仍未改善。2021年1月9日,根據糖皮質激素在SLE患者合理應用的專家共識[1],給予甲潑尼龍500 mg/d大劑量沖擊、升白細胞藥(瑞白)與靜脈注射人免疫球蛋白(10 g/d)(4瓶/d)半量沖擊治療,但當晚出現精神興奮、失眠、對答不準確、鼻腔黏膜出血等癥狀,加用鎮靜劑;次日繼續沖擊治療,復查血常規:WBC 9.22×109/L,HGB 96.00 g/L,PLT 92.00×109/L,提示血象回升近正常水平。2021年1月11日,甲潑尼龍減量至80 mg/d(繼續使用丙種球蛋白1天)。2021年1月13日,復查血常規:WBC 2.44×109/L,HGB 103.00 g/L,PLT 88.00×109/L,提示血象再次明顯下降,伴鼻腔黏膜少量出血,征得患者及家屬同意后,給予利妥昔單抗(美羅華)500 mg治療。2021年1月15日,復查血常規:WBC 16.60×109/L,HGB 102.00 g/L,PLT 103.00×109/L,提示血象恢復正常,且皮疹炎癥、關節疼痛等其余癥狀基本恢復正常。2021年1月19日,再次給予利妥昔單抗500 mg治療。次日出院,改服潑尼松60 mg/d維持治療。
出院后,繼續完成利妥昔單抗治療療程(500 mg/周×2周),糖皮質激素逐步減量,病情穩定,復查血常規、血生化等均正常。其后,在2022年2月10日、2022年10月17日,分別予利妥昔單抗(美羅華)500 mg鞏固治療1次(總共6次)。隨訪至目前,2023年5月1日(出院后約2.5年),以潑尼松片10 mg/d、羥氯喹0.2 g/d維持治療,病情穩定。
討論系統性紅斑狼瘡(SLE)是一種可累及多系統、多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據統計,女性發病率約為男性的10倍[2]。目前,SLE的治療包括糖皮質激素、羥氯喹、環磷酰胺、嗎替麥考酚酯等多種藥物。然而,SLE的致病因素復雜,其病理機制未明,故單一藥物難以控制病情。特別指出的是,典型的SLE患者通常屬于育齡期女性,常用的免疫抑制劑(如環磷酰胺)可能因其致畸、致癌等特性對生育能力產生短期或長期的不良影響[3]。一般認為,自身產生的抗體和免疫復合物會在多個器官大量沉積,導致出現皮疹、關節炎、漿膜炎、血細胞減少、腎炎和神經精神異常等一系列癥狀[4,5]。其中,B細胞作為抗原提呈細胞,將自身抗原提成給T細胞,T細胞激活并誘導B細胞分泌自身抗體。因此,B細胞在SLE發病機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采取某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減少B細胞,則對SLE疾病控制會產生積極的作用[5]。利妥昔單抗(rituximab, RTX)是一種人鼠嵌合的CD20單克隆抗體,可與B細胞表面的CD20結合,通過抗體及補體介導的細胞毒作用及誘導B細胞凋亡,特異性殺傷表達CD20的B細胞,從而阻斷炎癥反應、減少細胞因子和自身抗體的產生,最終能夠控制SLE病情[6]。盡管目前尚無根治SLE的藥物,但是生物制劑(如利妥昔單抗)有助于減輕SLE患者的病痛,提高生活質量,給患者帶來長期獲益。
本例患者為中年女性,病程較短(2個月),臨床以顏面部水腫性蝶形紅斑、關節炎、全血細胞減少、發熱為特點。根據系統性紅斑狼瘡國際協作組發布的標準(2012年),患者滿足臨床標準:亞急性皮膚狼瘡改變、關節炎、腎臟病變、貧血、白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及免疫學標準:ANA(+)、抗dsDNA(+)、抗Sm(++)、低補體,故符合系統性紅斑狼瘡的診斷標準。患者在住院早期,血細胞三系呈進行性降低,伴有發熱、乏力及鼻腔黏膜出血,主要治療措施采用從標準量激素遞增到500 mg甲潑尼龍(聯合丙種球蛋白)沖擊治療,皮疹與血象等癥狀均得到改善,但出現精神癥狀等不良反應。予糖皮質激素減量,病情反彈,伴鼻腔黏膜少量出血。使用RTX治療,病情好轉,辦理出院。隨訪2.5年,病情穩定。
該患者入院后血液指標進行性、快速惡化,出現全血細胞減少,符合SLE血液危象臨床特點。因其血液系統損害突出,并對使用大劑量、沖擊劑量糖皮質激素傳統治療抵抗,因此我們查閱文獻以尋求更適合該患者的治療方案,發現國際上關于RTX治療SLE的給藥方式尚無統一標準。目前,有3種主流的給藥方式:(1)小劑量RTX:100 mg/次,1次/周,共4次;(2)標準劑量RTX:375 mg/m2,1次/周,連續4周;(3)2劑療法:RTX單次使用 500 mg或者1000 mg,第1、15天各用1次[7]。我們采用RTX 375 mg/m2×4次的標準劑量用法,在僅使用2次RTX后,SLEDAI評分由入院時21分降至出院時5分,即疾病活動度由重度降至輕度,未出現因使用RTX所帶來的嚴重感染等并發癥,療效顯著。由此可見,RTX既能快速改善血象、降低疾病活動度,又能減少糖皮質激素用量,避免相應的不良反應,逐漸成為SLE患者的一種新型治療策略。
隨訪至出院后約2.5年內,共予相同劑量RTX治療6次,病情穩定無復發,亦未出現RTX的嚴重不良反應。據報道,RTX小劑量與標準劑量療效相仿,安全性與依從性更好,并有助于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7]。對于難治性狼瘡,65%~80%患者應用RTX的起效時間為3~9個月,其中血象的緩解率達61%,盡管復發率為25%~40%,約80%患者在重新用藥后還能成功獲得療效[8-12]。目前,按需使用RTX,或者重復使用,還沒有明確的答案[13]。需要指出的是,患者在使用RTX時可能存在并發嚴重感染的風險,在RTX聯合大劑量糖皮質激素沖擊治療時,應該密切留意感染的征象。當SLE合并嚴重血液系統損害時,RTX的應用時機、治療間隔、使用劑量、療效及并發癥等諸多經驗還須進一步積累。本文報道的RTX臨床應用案例,對SLE的個性化治療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參考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