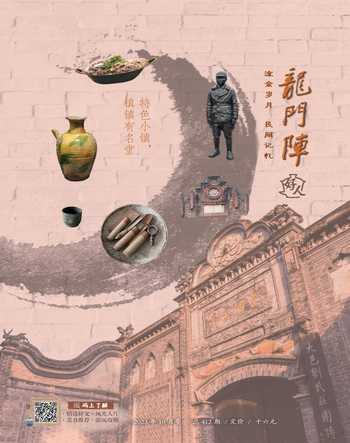走街支磯石
朱文建
成都支磯石街是一條普普通通的小街,但它又不是一條普通的街,與兩千多年前的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西漢學者有著密切的聯系……
仙氣小街支磯石
我住在成都北門青龍場,五月天里頂著大太陽騎著共享單車,去往支磯石街。支磯石街是有塊支磯石的,清代金朝覲《支機石》詩云:“想是媧皇煉未成,相隨織女下昆明。自從此石來天上,博得西川作錦城。”說的就是支磯石的來歷。
街口的巨石自然不是女媧娘娘的那一顆補天石,但不過四五百米的支磯石街自帶一種“占卜算卦,仙風道骨”的氣場。這跟一個人有關,他就是西漢的嚴君平。
嚴君平(約公元前80年—公元10年),本名莊遵,字君平,東漢史學家班固在著《漢書》時,為避漢明帝劉莊的名諱,而將其姓由“莊”改為“嚴”。 嚴君平是西漢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天文學家,與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并稱為“蜀中四君子”。左思《蜀都賦》概括蜀中人杰地靈時說:“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其中嚴君平最為奇特,皭若君平,皭然泥而不滓也。
嚴君平性情高潔,他不愿做官,不愿被束縛,云游四方,教書授徒。他來到成都住在一條偏僻的小街上,每天以占卜算卦為生,并自得其樂,心靜如水,無欲無望。每天掙得一百錢,夠自己生活就收攤,后面給再多的錢都不做,回到破舊的茅草小屋里讀《老子》。蜀中富人羅沖見他一個大儒又不當官,過得如此清貧簡單,就準備行施舍之舉,給他一些車馬錢糧。羅沖來到小屋表達心意,也是要在嚴君平面前炫耀一番,你不愿做官就給你些錢糧。
嚴君平全然不受,并說出一個哲理——富人是在不斷以自己的不足來彌補多余。羅沖不明白,問他什么意思。嚴君平說:“你為這個家日夜操勞,掙下了千萬財產,但你還是從未感到滿足過,還在繼續地挖空心思去掙去彌補,一輩子都是如此。而我就以簡單的卜筮為業,不用下床就有人把錢送上來,這是多輕松的事!我現在屋里還余數百錢找不到可用的地方,要不給你?這當然就是我有余而你不足了。”說得羅沖臉紅筋脹,默然離去。
《漢書·鄭子真、嚴君平傳》載:“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子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曰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余萬言。”
嚴君平淡泊名利,但這條無名的小街卻因他的到來而熱鬧起來,每天前來找嚴君平問卜算卦的人絡繹不絕,小街沾了人氣更沾滿了仙氣。
據說成都還有專備嚴君平所用的“通仙井”,而這種“井”,廣漢也有,郫縣也有。這井并不是普通水井,而是“仙道”,一條條供神仙出入的地下快速通通道。嚴君平利用“通仙井”在各地往來自如,從成都眨眼間就能來到廣漢,擺上賣卜臺,讓人產生錯覺。唐代詩人岑參任嘉州刺史離任,追尋杜甫不成,轉道來成都,除了踏歌駟馬橋,看望司馬相如舊跡,還在這條小街上尋找過嚴君平的足跡,他在《嚴君平卜肆》一詩中說:“君平曾賣卜,卜肆蕪已久。至今杖頭錢,時時地上有。不知支機石,還在人間否。”
我把共享單車停在街邊,拿出手機拍了一下支磯石,接著用雙腳在支磯石街上來回丈量著,穿行于遠去的歲月當中。在一處樓下的窗戶邊,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我忽然找到一塊不起眼的小石塊子,上書:君平卜肆。下面是岑參的兩句詩:君平曾賣卜,卜肆蕪已久。這里就是當年嚴君平擺攤賣卜的地方,地方依舊在,卜肆已荒蕪,賣卜人早就遠去了。
名師出高徒揚雄
查閱史料,嚴君平并不單是算卦賣卜之類,這只是他的一個業余事,一個謀生的手段,他更多的是鉆研學術,教書育人,并教出了西漢一代文豪大儒揚雄。
嚴君平在成都做了幾年時間的卜筮業不得而知,有一句話叫大隱隱于世,他卻是反其道而行之,來到離城不遠的郫縣橫山子隱居下來。橫山子又稱平樂山、桓山子。平樂山不大,山勢不高,也并不雄偉,就是平川上一個突起的小山丘,嚴君平則看中了這里景色,樹林蔽蔭,環境優雅,他在山上著書立說,開辦橫山讀書臺,開創了私人辦學的先例。嚴君平廣招學生,許多有志青年慕名而來,其中就有揚雄。
揚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縣人,漢代大辭賦家、思想家,因為口吃,不善于表達,不過,他心里很想成為司馬相如那樣的文人。揚雄遵照傳統的拜師禮,拜嚴君平為師。向嚴君平行過禮后遞上十條臘肉。嚴君平擺手說:“算了算了,不講究這些。”《論語·述而》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是孔子的話,意思是只要自愿拿著十塊干肉來見我的人,我從來沒有不給他教誨的。嚴君平則是看中了揚雄這個學生頗有靈性,心中有貨,凡事有自己的見解。
揚雄如饑似渴,孜孜不倦,在橫山一學就是八年,可說是盡得嚴氏精髓,后來終于成為一代大家,受后世景仰。揚雄學成后在京師做官,廣為宣傳嚴君平的思想體系,與人交談把盞,每每懷念起橫山讀書臺的美好時光,《漢書·鄭子真、嚴君平傳》說:“揚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群平德。”
橫山讀書臺吸引著歷代文人學者前來參觀憑吊,包括李白。就連《李翰林集序》都不忘提到嚴君平:“自盤古開天地,天地之氣艮于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則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杰出。是生君平、相如、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嚴君平的聲名和影響力可見一斑。
支磯神石傳神話
支磯石街的得名源于那塊大石,更在于相關傳說中,嚴君平“認識”并“定義”了那塊大石,大石因嚴君平而名。
相傳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張騫來到了大夏大河的盡頭,用船載回來一塊大石頭,不知是何物。嚴君平智謀高深,知曉天地,張騫將大石運來成都,求問嚴君平。
嚴君平審視大石半晌,對張騫說,“這是天上的石頭,你已經到了天邊了。去年我看到有客星侵入牛郎、織女星座就覺得奇怪,原來你已經到了日月旁邊了。這是天上織女的支機石啊!”
張騫十分驚訝,他說:“我來到河的盡頭,見一個女子在織錦,一個男子在牽牛,問這是什么地方。女子說:‘這不是人間,你怎么來這里了?叫我把這塊石頭帶回去問西蜀君平,會告訴我到了什么地方。”
這個傳說故事,在《蜀中廣記》有“原型”記載:“初,博望侯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歸舟中載一大石,以示君平。君平咄嗟良好曰:‘去年八月有客星犯牛,女,意者其君乎?此織女支機石也。……”
其實這就是一個神話傳說,張騫和嚴君平雖同為西漢人,但并不是一個年代的,對不上號。張騫奉漢武帝命入蜀開辟古老的蜀地到印度的貿易之路——蜀身毒道,也并沒有帶來什么大石。實際情況有可能是,西漢某個人以大石來求問嚴君平,明人曹學佺在編撰《蜀中廣記》時,就直接或也是根據相關傳說安在了張騫頭上,這大概是張騫有名,嚴君平也有名,如此編撰更有神話傳奇性吧。
有文化氣息的街
支磯石街不僅是一條賣卜算卦的街,一條神話傳說的街,還是一條文化氣息濃厚的街。最為著名的就是在同仁路相交處有一處古色古香的大四合院,雖不及“庭院深深深幾許”那樣幽深縱橫,也看得出是有上百年歷史的大院,這就是著名的成都畫院的所在地。
1980年,成都畫院在這里成立。成都畫院是改革開放后全國第一批由政府組建的從事書畫創作和美術理論研究、學術交流的專業機構,經常舉辦藝術畫展,開辦藝術創作活動。成都畫院的前身是五代時期后蜀孟昶所創辦的翰林書畫院,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家畫院,形同第一個國家高等美術院校,被視為中國畫院體制的始祖。畫院墻上展示出各種風情的國畫,山川、人物、節氣等等,更給支磯石街增添了不少的書香氣。
在改造支磯石街和同仁路時,最初規劃是要將這座古老的四合院全部拆除,夷為平地。為保留這座珍貴的建筑,人們重新規劃,才使得這個典型的川西四合院古建筑得以保存。
從街上走過就會看到,街墻上種植著各種綠色植物,墻上還有題詩,盛贊成都之美,給古老的小街增添了人文氣息。唐代田澄《成都為客作》說:“蜀郡將之遠,城南萬里橋。衣緣鄉淚濕,貌從客愁銷。”元代虞集《題王庶成都山水畫》說:“蜀人偏愛蜀江山,圖畫蒼茫咫尺間。駟馬橋邊車蓋合,百花潭上釣舟閑。亦知杜甫貧能賦,應嘆揚雄老不還。花重錦官難得見,杜鵑啼處雨斑斑。”也有杜甫《春夜喜雨》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墻上還嵌有一首浮雕式的詩句,凹凸錯落,更是別具一格。這是民國時期著名詩人、游記作家易君左的《成都》一詩:“細雨成都路,微塵護落花。據門撐古木,繞屋噪棲鴉。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風味足,楚客獨興嗟。”
1939年1月,易君左從重慶來成都游歷七天,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獨特魅力,美不勝收,是名副其實的錦繡之城,他寫下的《錦城七日記》,筆墨或濃或淡,或敘或描,將錦城的秀美展示在世人面前。
街兩邊打造成傳統的川西民居風格,灰白色的建筑墻面幽雅而別致,古老的黃桷樹和銀杏樹競相成長。看著眼前的景物,我又想到以前的支磯石街,那是一個怎樣的景象呢?
據當地老住戶介紹,和許多老街舊街一樣,以前的支磯石街也是凌亂不堪,街上污水橫流,街兩邊棚戶張揚,擺放著雜七雜八的貨品。棺材鋪老板終日黑喪個臉,顯得陰森恐怖,有叫花子來討要:“老板的棺材做得好,裝起死人不得跑。”如果店老板吝嗇,一毛不拔,那又是另一個說詞:“老板的棺材做得戳,裝起死人要跑脫。”有鍋盔攤子,也有一句話:“風大雨大,肖麻子的鍋盔要漲價……”在那個年代里,好多年輕人,都搬離了支磯石街,到別處去了。街邊偶見有擺攤算命看相的,似乎還在延續著當年嚴君平的行當。
支磯石街的改造是在十多年前,治理臟、亂、差,統一街道設施,打通污水管道,經過努力,一條全新的街道呈現在世人面前,再不是一副的邋遢相,變得整潔好看、設施俱全了。支磯石街與熱鬧的寬窄巷子隔街相望,一些人看夠了熱鬧的寬窄巷子,難免不拐個彎來這里做另一番享受——清幽雅靜。如今,一些有志氣有想法的年輕人又回到了支磯石街上,開起了各種各樣的店鋪,這里的煙火氣息又漸濃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