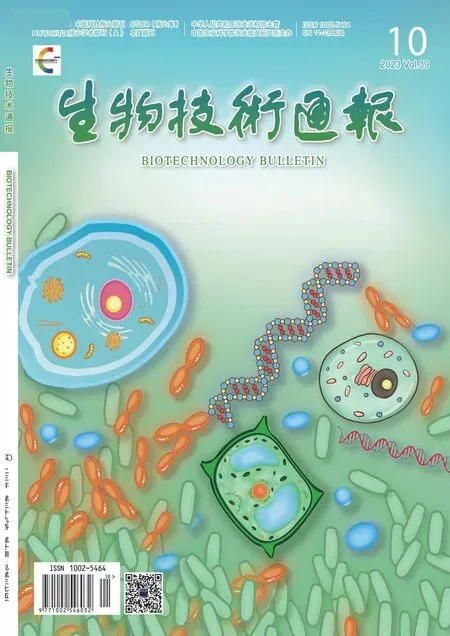抗豬繁殖與呼吸障礙綜合征基因編輯豬研究進展
李雙喜 華進聯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動物醫學院 陜西省干細胞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楊凌 712100)
國家生豬產業體系對我國生豬產業現狀的調研顯示,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豬繁殖與呼吸障礙綜合征(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PRRS)和豬流行性腹瀉(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PED)是影響我國生豬生產的最重要的三大疫病。其中,PRRS是一種由豬繁殖與呼吸障礙綜合征病毒(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引起豬群發病的傳染性病毒性疾病,在臨床上主要表現為母豬的繁殖障礙和生長育肥豬的呼吸系統紊亂。雖然近兩年在田間流行的類NADC30和類NADC34毒株尚未造成大面積疫情暴發,但對豬群健康的影響持續存在[1]。此外,從豬場經濟學的角度來看,PRRS是對豬場經濟影響最重要的疾病。目前對于該病的防控主要依賴于養殖場內外部生物安全體系,采取合理措施降低病毒的污染,切斷病毒傳播途徑。
從保護易感動物的角度而言,抗病育種也是疫病防控的重大策略之一。近年來,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和成熟,分子育種作為豬抗病育種的核心技術,已取得很多突破性進展。本文以PRRSV受體為切入點,綜述豬抗PRRS育種的研究現狀,以期為PRRS的防控和豬的抗病育種研究提供線索。
1 PRRS流行和防控現狀
豬繁殖與呼吸障礙綜合征于1987年首次在美國報道,該病在臨床上的癥狀表現為母豬流產、早產、木乃伊胎等繁殖障礙,斷奶豬的呼吸道癥狀、生長遲緩以及死亡率增加。當時由于病因不明,稱其為“豬神秘病”。1991年,在歐洲首次分離到該病病原,稱為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病毒(PRRSV),并命名為Lelystad[2]。北美分離株VR?2332于1999年分離,并進一步獲得該毒株的全基因組序列[3]。根據基因序列的差異,PRRSV可分為歐洲株(PRRSV?1,代表毒株Lelystad)和美洲株(PRRSV?2,代表毒株VR?2332)兩個基因型,二者的核苷酸序列相似性為50%-60%,且均能夠引起長期感染并且具有相似的臨床癥狀[4]。在2020年國際病毒命名委員會發布的最新病毒分類報告中,這兩個基因型作為兩個種,分別命名為豬β動脈炎病毒1型和2型[5]。
我國于1995年底在華北地區規模化豬場首次暴發PRRS[6-7]。隨后,PRRS在我國豬群中不斷傳播[8]。2006年,高致病性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highly pathogenic PRRS,HP?PRRS)在我國暴發,在臨床上表現為高熱、高發病率和高致死率,造成大量豬只死亡,重創當時的養豬產業。HP?PRRS自2006年后成為我國豬只中流行的優勢毒株[9],并傳入周邊國家[10]。2014年,我國相繼出現類NADC30毒株[11-12],成為我國優勢流行毒株之一,且該毒株易與其他的毒株發生重組。同年,美國首次報道NADC34毒株[13],而我國于2017年在東北部地區檢測到與之相似的毒株——類NADC34毒株[14],之后中部地區多個省份也陸續檢測到了該類毒株[15-16]。與類NADC30毒株相似,類NADC34毒株也易與其他毒株發生重組。PRRSV極易變異和重組的特性,致使新毒株層出不窮,給該病的防控帶來了嚴峻挑戰。
疫苗是防控傳染病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然而對于PRRS而言,滅活疫苗基本無效,減毒活疫苗目前在豬場免疫較為普遍,可對同源毒株提供臨床保護,但是對異源毒株的交叉保護非常有限,甚至是無效的[17-18]。PRRS治療方法也大多停留在研究階段,尚未有可在臨床上應用的有效治療性藥物。因此,在生產實踐中常采用完善和加強豬場生物安全、合理使用疫苗、剔除陽性豬只、馴化陽性場等多項舉措并施來防控PRRS,使豬群處于相對穩態[19]。抗病育種豬是PRRS防控的新策略。隨著近年來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和成熟,使得對動物基因組特定位置的編輯變得更加簡便、精準和快速。國內外多個研究團隊也利用該項技術對豬進行基因編輯,進行抗PRRS育種研究和探索。
2 抗PRRS基因編輯豬研究進展
基因編輯是指利用基因編輯工具對細胞、植物或動物基因組中進行特定基因序列的插入、刪除或突變,從而改變該基因的表達。基因編輯工具以核酸酶為主要成分,最初的基因編輯工具為鋅指核酸酶(ZFNs)基因編輯系統,該系統剪切效率低,且易產生非特異性脫靶切割[20]。2009年出現轉錄激活子樣效應子核酸酶編輯系統(TALENs),與鋅指核酸酶基因編輯系統相比,該系統識別位點多、剪切效率高,且操作簡便,節省時間[21]。近年來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已成功應用于體內外基因治療、動植物抗病育種等多個方面[22]。
目前,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是在基因編輯豬中應用比較廣泛的基因編輯技術。國內外針對抗PRRS基因編輯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造PRRSV受體血紅蛋白清道夫受體(haemoglobin scavenger receptor)分子。大量的研究證實,CD163可以介導PRRSV入侵細胞,且被認為是眾多受體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分子。CD169雖然也可介導病毒內化,但是研究表達該蛋白并非PRRSV感染所必需的,且敲除該基因對PRRSV感染無明顯影響[23]。因此,近年來國內外多項研究致力于CD163敲除或功能域缺失對PRRSV感染的影響。
2.1 CD163蛋白的結構與功能
PRRSV在豬體內的靶細胞是豬肺泡巨噬細胞(porcine alveolar macrophage,PAM)。研究發現多種細胞受體可介導PRRSV進入PAMs,包括CD163(cluster differentiation 163)、唾液酸黏附素(sialoadhesin,Sn;CD169)、硫酸乙酰肝素(heparin sulphate,HS)、波形蛋白(vimentin)、CD151分子、樹突狀細胞表面的DC?SIGN(CD209)以及肌球蛋白重鏈9(MYH9)。其中,CD163分子研究最為廣泛。
CD163分子,又稱血紅蛋白清道夫受體,屬于I型膜蛋白,分子大小為130 kD,包含9個清道夫受體超家族(scavenger receptor cysteine?rich, SRCR)結構域,富含半胱氨酸[24]。豬源CD163基因含有7個外顯子,編碼的CD163蛋白包括N端信號肽,9個SRCR結構域、2個脯氨酸-絲氨酸-蘇氨酸(PST)域和C端胞內域,其中PST結構域分別位于SRCR6和 SRCR9之后[25]。
CD163蛋白可作為多種分子的受體,參與維持機體的自身穩態。首先,在機體受到病原感染或組織發生損傷后,CD163蛋白發揮清道夫分子作用。CD163蛋白可通過其SRCR2?SRCR3結構域結合血紅蛋白-觸珠蛋白復合物,該復合物經內吞進入巨噬細胞內體和溶酶體,最終清除游離血紅蛋白,從而維持機體處于健康狀態[26-28]。其次,CD163分子可作為腫瘤壞死因子樣凋亡微弱誘導劑(TNF?like weak inducer of apoptosis, TWEAK)受體,與后者結合后參與調控腫瘤細胞的增殖或凋亡[29]。同時,CD163分子屬于成紅血細胞黏附分子,它與成紅細胞相互作用,在紅細胞生成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30]。此外,2005年Fabriek等[31]研究發現表達CD163的巨噬細胞或可溶性CD163在炎性組織中大量存在,提示其通過巨噬細胞調節細胞因子的釋放,在機體防御中發揮作用。
除了發揮以上生理功能之外,CD163分子還可作為PRRSV感染的受體。2007年,Calvert等[32]的研究首次發現CD163分子與PRRSV感染高度相關,是基因I型和II型PRRSV的受體。CD163主要介導PRRSV在細胞質中的脫衣殼和病毒基因組的釋放,并且已經確定CD163的病毒結合區為SRCR5?SRCR9,胞外N端的SRCR1?3不影響CD163與PRRSV結合的受體活性。2009年,Van Gorp等[33]在CD163之前的研究基礎上,通過構建缺失突變和嵌合突變體,進一步鑒定受體結合區域。攻毒感染試驗揭示了SRCR5結構域在PRRSV感染中是必需的,而N端4個SRCR結構域和C端胞質區不參與病毒感染過程。除此之外,其余的CD163蛋白區域需要保留,但若將其替換為CD163?L1(CD163b)的SRCR區域,則可引起感染效率降低(SRCR6及域間區)或不變(SRCR7?SRCR9)。另外,該項研究還證實,識別CD163?SRCR5的特異性抗體可降低PRRSV的感染。隨后的研究解析了SRCR5的晶體結構信息,通過突變實驗揭示在長環(long loop)區域的561位的精氨酸殘基在PRRSV感染中發揮重要作用,進一步分析得知很可能是在病毒入侵過程中其參與CD163與PRRSV的結合[34]。病毒凋亡模擬(viral apoptotic mimicry)作為一種新型感染方式,在PRRSV感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發現PRRSV囊膜表面暴露有磷脂酰絲氨酸(PtdSer)模擬凋亡,T 淋巴細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T cell immunoglobulin domain and mucin domain,TIM)等可通過該物質識別PRRSV感染,進而通過CD163分子介導病毒入侵[35]。
2.2 以CD163為靶標的基因編輯豬抗PRRS研究現狀
CD163分子在PRRSV復制周期的作用使其成為基因編輯豬抗PRRS研究的重要靶點。近年來國內外很多研究關注在缺失CD163受體的豬只對PRRSV的易感性。利用CRISPR系統結合體細胞移植技術,對豬CD163基因進行有針對性的編輯。待獲得基因編輯豬后,利用豬只或者從豬只上分離PAMs,分析其對不同PRRSV毒株的易感性。
2016年,Whitworth等[36]首次使用CRISPR/Cas9編輯技術敲除已經報道的PRRSV受體發現,敲除CD163分子SRCR5結構域的豬能夠完全抵抗II型PRRSV感染。隨后,許多研究團隊開始了針對CD163的抗PRRSV感染豬的基因編輯育種工作。次年,有研究發現完全敲除CD163分子或者缺失SRCR5結構域的豬只及其PAMs細胞對基因I型和II型PRRSV毒株均不易感,而利用人源類CD163分子(hCD 163L1)SRCR8區域替換豬源CD163分子 SRCR5區域,表達嵌合CD163分子的豬只和PAMs,只對基因I型毒株耐受,對基因II型毒株仍然易感[25]。然而,Chen等[37]發現hCD 163L1結構域替換豬源CD163分子SRCR5結構域的基因編輯豬對高致病性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病毒(HP?PRRSV)不易感。另一研究團隊的結果表明,CD163分子SRCR5結構域缺失的豬只及PAMs和集落刺激因子因子1刺激的外周血單核細胞(PMMs)對基因I型高致病性毒株不易感。值得注意的是,除基因I型外,PMMs對基因II型的毒株也不易感[38-39]。
2018年,Yang等[40]研究也發現用HP?PRRSV TP毒株感染CD163基因敲除豬后,豬只不表現出病毒血癥、抗體反應、高熱以及其他PRRS相關臨床癥狀,提示其可完全抵御病毒感染。2019年,Guo等[41]利用雙熒光篩選的方法提高了基因編輯豬的陽性率,并發現只缺失CD163分子SRCR5結構域41個氨基酸(缺失區域包含病毒受體結合位點)即可使豬抵抗基因II型毒株JXA1和MY毒株的感染。多基因同時敲除從而獲得抵抗幾種病毒感染的豬只更能迎合當下疫病防控的需求。2020年,Xu等[42]首次通過CD163和pANP雙基因敲除獲得了能同時抵抗基因II型PRRSV、TGEV和德爾塔冠狀病毒的編輯豬,在肉質品質和繁殖性能上,與野生型無差異,但在雙缺失型豬只的肌肉中檢測到升高的鐵。表1歸納總結了當前以CD163為靶標的基因編輯豬抗PRRS的主要進展。

表1 以CD163為靶標的基因編輯豬抗PRRS的主要進展Table 1 Advances in anti-PRRS gene-editing pigs targeting CD163
除了靶向PRRSV受體CD163分子對豬抗PRRS進行探索之外,研究人員也在挖掘病毒感染過程中的關鍵宿主因子,以期篩選出新的靶標。利用全基因組基因敲除的豬源gRNA文庫及高通量基因篩選技術篩選并在細胞水平上鑒定IL20RB、ATP6V0A1和STX10均可顯著抑制PRRSV感染,為抗PRRS育種的研究奠定基礎[43]。
在基因編輯方法上,近年來也取得一些重要進展。Xu等[44]開發了一種稱為報告RNA富集的雙引導RNA核蛋白(RE?DSRNP)編輯技術,可用于快速構建無外源DNA基因編輯的克隆豬。該技術可提高編輯效率,避免質粒DNA隨機整合到目標細胞的基因組,同時無單克隆細胞選擇過程,縮短體細胞培養時間,降低體細胞異常比例。本實驗室通過比較不同sgRNA的表達策略發現,連續的 sgRNAs表達盒策略可以顯著提高豬源細胞的多基因編輯效率,并對仔豬全基因組測序,驗證了該方法的安全性。近期,有研究團隊通過把二元四環素誘導表達元件分別精確插入Rosa26和Hipp11位點,建立多西環素誘導SpCas9表達(DIC)豬模型。在該模型基礎上,構建了一種基于Cas9條件敲除豬基因的方法。該方法可通過藥物和sgRNA調控基因的沉默和過表達。DIC豬模型也可作為開發單一轉基因整合的基本工具,對豬進行時空基因敲除,從而對一些復雜的疫病進行復制,進從而精準剖析蛋白功能。而且,DIC豬SpCas9蛋白表達的可調控性對探究該蛋白的劑量及譜系示蹤研究至關重要[45]。
綜上所述,關于抗PRRS豬育種已經取得許多重要研究進展,但是仍有一些問題是需要認真思考的。由于CD163的表達屬于顯性性狀,遵循經典的孟德爾遺傳定律,CD163-/-的親本與野生型CD163+/+雜交會產生雜合CD163+/-胎兒,該胎兒能夠表達正常的CD163蛋白。可喜的是,研究發現CD163基因敲除的母豬可以充分地保護仔豬免受PRRSV感染。盡管CD163基因敲除母豬產出的表達CD163分子后代在出生后對病毒存在易感性,但在母體內存在針對PRRSV的保護能夠很大程度上減少經濟損失以及滿足動物福利的要求[46]。
3 展望
傳染病防控三要素包括消滅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以及保護易感動物這三方面,培育具有抗病基因的動物就是從保護易感動物這個角度入手進行研究,在農業領域,具有抗蟲性、抗寒性、抗鹽堿性的作物,如水稻、棉花等作物的生物措施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植物與人的親緣關系較遠,具有天然的遺傳屏障,相對較為安全,而在動物上的轉基因操作出于倫理、人獸共患病等方面的考慮,科學界及社會則從未停止過爭論。
近幾年對于抗病豬的育種研究,研究人員取得了大量突破性的進展,包括抗PRRSV(CD163)單基因編輯豬、抗PRRSV/TGE(CD163/pAPN)的雙基因編輯豬,都為未來豬病的防控開辟了新的道路。此外,一些特定品種的豬對某些疾病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通過分析比較基因組差異,編輯差異位點也是抗病育種的一個思路。例如,2020年McCleary等[47]通過對比較易感非洲豬瘟病毒的家豬和不易感的非洲疣豬的基因組序列分析后發現,RELA基因存在3個單核苷酸多態性位點差異,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將非洲疣豬的SNP替換到家豬上獲得基因編輯豬,該豬感染非洲豬瘟病毒產生臨床癥狀的時間晚于野生型豬,且排毒量也較低。2018年Xie等[48]應用CRISPR/Cas9為基礎的定點整合(knock?in)平臺,結合RNA干擾技術,將篩選出的能有效抑制豬瘟病毒復制的shRNA基因精確整合至豬內源Rosa26基因啟動子區域的下游,成功地篩選出能穩定表達抗病基因的細胞系。接著通過體細胞核移植技術和胚胎移植技術成功地獲得抗豬瘟病毒的基因編輯豬。體內外攻毒實驗均證實這些基因編輯豬能有效限制豬瘟病毒的感染并能顯著地降低豬群中豬瘟疾病相關的臨床癥狀和致死率。隨后,該團隊又在豬基因組上發現另一外源基因整合位點miR?17?92基因簇,通過將針對豬流行性腹瀉病毒的shRNA整合到該位點可獲得抗病基因編輯豬。這些研究都為抗PRRS基因編輯豬的探究提供了線索[49]。綜上所述,基于基因編輯及多能干細胞手段賦予豬體抗病毒能力的方法是一種有效的抗病育種策略,或者篩選更加有效的抗病靶標及策略[50-52],且其具有非常廣闊的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