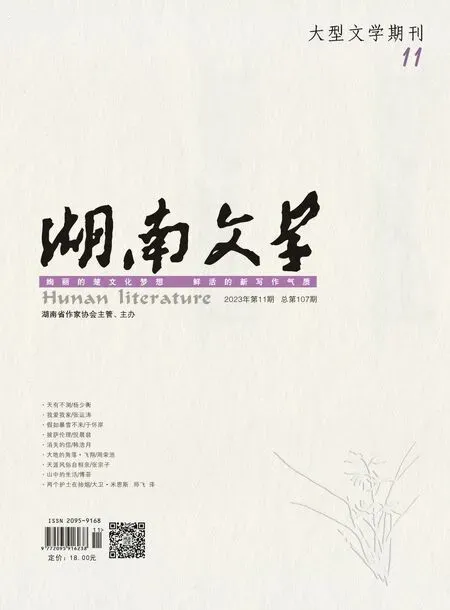千磚萬瓦窯
陳焰
秦磚漢瓦,顧名思義就是秦代的磚頭好、漢代的瓦當好。民間建房造屋的青磚青瓦雖說質(zhì)地沒有那么優(yōu)良,也沒有那么好看的圖飾紋樣,但制作過程應該差不多,都是將泥坯放到特制的窯里燒出來的。我外公家的房子建于清代,我小時候他家房子還沒損壞,雕梁畫棟的,燒制后經(jīng)過打磨的墻磚,磨刀石一樣光滑,磚上刻有云形圖案,如此精益求精,除了有錢,還必須有一個不浮躁的社會大環(huán)境。我多次扮磚造屋,磚瓦就做得粗糙許多,不僅磚尺寸大了許多,更談不上圖飾。物質(zhì)匱乏的年代,蓋房就只為有一個遮風避雨的窩。
一
我居住在湘北一個小山村里,祖上留下一棟房子,到我父輩,兄弟幾個每人只分得一間。有了我兄弟后,父母扮磚燒窯又做了一間。一九五八年,糧食鍋碗犁耙無償歸公,房屋也歸了公,村子里的人全部分遷到附近兩個村莊居住吃公共食堂。說是“陳磚頭當大糞”,隊長一聲令下,我父母做的那間房就被拆了,泥磚倒進田里,火磚和瓦挑到鄰村做了公共廁所。
一九六○年底散食堂,大家依舊回到原來的住所。那年我十五歲,輟學回了家,下面兩個八歲的雙胞胎弟弟,一家五口只有一間房。父親只好在堂屋樓上開個行鋪,我就睡在三叔房里。第二年環(huán)境寬松了些,可以開墾小片荒地種菜,可以喂雞養(yǎng)豬,可以做點小生意,大家慢慢恢復了些元氣。父親和我商量,扮點磚,把拆掉的那間房再做起來。收了中稻有了口糧,屋場里幾個缺房戶合伙開了個泥塘扮磚。以前扮磚燒窯請外地師傅,這次大家自己干,也省了請人的嚼用。我負責捏掿坨,還學會了掌架扮磚,開始我一天能扮一千三四百塊,后來一天能扮千七八。
那年冬天雨雪多,沒法打窯,如果等到春雨來時,泥磚就會變回一堆爛泥。鄰村金華叔待人和善,我去借他的窯燒磚,他將自己的一窯青磚先換給我,說等我的磚燒好了再還給他,我就可以一擔泥磚送去,帶回一擔燒磚,這樣就節(jié)省不少工夫。趁著春節(jié)農(nóng)閑,我兩個姐夫也來幫忙,與父親和我四個人挑了三天,總算一窯泥磚送去,一千多塊火磚挑了回來。一塊磚十斤左右,我一擔挑八塊。二姐夫長年挖長石煉起了勁,一擔能挑二三百斤。接著又挑了五六十擔窯柴。
窯是千磚萬瓦窯,意思是燒一窯磚能燒一千塊左右,燒瓦能燒一萬片左右,也可以半窯磚半窯瓦燒,磚裝下面,瓦裝上面。裝窯是門技術(shù)活,磚交錯著裝才能最大面積接受火煉,裝密了不透火,疏了浪費空間劃不來,而且下面磚之間的空隙要寬松一點,上面緊密一點,因為火往上沖,上面火力比下面大。我請人剛裝好窯,接連下了兩天雨,等天晴才起火燒窯。連軸轉(zhuǎn)的強體力勞動,年過半百身量不大的父親明顯體力不支了,只能幫著搬點柴到窯門口,下半夜柴都搬不動了。第二天元宵節(jié),一早又下起了雨夾雪,我頭上的帽子往下滴水,衣服也濕了,胸前烤著火直冒熱氣,背上又冰涼的,只好給火膛送一抱柴后,又轉(zhuǎn)身烤后背。就這樣堅持了二十多個小時,終于燒下了腳,好了。
窯燒得順利,一般二十個小時左右就燒好了,燒了差不多一半時間,從天心往窯里看,磚燒紅了,還帶著白色光閃閃的邊,就要一步步封天心了。天心是窯頂偏后留的約一尺多點見方的孔,上大下小像個漏斗。封天心的三塊磚在裝窯后就按天心大小削好,放在窯頂備用。封天心時從后往中間一塊一塊封,不能一次封死,要留一點縫帶火往上跑。當封天心的磚也燒到一定程度,火苗從磚縫里躥出兩尺多高了,就用踩熟的泥巴將其密封。
天心關(guān)好后,煙囪的煙明顯由帶有水汽的白煙慢慢變成黑煙,一轉(zhuǎn)一轉(zhuǎn)往外吐。當煙能點燃稻草時,就把煙囪口關(guān)小,關(guān)到三寸左右,把火氣往下壓。不能全關(guān)了,否則火從火門口一竄就出來了。當黑煙慢慢變成青煙,磚就快燒好了,這時從火門口望進去,窯里面的火燒得旺旺的,像紅色的鐵水一般,便可以開始封窯。
封窯必須兩個人:一個人攪窯,用木棍攪火膛里的柴火,讓燃燒的木柴全部變成小炭渣;同時另一個人在窯頂立即把三個煙囪關(guān)好,用泥糊起來,防止泄火,因為下面火勢一小,上面不及時關(guān)煙囪,火力會嗖的一下從煙囪跑掉,就會導致窯內(nèi)火力不足致使磚不成熟。煙囪一關(guān)好,就快速用磚封火門。火門一塊磚寬,三塊磚高,封好后,再用加灰拌好的泥巴將窯門封死,加了灰的泥巴不開裂,熱氣就不會外泄。
封窯后,我去金華叔家換上干衣服。吃過中飯,雨雪也停了,又與父親挑了幾十擔窯田水。封窯后要往里灌水,灌水了磚才轉(zhuǎn)釉,不灌水就是紅磚。一般燒四十擔柴,灌三十擔水,依此類推。窯頂四周像稻田一樣起了土坎圍起來,灌水必須從窯田慢慢往下浸。不能直灌,灌急了灌多了會傷水,磚會碎。灌少了,又不會轉(zhuǎn)釉成青磚,而是紅磚。
皇天不負苦心人,隔一天開窯門一看,清一色的青磚好貨。我把火膛里的炭渣鏟出來,再去開煙囪和天心。這里也有個講究,不能先開煙囪和天心,否則火膛里的炭渣會復燃,已經(jīng)轉(zhuǎn)釉的青磚又會被燒成紅色。待到第二天窯內(nèi)冷卻了出窯,把磚堆好還給了金華叔,金華叔也很滿意。
正月一過,就請人在五八年拆掉的那間房子的原地基上做起了一間房,瓦也沒有,蓋的茅草。
我能掌架扮磚了,后來別人家扮磚就請我?guī)兔Γ艺门c他們換工。我就像燕子銜泥,一點點準備木料,陸陸續(xù)續(xù)與人換工做了一張梨木書桌、一張株木拔步床和一個大衣柜。十八歲生日那天晚上,我睡在自己做的房、請人做的床上,想起已經(jīng)有了三件像樣的家具,心里真是樂滋滋的。
二
一九六七年,我已經(jīng)結(jié)婚生子,妻子又懷上了二胎。一間房不夠用,屋后搭一個小灶,刮風下雨就沒法做飯。增加住房迫在眉睫,可是既無余糧,又無余錢,無法動手。中秋節(jié)去岳母家拜節(jié),聽我說想做房子,老人連忙去打了一籮谷,第二天我挑著三十多斤米和一籮筐干紅薯絲回家,就開始打堤腳開塘踩泥,扮了四天磚,七千多塊。
我摸索著自己打窯,因為沒有經(jīng)驗,打窯的地方水汽太重,剛做好,接著下雨就垮了。
新化縣陳師傅三人在鄰村做瓦,我就去請他們幫忙。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jīng)常有新化、汨羅的師傅在我們這里扮磚燒窯,他們打的窯一窯能燒二千五百塊磚兩萬多片瓦。但無論窯大窯小,式樣是一樣的,就像如今的電飯煲,只是按比例放大或縮小而已。
陳師傅幫我選址在七寸咀上,這里有高墈,當風,土層厚土質(zhì)好。在有一定高度的墈上挖窯比在平地建窯牢固,還節(jié)約工程成本。當風的地方開窯門好理解,俗話說“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我也得到了一些經(jīng)驗:在不積水的地方打窯,地下水少,容易燒,省柴火。否則就算窯打成功了,也不省柴火,遇上久雨,土坯磚受潮損基腳,窯還是會垮。但沙礫石土不行,封窯灌窯田水后,因為沙礫石土過氣,窯內(nèi)的余炭和高溫會繼續(xù)把磚燒成紅磚。再者,土層不厚不堅實的地方容易遇上石頭,鑿煙囪會是個大麻煩。
窯址選好后,先將墈上的斜面整平,畫線確定開火門與煙囪的位置及其長寬等,再行開挖。窯桶和窯門可以同時起土,窯門一般二尺多點寬,門洞四尺左右高,門洞的底比窯桶的底最少要低二尺以上。窯桶豎切面呈扇形,上部寬,火門口窄。
窯桶挖好了,再鑿煙囪,沿著窯桶壁鑿出三個下面大上面小、大致半圓的槽,底部寬約二尺三四寸,比窯桶底深五寸左右。用磚砌煙囪時,在煙囪和窯桶底之間留一個洗臉盆大的口子,中間豎一塊磚做支撐,看上去像個鼻子。上面煙囪口一般七寸長,四寸五寬,一塊磚就能蓋嚴。這個煙囪的設(shè)計真正令人贊嘆,燒窯時,火往上沖,窯頂又把火力和煙氣壓下來,火氣就在窯內(nèi)循環(huán),煙最后從窯桶底部往下鉆入煙囪再排出去。窯內(nèi)的水汽以及可能滲出的少量地下水怎么處理的呢?在窯桶底挖三寸左右深的小溝連接到煙囪,起火后,水多了會往小溝里匯聚,再流到煙囪里蒸發(fā)出去。
那個冬天,我沒有穿過一次棉衣,不是天氣不冷,每天不停地干活,出力出汗就感覺不到冷,晚上洗澡了就上床。記得窯打好的第二天要裝窯,那晚睡一覺醒來,也不知到了什么時候,看見外面亮著,有月光,就起床到對面山上挑柴,挑了三十多擔柴天才亮。又挑了十來擔,一個窯的柴差不多挑齊了家里才喊吃早飯。陳師傅三人和我父親幫忙,一上午就把窯裝好了。下午起火,磚干柴干火旺勁足,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窯就燒好了。第二天上午挑窯田水,下午挑窯柴,就這樣不到十天燒了三個窯。
雖然勞累卻不覺得苦,除了年輕身體扛得住,關(guān)鍵是感覺生活有奔頭。兒子一歲多了,天天追著我,我空擔去挑磚就把他抱在手里,挑磚回來就一頭少放一點磚讓他坐在里面,就這樣把兒子抱去挑來。
那些年破除迷信搞得很厲害,但人們心中依然有一些莫名的禁忌。吃飯時,陳師傅有意無意講,女人不準到窯頂上去,也不能將身子對著窯門站。燒窯的時候,我愛人帶兒子給我送飯,她自覺地站在窯的側(cè)邊,不到窯門口去。我不太信。十幾年后,我的子女漸漸長大了,房子又不夠住了,再次扮磚燒窯蓋房時,就完全不理會這一套了,我愛人不僅要幫忙裝窯出窯,我吃飯時還讓她送上幾把火。
只是有一件事回想起來至今讓人疑惑。燒第二個窯時,磚同樣干,柴同樣干,同樣是我自己燒,但燒了一天一夜,燒掉了一個半窯的柴火,仍然沒有燒下腳。沒有辦法就去請教陳師傅。陳師傅要我去搞一個雞蛋,篩點酒、沏杯茶,拿幾片黃紙和三炷香來。我照辦。他安排我到窯頂上去撿卦。他站在火門口念念有詞,插上香,跪下拜了三拜,然后脫掉腳上的馬鞍靴,往窯頂上一摔,說“圣告”,要我去驗證。圣告就是一只仰一只伏。我說是圣告,把鞋扔給他。他念了幾句又往上一扔,說“陽告”。陽告就是兩只鞋全仰著。我驗證后又扔給了他。他繼續(xù)如前,又扔上兩只鞋,說“陰告”。陰告就是兩只鞋全伏著。我驗證了,把鞋扔下去。他接著大聲說:圣告,圣上保佑;陽告,洋洋得意;陰告,陰中積福。然后又跪下拜了三拜,叫我下來再攪窯放火。說來也怪,十幾分鐘,便燒下了腳。
有人說我打窯的地方有問題。山里往往根據(jù)山形地貌取名,比如七寸咀,就是地形像一條蛇,我打窯的位置正好是蛇的七寸位。說窯打在蛇的七寸上,它逃不了就作怪。再者,旁邊不遠處是水井,按民間說法,井水也有菩薩管,叫泉水菩薩。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短短幾個春秋,所知所見何其有限,也只能胡亂猜測了。
每天要出集體工,沒有重要事情不能請假,我就利用早晚時間打地基。打地基的地方是個斜坡,斜坡最高處比地基高出三米多,這么多土要挖平,全靠鋤挖肩挑,有如愚公移山。那時候蓋房子花錢不多,用工都是親朋戚友和隊里人助工,吃的是一點紅薯絲飯,一點蘿卜白菜,炒菜的油都難以保證。糧食除當初岳母給我三十斤米,岳父后來又用紅薯絲換了兩擔谷給我。至于煙,當時流傳一首順口溜:縣里干部抽白金龍,公社干部抽喜相逢,社員抽喇叭筒。做屋的時候,我把自己種的煙曬干后切成絲,用一個大竹筒盛著,再裁一點舊書紙擱在旁邊,誰想抽煙就自己卷“喇叭筒”。
房子砌起來了,門是我自己做的。沒有瓦,蓋的冬茅,靠屋檐蓋的一排杉樹皮。臘月中旬,我和愛人帶著兒子搬到新屋。我兩個弟弟也有十六七歲了,正急需住房,我就把之前住的那間房還給了父母。
三
眼看春節(jié)來臨,家中糧食吃空了,錢更是分文無存,幸好那幾年供銷社收購檵木條,我和妻子決定去砍幾天。小年那天,生產(chǎn)隊開始放春節(jié)假,當時妻子已身懷六甲,一大早還是同我出了門。附近山上的檵木基本上砍光了,我們就到屋場靠背山的反背坡去砍。半上午,妻子先背一捆檵木回家做飯,我挑一擔直接送到離家五里路的供銷社再回來吃中飯。下午又去砍,傍晚妻子背一捆回家后做晚飯,我挑一擔送回家后,再去山上挑一擔回來。吃過晚飯,我和妻子再把檵木條送到供銷社。那時收購員也很好,拿著手電筒,端著煤油燈,幫我們過秤收購。這樣五天下來結(jié)賬,共五千五百多斤,每百斤一元一角錢,共掙了五十多元錢。
正月十六日長女出生了。年前我們從別人家得了十四斤肉,過年沒吃,留作孩子出生后辦“三朝酒”待客。可是家中僅有兩斤酒,還是用春節(jié)按戶分的酒指標買的。三朝酒那天來了幾桌客人,最少要上七斤酒,當時無處借,有錢也無處買。正一籌莫展時,一個通城賣酒的挑著一擔米酒來了,五角錢一斤,我們購了二十斤。大家都說,這孩子今后會不錯的,一出生就住新房,只愁冇酒喝,酒就送上門來了。
房子做起來了,又喜添嬌兒,我打心眼里高興。只是今日回想起來,妻子在臨盆足月之際,還與我上山砍檵木棒,確實感到內(nèi)疚。這房子后來賣給了弟弟家,弟弟把房子拆了在原址上蓋起了樓房。每一塊曾經(jīng)無數(shù)次經(jīng)過我雙手的磚頭,拆屋時碎的碎了,沒碎的堆在屋旁邊,慢慢零落稀少不見了。過往都成云煙,漸漸無跡可尋,但是那幾間簡陋的房子不僅承載過我對生活的向往,更是承載過我一家老小無數(shù)的歡聲笑語,至今讓我追懷不已。
責任編輯:易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