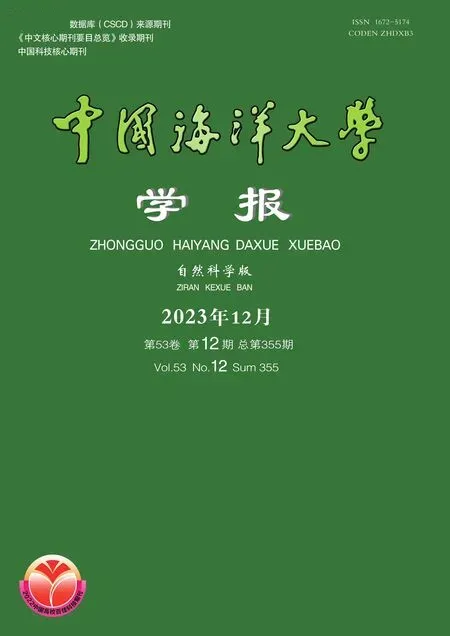2021年夏季珠江口顆粒有機碳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包孝涵, 畢 蓉??, 朋 鵬, 李 超, 張海龍, 金貴娥, 趙美訓,
(1. 中國海洋大學 海洋化學理論與工程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山東 青島 266100; 2. 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珠海), 廣東 珠海 519000)
顆粒有機碳(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POC)是有機碳在海水中存在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重要變量之一[1-3],對評估全球碳循環CO2通量至關重要[4]。河口連接著陸地、河流、大洋和大氣,是全球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最活躍的區域[2]。河口碳循環是全球碳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3],全球河流通過河口每年向海洋輸送約200 Tg POC,占有機碳總量的45%[5]。河口POC組成較為復雜,包括陸地植物碎屑和土壤、淡水浮游植物生產和海洋生物原位生產[3]。同時,河口POC濃度的空間分布受到物理(河流淡水輸入、表層沉積物再懸浮等)、化學(氧化降解、絮凝沉降、礦化等)以及生物(浮游生物合成、微生物降解等)因素的強烈影響[6],不同年份、不同海域以及不同水層間POC濃度存在差異[7-12]。因此,厘清河口區域POC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是深入理解河口碳循環過程的關鍵。
珠江按徑流量是中國第二大河流,世界第十三大河,主要由東江、西江和北江三大支流組成,年徑流量3.3×1011m3,年輸沙量8.5×107t[13],4—9月為豐水期,期間徑流量占年徑流量的80%,10月至次年3月為枯水期[14]。珠江口是位于中國南部海岸的典型亞熱帶河口,主要由伶仃洋(Lingdingyang)、黃茅海(Huangmaohai)和磨刀門(Modaomen)三個次級河口組成。珠江三角洲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是華南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帶,頻繁的人類活動對這一區域的生態環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3]。珠江口是珠江向南海北部輸送陸源有機碳的主要區域[15],珠江口每年接收來自珠江輸送的102 Mt 陸地沉積物和0.54 Mt POC,總有機碳(TOC)入海通量約為9.2×105t·a-1,約占全球河流總通量的0.1%~0.2%[16]。在過去三十年間,珠江流域水庫和大壩的建立截留了大量泥沙和懸浮顆粒物,導致珠江輸送的POC通量減少[17]。同時,由于工農業活動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大量營養鹽輸入珠江口[18],加重了珠江口水體富營養化程度并影響了生物過程[19]。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珠江口POC的來源與分布更為復雜。
前人對珠江口POC空間分布及其影響因素已開展了一定的研究。陳金斯等[7]、陳紹勇等[20]和蔡艷雅等[21]探討了珠江口表層POC濃度的分布特征及季節變化。劉慶霞等[8]報道了2010年夏季珠江口POC空間分布特征,指出伶仃洋POC主要來自陸源輸入,南部海域POC主要來自海洋自生。郭威等[9]報道了伶仃洋表層水體POC分布的季節變化,并結合葉綠素a(Chlorophylla, Chla)、C/N摩爾比和溶解氧等參數,指出伶仃洋表層水體POC主要受到水體自生浮游植物有機碳輸入的影響。Ye等[22]根據伶仃洋海域四個季節的表層水體POC數據,結合δ13C和δ15N三端元混合模型得出濕季POC主要來自河流淡水輸入,而枯季則主要來自海洋浮游植物。綜上,前人主要對伶仃洋海域表層水體POC來源及分布特征進行了研究,對珠江口大范圍區域,尤其是不同水層POC的空間分布及其影響因素認識不足,限制了對珠江口大范圍區域碳循環過程和機制的深入解析。
本文依據2021年7月(珠江豐水期)在珠江口獲取的POC數據及水文調查資料,系統分析該區域POC濃度的水平和垂直分布特征,并與多種環境和生物因素進行相關性分析,主要對POC濃度與鹽度、懸浮顆粒物(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SPM)和浮游植物類脂生物標志物總濃度(Sum of phytoplankton biomarkers concentrations, ΣPB)的相關性進行討論。研究結果為進一步厘清珠江口夏季POC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豐富珠江口有機碳研究資料、探討河口區域碳循環提供基礎。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區域與樣品采集
2021年7月12—23日搭載“海科68調查船”在珠江口海域進行樣品采集。本航次設置28個采樣站位,根據水深劃分了表層(水深約1~2 m)、葉綠素最大層(通過CTD測得水深范圍約為4~22 m)和底層(距離海底約1~3 m),共獲得74個POC樣本,其中表層28個,葉綠素最大層20個,底層26個。根據三個重要口門劃分了A、B和C三個斷面:A斷面位于黃茅海至珠江口外側,B斷面位于磨刀門至珠江口外側,C斷面位于伶仃洋至珠江口外側(見圖1),這三個斷面分別代表本研究區域的西部、中部和東部海域。

(藍色圓點為采樣站位,黑色虛線連接三個斷面。The blue dots represent sampling stations, and the black dotted lines denote the three sections.)
使用經過校準的CTD(Seabird 25 plus,海鳥電子公司,美國)測量海水溫度、鹽度、溶解氧和濁度等參數。使用CTD采水瓶(Niskin bottles)采集不同水層的海水,通過Whatman GF/F膜(直徑:25 mm;預先450 ℃灼燒6 h)過濾,濾膜儲存于-20 ℃,用于分析POC和SPM。使用深水泵采集不同水層海水,通過Whatman GF/F膜(直徑:150 mm;預先450 ℃灼燒6 h)過濾,濾膜儲存于-20 ℃,用于分析類脂生物標志物。
1.2 樣品分析
SPM樣品經過冷凍干燥72 h后置于干燥器中,待恒重后稱重,根據質量差與過濾海水的體積計算SPM濃度(mg/L)。將6 mol /L HCl滴加到稱重后的濾膜去除無機碳,反應2 h,然后在55 ℃烘箱中烘干,使用元素分析儀(Thermo Flash EA 2000,美國)進行分析,得出POC的質量百分含量(POC%)。POC的測定利用空白樣、標準樣進行質量控制,標準樣的標準偏差為0.05% (wt.%) (n= 11)。SPM濃度乘以POC%得到POC濃度(mg/L)。
類脂生物標志物根據Zhao等[23]的方法進行提取和測定。將GF/F濾膜凍干,加入40 μL C19烷醇內標,加入二氯甲烷:甲醇(3∶1, vol/vol)混合溶液,進行超聲萃取8次,再加入20 mL 6% KOH的甲醇溶液進行堿水解12 h,然后使用正己烷溶液萃取得到提取物。用硅膠色譜法分離提取物中極性組分,并用22 mL二氯甲烷:甲醇(95∶5, vol/vol)溶液淋洗得到目標組分,然后在柔和的N2下干燥。洗脫后轉移至2 mL細胞瓶,再在柔和的N2下干燥,分別加入40 μL二氯甲烷和N,O-雙(三甲硅烷基)三氟乙酰胺(BSTFA),70 ℃條件下進行衍生化反應1 h。在配備氫火焰離子化檢測器(FID)的Agilent 8890氣相色譜儀上分析,使用HP-1毛細管柱(50 m×0.32 mm內徑×0.17 μm膜厚度)。通過對比目標峰面積與內標峰面積,對類脂生物標志物濃度進行量化。ΣPB為類脂生物標志物菜籽甾醇、甲藻甾醇和C37長鏈烯酮總量,單位為ng/L;菜籽甾醇、甲藻甾醇和C37長鏈烯酮各自濃度引自Bao等(未發表數據)。
1.3 數據統計分析
采用ODV 5.3.0(Ocean Data View)軟件繪制水文參數(溫度、鹽度和濁度)、SPM、POC濃度、POC%和ΣPB平面與垂直分布圖。使用IBM SPSS 26軟件進行Spearman秩相關分析(雙尾顯著性檢驗),定量評估POC濃度與水文參數(溫度、鹽度、溶解氧和濁度)、營養鹽(DIN、DIP和Si)濃度(張勁等,未發表數據)、SPM濃度和ΣPB之間的關系,顯著性水平設置為p<0.05。使用Origin 2021軟件繪制鹽度與POC濃度、SPM與POC%的相關圖。
2 結果
2.1 溫度、鹽度和濁度空間分布
海水溫度在整個調查區域內變化范圍為21.9~31.8 ℃,均值(平均值±SD)為(28.2±2.9) ℃(見表1),平均海水溫度隨深度的增加而降低,表層平均海水溫度比底層高4.5 ℃。水平分布上,表層海水溫度在西部海域有高值,在伶仃洋海域有低值(見圖2(a));葉綠素最大層海水溫度在西部海域有高值,在東部海域有低值(見圖2(d));底層海水溫度近岸有高值,隨著離岸距離的增加海水溫度逐漸減小(見圖2(g))。垂直分布上,三個斷面剖面圖均顯示海水溫度存在分層現象,隨深度的增加而降低(見圖3(a)—3(c))。

表1 2021年夏季珠江口水文參數(溫度、鹽度、濁度和溶解氧)、SPM、POC濃度、POC%和ΣPB范圍及平均值

((a)表層溫度;(b)表層鹽度;(c)表層濁度;(d)葉綠素最大層溫度;(e)葉綠素最大層鹽度;(f)葉綠素最大層濁度;(g)底層溫度;(h)底層鹽度;(i)底層濁度。(a) Surface layer temperature; (b) Surface layer salinity; (c) Surface layer turbidity; (d) Deep chlorophyll maximum layer temperature; (e) Deep chlorophyll maximum layer salinity; (f) Deep chlorophyll maximum layer turbidity; (g) Bottom layer temperature; (h) Bottom layer salinity; (i) Bottom layer turbidity. )

((a)A斷面溫度;(b)B斷面溫度;(c)C斷面溫度;(d)A斷面濁度;(e)B斷面濁度;(f)C斷面濁度;(g)A斷面POC濃度;(h)B斷面POC濃度;(i)C斷面POC濃度;(j)A斷面鹽度;(k)B斷面鹽度;(l)C斷面鹽度;(m)A斷面SPM;(n)B斷面SPM;(o)C斷面SPM;(p)A斷面ΣPB;(q)B斷面ΣPB;(r)C斷面ΣPB。(a) Section A temperature; (b) Section B temperature; (c) Section C temperature; (d) Section A turbidity; (e) Section B turbidity; (f) Section C turbidity; (g) POC concentrations of section A; (h) POC concentrations of section B; (i) POC concentrations of section C; (j) Section A salinity; (k) Section B salinity; (l) Section C salinity; (m) SPM of section A; (n) SPM of section B; (o) SPM of section C; (p) ΣPB of section A; (q) ΣPB of section B; (r) ΣPB of section C.)
鹽度的變化范圍為7.8~34.6,均值為(28.2±7.9),葉綠素最大層和底層平均鹽度相近,分別比表層高10.0和8.8(見表1)。表層鹽度在南部及東南部海域有高值,隨著離岸距離的增加不斷增大(見圖2(b));葉綠素最大層鹽度在磨刀門近岸海域較低(見圖2(e));而底層鹽度伶仃洋海域較低(見圖2(h))。垂直分布上,底層平均鹽度比表層平均鹽度高10.3(見表1),三個斷面剖面圖均顯示鹽度存在著分層現象,隨深度的增加而升高(見圖3(j)—3(l))。
濁度的變化范圍為0.1~24.5 mg/L,均值為(3.1±4.7) mg/L,底層濁度平均值最高,分別比表層和葉綠素最大層高2.5和4.3 mg/L(見表1)。水平分布上,表層濁度高值區集中在近岸海域(見圖2(c));葉綠素最大層濁度整體偏低,分布較為均勻(見圖2(f));底層濁度與表層分布相似,高值區集中在近岸海域(見圖2(i))。垂直分布上,A斷面濁度在底層明顯高于表層(見圖3(d)),B和C斷面近岸區域濁度較高,河口外部濁度較低(見圖3(e)—3(f))。濁度的上述分布特征受到珠江河水輸入以及河口較強水動力的影響,即:近岸海域濁度總體高于離岸區域,底層濁度高于表層濁度。
2.2 SPM和POC濃度空間分布
SPM濃度的變化范圍為6.0~63.3 mg/L,均值為(18.7±10.2) mg/L,平均值SPM濃度底層比表層高13.0 mg/L(見表1)。水平分布上,SPM濃度在表層呈現出隨著離岸距離的增加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見圖4(a)),在葉綠素最大層呈現出近岸濃度高,外海濃度低的分布趨勢(見圖4(e)),在底層高值區集中在研究海域的中部和西北部(見圖4(i))。垂直分布上,A斷面SPM濃度隨著深度增加有增加的趨勢(見圖3(m)),B斷面表層SPM濃度較低,近岸SPM濃度相對較高(見圖3(n)),C斷面SPM在近岸底層有高值區(見圖3(o))。

((a)表層SPM;(b)表層POC;(c)表層POC%;(d)表層ΣPB;(e)葉綠素最大層SPM;(f)葉綠素最大層POC濃度;(g)葉綠素最大層POC%;(h)葉綠素最大層ΣPB;(i)底層SPM;(j)底層POC濃度;(k)底層POC%;(l)底層ΣPB。(a) SPM in the surface layer; (b) POC concentrations in the surface layer; (c) POC% in the surface layer; (d) ΣPB in the surface layer; (e) SPM at the deep chlorophyll maximum layer; (f) POC concentrations at the deep chlorophyll maximum layer; (g) POC% at the deep chlorophyll maximum layer; (h) ΣPB at deep chlorophyll maximum layer; (i) SPM at the bottom layer; (j) POC concentrations at the bottom layer ; (k) POC% at the bottom layer; (l) ΣPB at the bottom layer. )
POC濃度的變化范圍為0.05~0.85 mg/L,均值為(0.29±0.19) mg/L,平均濃度表層最高,比葉綠素最大層和底層高0.07~0.09 mg/L(見表1)。水平分布上,表層POC濃度高值區集中在西北部和香港南部海域,最高值站位是T53和T39站位,位于磨刀門東、西兩側海域(見圖4(b)),葉綠素最大層POC濃度高值區在近岸區域(見圖4(f)),而底層高值區集中在西北部近岸海域(見圖4(j))。垂直分布上,POC濃度在A和B斷面近岸海域分布較為均勻,隨著離岸距離的增加出現分層現象(見圖3(g)—3(h)),C斷面在香港以北海域垂向分布較為均勻,到了香港南部海域水體POC濃度增大,再向外海POC濃度減小且底層POC濃度增大(見圖3(i))。
2.3 ΣPB濃度空間分布
ΣPB濃度的變化范圍71.8~545.6 ng/L,均值(219.8±121.6) ng/L,表層與葉綠素最大層濃度相似且大于底層,表層平均值濃度比底層高47.2 ng/L(見表1)。水平分布上,ΣPB高值區與POC濃度高值區分布相似,表層在磨刀門及香港南部海域(見圖4(d)),葉綠素最大層在磨刀門鄰近海域及香港以南海域(見圖4(h)),底層在西北部近岸海域(見圖4(l))。垂直分布上,ΣPB 在A斷面近岸區域底層較高,隨著離岸距離的增加轉變為表層較高(見圖3(p)),在B斷面隨著深度的增加濃度逐漸降低(見圖3(q)),在C斷面整體上ΣPB濃度垂直分布較為均勻(見圖3(r))。
2.4 相關性分析
總體上,在某些海域和水層,溫度、濁度、溶解氧、營養鹽濃度、SPM以及ΣPB等參數與POC濃度具有顯著正相關,而鹽度與POC濃度具有顯著負相關(見表2)。具體而言,鹽度與POC濃度具有極顯著負相關(p<0.001),其中在表層(p=0.001)和葉綠素最大層(p=0.005)和B斷面(p=0.002)具有極顯著負相關,在底層具有顯著負相關(p=0.013)。SPM與POC濃度在底層具有極顯著正相關(p=0.004),在伶仃洋具有顯著正相關(p=0.011)。ΣPB與POC濃度具有極顯著正相關(p<0.001),其中在表層(p=0.001)和C斷面(p=0.008)具有極顯著正相關,在底層(p=0.046和B斷面(p=0.038)具有顯著正相關。

表2 POC 與多種環境與生物因子之間的斯皮爾曼相關系數
3 討論
3.1 POC的空間分布特征
河口及鄰近海域水動力環境復雜,POC濃度空間分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研究表明,2021年7月(珠江豐水期)珠江口大范圍海域POC濃度具有明顯的水平和垂直分布特征。我們將結合前人研究系統地討論珠江口POC濃度的水平和垂直分布特征。
不同年份間,夏季(5—8月)POC濃度差異較小(見表3)。本研究中POC濃度在水體中的變化范圍為0.05~0.85 mg/L,75個樣本平均值為(0.29±0.19) mg/L。在伶仃洋表層水體的變化范圍為0.17~0.64 mg/L,平均值(0.30±0.15) mg/L,這一變化范圍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見表3),例如劉慶霞等[8]和郭威等[9]對伶仃洋海域表層水體的研究,以及陳金斯等[7]和Huang等[10]在珠江口的研究發現,除了個別站位外,POC濃度范圍與本研究接近。同時,上述研究的POC平均濃度比本研究結果略高。例如,陳金斯等[7]和劉慶霞等[8]的研究區域包含了一些河流站位,這些站位位于鹽度較低的區域,河流淡水源有機碳比例較高。另外,對比不同年份數據發現,并且近十幾年POC濃度明顯降低。近幾十年來,珠江口流域輸沙量明顯減少[24],這與珠江流域大型水庫的建設有關,導致河口懸浮泥沙濃度降低[24],河流淡水源POC貢獻減少[17],不同月份間河流徑流量差異使河流淡水源POC輸入不均勻導致POC濃度差異[11, 22];另外,水體富營養化使海洋自生POC增加也會導致POC濃度的差異[19]。上述因素可能導致本研究中POC濃度與前人研究結果的差異。在其他受大河影響的河口區域,如長江口及鄰近海域[11, 25]以及黃河口[12]的研究也發現大型水庫的建設使河流輸送的懸浮泥沙量減少,導致河流淡水輸送的POC通量降低。

表3 不同研究區域和不同調查時間POC濃度的比較
水平分布上,不同區域間存在明顯差異。POC濃度高值區集中在磨刀門近岸海域和香港南部海域,低值區集中在伶仃洋及南部海域(見圖4(b), 4(f), 4(j)),POC%也有相似的分布(見圖4(c), 4(g), 4(k))。A和B斷面結果顯示,POC濃度從近岸到河口外部區域逐漸降低(見圖3(g)—3(h)),而在C斷面POC濃度呈現先增加后降低的分布趨勢,在香港南部有高值區(見圖3(i))。上述結果與前人研究一致,Li等[26]在2015年7月的研究顯示POC濃度磨刀門海域大于伶仃洋海域。劉慶霞等[8]在2010年8月的研究顯示POC濃度香港南部海域大于伶仃洋海域。本研究中,磨刀門近岸海域ΣPB濃度較高(見圖4(d), 4(h), 4(l)),表明浮游植物生物量較高,并且該區域毗鄰入海口門河流淡水源貢獻率較高[10],所以該區域POC濃度較高。香港南部海域濁度相對較低(見圖2(c), 2(f), 2(i)),光限制減弱,并且營養鹽充足[27],ΣPB濃度較高(見圖3(r), 4(d), 4(h), 4(l)),表明浮游植物生物量較高,海源自生有機碳貢獻較高[8],因此該區域POC濃度較高。伶仃洋海域鹽度較低,表明受到淡水輸入的強烈影響,在混合區域陸源輸入POC被大量降解和礦化[9],并且水體也相對渾濁(見圖2(c), 2(i)),ΣPB濃度較低(見圖3(r)),浮游植物生物量較低,海源有機碳貢獻較小,因此伶仃洋海域POC濃度較低。外海海域POC濃度較低的原因為受河流淡水輸入影響較小,營養鹽濃度較低[28],ΣPB濃度較低(見圖4(d), 4(h), 4(l)),有研究表明外海海域陸源有機碳貢獻率僅為27%[10],因此導致了該區域POC濃度較低。
垂直分布上,不同區域存在明顯差異(見圖3(g)—3(i))。A斷面POC濃度最大值出現在近岸及葉綠素最大層(見圖3(g)),B斷面POC濃度最大值出現在表層(見圖3(h)),而C斷面大部分站位垂直分布較均勻(見圖3(i))。上述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相似,例如Huang等[10]在2017年6月的研究顯示,黃茅海(本研究A斷面)近岸POC濃度較高且垂直分布均勻。劉慶霞等[8]在2010年8月在伶仃洋的研究結果與本研究C斷面相同,伶仃洋上游至香港南部海域POC濃度垂直分布較均勻,香港南部海域至南部海域底層POC濃度明顯高于其他水層。同樣,在長江口及鄰近海域的研究也發現了A和B斷面類似的POC分布,口門附近底層大于表層,隨之離岸距離的增大轉變為表層POC濃度大于底層[11]。本研究POC濃度呈現出三種不同的垂直分布格局,表明這三個斷面POC濃度垂直分布受到不同因素的調控。一方面受到河流淡水輸入的影響,上層水體受到河流沖淡水影響顯著而底層受影響較小(見圖3(a)—3(c), 3(j)—3(l)),珠江中POC濃度顯著高于珠江口[29],近岸濃度高于河口外部區域濃度。三個斷面分別受到不同口門陸源來源POC的影響(見圖1),A和B斷面對應的口門POC輸出通量高于C斷面[16],通量越高表示受到河流淡水輸入POC影響越顯著,使A和B斷面上層水體POC濃度要高于底層水體。另一方面受到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影響,B和C斷面ΣPB濃度與POC濃度的垂直分布趨勢相似(見圖3(h), 3(i), 3(q), 3(r)),并且二者之間顯著性正相關(見表2),表明浮游植物生物量對于POC垂直分布具有重要貢獻。此外表層沉積物再懸浮也具有一定影響,A斷面底層和葉綠素最大層SPM濃度較高(見圖3(m)),底層濁度較高(見圖2(i)),表示還受到了表層沉積物再懸浮作用的影響,使得葉綠素最大層POC濃度較高。
3.2 POC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
本文系統分析了多種因素與POC濃度的相關性。總體而言,鹽度與POC濃度呈負相關,而其他因素與POC濃度呈正相關(見表2),上述相關性在不同水層和海域存在差異。前人研究表明,珠江口水體的鹽度、SPM和浮游植物生物量等是影響POC濃度空間分布的重要因素[7-10, 21, 22, 30]。本文使用ΣPB表征浮游植物類群(包括硅藻、甲藻和定鞭藻),具有來源明確、化學穩定性較好和對環境變化敏感等優點,已被廣泛應用于示蹤浮游植物生物量[31-33]。本研究將主要圍繞鹽度、SPM和ΣPB與POC濃度的相關性進行詳細討論。總結影響POC空間分布的因素。
3.2.1 鹽度與POC的相關性 本研究表明,總體上鹽度與POC濃度具有極顯著負相關,在表層和葉綠素最大層也具有極顯著負相關,底層具有顯著負相關(見表2),而且不同鹽度梯度對POC濃度空間分布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見圖5(a))。當鹽度<15,表層POC濃度隨著鹽度增加呈上升趨勢,當鹽度在15~25之間,表層和底層POC濃度隨著鹽度增加而減小,當鹽度>25,表層和葉綠素最大層POC濃度隨著鹽度的增加而減小(見圖5(a))。本文研究結果與前人研究相似,例如,李倩等[34]在春季長江口也發現表層和底層POC濃度分別在鹽度在9和15時達到最大值,然后隨鹽度下降而迅速下降。郭威等[9]在伶仃洋海域、蔡艷雅等[21]在磨刀門海域的研究顯示,表層POC濃度與鹽度也呈顯著負相關。上述鹽度梯度的變化對POC濃度的影響主要是由不同鹽度區間POC生物地球化學行為不同造成的,包括絮凝沉降、海水稀釋作用[35],以及陸源輸入和表層沉積物再懸浮等過程也產生一定影響[36]。珠江沖淡水攜帶大量泥沙和懸浮顆粒物與海洋高鹽水混合,顆粒間會因為電化學作用而相互吸引絮凝成團[34],POC濃度隨著絮凝沉降而減少,鹽度的增加表示海水對陸源POC稀釋作用增強。當鹽度<15,此時為初始咸淡水混合階段,站位靠近口門且受陸源輸入影響較大,磨刀門和黃矛海陸源POC輸出通量高于虎門[16],這兩個口門鄰近站位鹽度和POC濃度相對伶仃洋較高(見圖3(g)—3(h),圖5(a)),此時受到陸源輸入占主導。當鹽度在15~25之間,咸淡水混合程度增強,水動力更為強勁,絮凝沉降作用較強,懸浮顆粒物在水層中做懸浮沉降、再懸浮再沉降的周期性運動[37],POC在底層有較長的停留時間,因為沉積物再懸浮也是SPM的重要來源[38],絮凝沉降和表層沉積物再懸浮占主導作用。當鹽度>25,海水對河流淡水源POC稀釋作用增強,尤其在表層和葉綠素最大層(見圖2(b), 2(e)),POC隨著鹽度的增加而降低,此時海水稀釋作用占主導因素。因此,表層和葉綠素最大層受絮凝沉降和海水稀釋作用影響較大,所以鹽度與POC濃度具有極顯著負相關。

((a) 鹽度與POC濃度的相關圖; (b) SPM與POC%的相關圖。(a) Correlations between salinity and POC concentrations; (b) Correlations between SPM and POC%. )
3.2.2 SPM與POC的相關性 SPM與POC濃度在底層和伶仃洋海域具有顯著正相關,而在其他水層或區域都沒有顯著相關性(見表2)。前人也有相似的研究結果:在黃河口和長江口也發現底層POC濃度與SPM正相關性系數要顯著高于其他水層[12, 39]。劉慶霞等[8]研究發現,在伶仃洋海域POC濃度與SPM濃度具有顯著正相關,但南部海域相關性較差。當SPM濃度較大時,其與POC濃度的相關性較好[34, 39, 40]。同樣,本研究底層SPM濃度較高(見表1),且在伶仃洋海域也具有較高濃度,在底層和伶仃洋海域我們也觀察到SPM與POC濃度顯著正相關。另一方面,SPM的來源可以用POC%來指示,POC%相似反映來源一致,反之則有多個來源[41]。本研究中,底層POC%變化范圍最小(0.49%~2.53%,平均值(1.15±0.55)%),而表層變化范圍最大(0.72~11.06%,平均值(3.16±2.34)%)(見表1,圖5b),說明不同水層SPM來源有差別。本文底層水POC%與商博文等[42]研究表層沉積物TOC%值(范圍:0.41~1.54%;平均值:(0.87±0.25)%)相近,伶仃洋海域以及研究區域整體底層水濁度較高(見圖2i),都表明了表層沉積物再懸浮的重要影響,因此底層水SPM濃度較高、POC%變化范圍較小且含量較低。上層水體較高的POC%表明受到了海洋自生增加的影響[43],此外陸源輸入有機質在上層水體中被大量絮凝沉降[34]和礦物質稀釋[9],導致SPM濃度較低。總之,底層水和伶仃洋海域受表層沉積物再懸浮的影響SPM濃度較高,SPM濃度和來源影響著POC的空間分布。
3.2.3 ΣPB與POC的相關性 ΣPB與POC濃度在整個研究區域水平分布模式相似(見圖4(b),4(d)),且在整個研究區域水體及表層水中呈極顯著正相關,在底層水中顯著正相關,但在葉綠素最大層卻無顯著相關(見表2)。珠江通過八大口門源源不斷為珠江口及鄰近海域輸送大量營養鹽,造成水體富營養化[44],使浮游植物初級生產力水平較高[19],對POC的貢獻會隨之增加[10]。之前的研究表明,在珠江口海域POC中河流淡水源有機質貢獻率是大于海源自生有機質的[7, 20],而最近的研究卻表明,伶仃洋海域海源自生有機質貢獻率超過了陸源輸入[8, 30]。硅藻和甲藻是珠江口海域重要的浮游植物類群[26,45-46],本文使用的菜籽甾醇、甲藻甾醇和C37長鏈烯酮可分別指示硅藻、甲藻和定鞭藻。整個研究海域總體上,三種類脂生物標志物總濃度ΣPB與POC濃度呈顯著正相關,表明類脂生物標志物可以指示POC濃度的空間分布,浮游植物生物量是影響POC濃度的重要因素。
在葉綠素最大層ΣPB與POC濃度缺乏顯著相關,這可以歸結于葉綠素最大層和生物量最大層形成的機制不同而深度通常不同(葉綠素最大層形成機制復雜,主要由光適應決定;生物量最大層出現在浮游植物生長速率與損失(如呼吸和捕食)和下沉速度的差異相平衡的水層)[33, 47, 48]。后續的研究中我們將深化珠江口類脂生物標志物對浮游植物生物量和群落結構指示作用的探討。
伶仃洋海域ΣPB濃度相對較低(見圖4(d), 4(l)),可能由于濁度較高限制了浮游植物生長[49],海源自生有機質對POC貢獻較低[8],所以ΣPB與POC濃度無顯著相關。如前文所述,香港南部海域濁度降低(見圖2(c), 2(i)),光限制減弱并且營養鹽濃度相對充足[27],ΣPB濃度較高(見圖3(r)),浮游植物生物量較高[48-49],海源自生有機碳對POC貢獻較高[8]。此外C斷面POC濃度和ΣPB垂直分布模式大體是相似的(見圖3(i), 3(r)),POC濃度與ΣPB極顯著正相關(見表2),所以ΣPB影響著C斷面POC濃度的垂直分布。A斷面底層和葉綠素最大層SPM濃度較高,表示了再懸浮作用的影響,使ΣPB對POC的貢獻率降低,所以A斷面ΣPB與POC無顯著相關,ΣPB對POC濃度垂直分布相對影響較小。B斷面ΣPB與POC濃度的垂直分布模式大體相似,ΣPB與POC濃度都相對較高(見圖3(h), 3(q)),相關性結果也表明ΣPB與POC顯著正相關(見表2),所以ΣPB在B斷面影響POC垂直分布。總之,ΣPB作為示蹤浮游植物生物量的生物標志物與POC有顯著正相關,在不同水層和海域存在相關性差異,表明了ΣPB對POC空間分布具有重要影響。
3.2.4 其他因素與POC的相關性 除了上文討論的鹽度、SPM和ΣPB對POC濃度空間分布的影響外,其它因素也存在潛在的影響,比如:溫度、濁度和營養鹽等(見表2)。溫度和營養鹽與浮游植物的生物量密切相關,溫度與POC濃度顯著正相關,可能由于溫度升高浮游植物生長加快,從而導致POC總量增加[49]。溶解氧在表層和葉綠素最大層與POC濃度顯著正相關,在這兩個水層溶解氧濃度升高,可能表示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增強,POC生產量增加。濁度與POC濃度具有顯著正相關,濁度較高表示水體較渾濁,可能指示了水動力的擾動引起了表層沉積物再懸浮現象。浮游植物初級生產和群落演替與營養鹽濃度密不可分,因此營養鹽濃度影響POC空間分布。
在復雜的河口環境中,影響POC空間分布的各種因素相互交織。本文初步分析了多種環境和生物因素對POC空間分布的影響,后續研究還需進一步加強各種因素的定量區分及其機制研究,尤其是可以結合多種類脂生物標志物及碳同位素技術對河口碳循環過程及其機制進行深入探究。
4 結論
本文通過分析2021年7月(珠江豐水期)珠江口POC空間分布特征,探究了鹽度、SPM和ΣPB等因素對POC空間分布的影響。主要有以下結論:
(1) 2021年夏季珠江口POC濃度范圍為0.05~0.85 mg/L,均值(0.29±0.19) mg/L,總體呈現近岸濃度高、河口外部區域濃度低的分布趨勢,平均POC濃度總體在表層最高,隨著深度的增加先減小再增加。對比不同年份數據,POC濃度略低于前人在珠江口海域豐水期的研究結果,并且近十幾年來POC濃度明顯降低。
(2) 相關性分析表明鹽度、懸浮顆粒物和浮游植物生物量影響著POC空間分布。高鹽度引起懸浮物絮凝沉降、海水稀釋使POC濃度隨鹽度的增加而降低。SPM濃度和來源控制著POC的濃度,表層POC受到新鮮有機質的影響較大,而底層POC濃度則受表層沉積物再懸浮作用影響明顯。ΣPB與POC濃度具有極顯著正相關以及空間分布相似,表明了浮游植物生物量是影響本研究區域POC空間分布的主要因素。類脂生物標志物作為示蹤浮游植物的指標在河口區域中有巨大的應用潛力,未來在珠江口及其它河口需要結合多種類脂生物標志物參數和同位素技術進行深入研究。
致謝:感謝“海科68調查船”全體人員在航次期間的幫助,感謝中國海洋大學李莉和丁楊對測試樣品提供的幫助,感謝中山大學吳加學和林姚坤提供的CTD數據,感謝中國海洋大學張勁、劉茜和李芳茹提供的營養鹽數據,感謝中山大學劉雙圓提供的樣品采集幫助,感謝四川大學候鵬飛對數據處理的幫助,作者對以上人員表示誠摯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