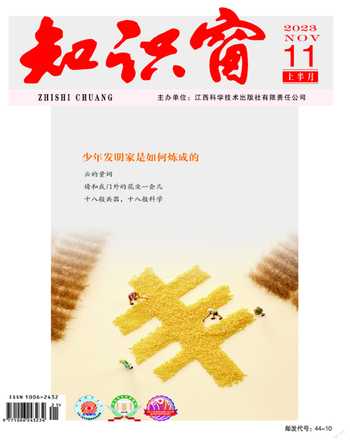格物致知
孫開元
第一次看到《大學(xué)》里的“格物致知”時(shí),我覺得“致知”容易理解一些,就是獲得一定的智慧,但對(duì)“格物”一詞感到茫然,不知是何意。
探究了很久,我想到了擺放物品的櫥架,里面有好些格子。在櫥架上擺東西是有講究的,比如把好書等一些珍貴東西放在最上面的格子,把茶壺、茶杯等常用的東西放在中間的格子,把一些不重要的雜物放在下面的格子,于是我想:“格物”也許就是要分清生活中的事情哪些好、哪些不好。
后來,我看了王陽明的《傳習(xí)錄》,才明白古人認(rèn)為,“格”有格除之意,“格物”就是格除心中的物欲。這時(shí),我對(duì)“格物”一詞有了更深的認(rèn)識(shí)。
如今的世界令人眼花繚亂,最容易擺放錯(cuò)位置的,一是利,二是情。錢是人生活的物質(zhì)基礎(chǔ),人想過好日子沒錯(cuò),但是如果把金錢的位置擺放過高,因之廢寢忘食而傷身,甚至見利忘義,那就錯(cuò)了。在網(wǎng)絡(luò)上時(shí)常看到這樣的新聞:有人開網(wǎng)店,日夜盯著電腦,廢寢忘食,竟因此得了重病,甚至因此殞命,令人惋惜。以財(cái)發(fā)身者智,以身發(fā)財(cái)者愚。
世人都有七情六欲,無可厚非,然而如果將欲望看得太重,成了欲望的奴隸,那就危險(xiǎn)了,此所謂“人心惟危”。
據(jù)說酒是夏禹時(shí)期的造酒官儀狄發(fā)明的,大禹治水有功而得到皇位,但因國(guó)事勞煩,身體漸衰。禹的女兒看著心疼,問儀狄是否有良策。儀狄獻(xiàn)上美酒,大禹喝了香醇的美酒后,精神百倍,體力恢復(fù),后來大臣們也都愛上了杯中酒。一天,大禹因飲酒耽誤了上朝,于是對(duì)眾人說:“飲酒使我荒廢朝政,后代一定會(huì)有因酒亡國(guó)的。”從此下了禁酒令。
在現(xiàn)代人看來,大禹禁酒似乎有些苛刻,但他在欲望面前知止,這一點(diǎn)便值得現(xiàn)代人學(xué)習(xí)。
東晉時(shí),重臣郗鑒和丞相王導(dǎo)是好友。郗鑒有個(gè)乖巧的女兒,才貌雙全。某年,郗鑒想在王家中為女兒選一個(gè)女婿,于是派門客去王家選婿。王家的幾個(gè)公子得知,皆衣冠齊楚,期盼好事降臨自己頭上。王羲之是王導(dǎo)的侄子,他剛剛在外面觀賞了東漢大書法家鐘繇的字碑,回到家躺在東邊的床上,一手拿著大餅,另一只手在空中比畫著寫字,全然沒把太傅選婿的事放在眼里。郗鑒得知,高興地說:“這正是我要找的佳婿啊!”這就是有名的“東床快婿”的故事。王羲之沒有把愛情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卻仍然得到了美好的愛情。
何為致知?知者,智也,并非花哨的奇技淫巧,也非追求名利的明招暗術(shù)。相反,孟子說:“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陽明講致知就是“致良知”,而如欲見到良知,需要下一番大功夫。
格物致知是修身之基,那么這物怎樣格呢,什么放在上面,什么放在下面,總要有個(gè)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或許可以這樣說:為公放在上面,為私放在下面;高雅放在上面,低俗放在下面;理性放在上面,情欲放在下面。如此,離“致知”不遠(yuǎn)矣。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然而如果人的心里有一個(gè)櫥架,分為上、中、下三格,你既不必將其擺在最低處,又不能將其擺在最高處,擺在中間的格子上就好。這樣,你拿不起時(shí)還能放得下,拿起來時(shí)也會(huì)輕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