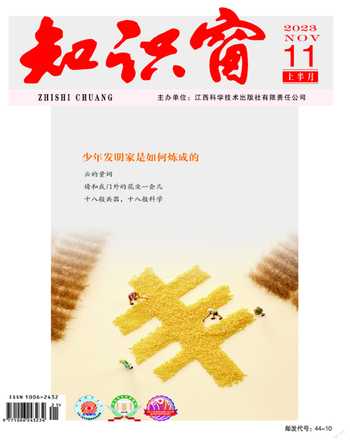青春里因詩詞長出的麥穗
徐寧遙
秋日的午后,我安靜地聽著老師講解古代文學。陽光透過窗格一點點照射下來,夾雜著涼意的微風四起,枝丫上的鳥雀抖動著羽翼,紛落的秋葉在半空中旋轉,像一場盛大煙火表演的落幕。當講到曹丕的《典論·論文》中的“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時,老師解釋道:“或許年壽有盡,榮樂隨心,它們都是有期限的,而文章所傳遞的情感和要義是無盡的。”這席話似一束光線穿透樹枝,載著綿軟的白云,在蒙上奶黃色濾鏡的記憶里游移。恍然之間,我又回到了那個流金鑠石的夏天。
少時,我常為記誦不清課本里的詩篇而苦惱。背《蜀道難》時,我剛背到“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下句的“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就好似天空中盤旋的花蝴蝶,一眨眼的工夫,就躲進了懸窗上放置的硯臺中。語文老師把我留在辦公室里背誦,我的腦海里閃過萬千詩章,“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咿呀學語時,我總聽父母講述嫦娥奔月的故事,中秋前夕,嫦娥在月宮里尋找鏡中萬花筒般迷離的夢;“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是叩開那扇古銅色的門,拭去歷史的塵埃,迎面而至一個素雅美麗、裊娜多姿的女子。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笛弄晚風三四聲,仿佛穿越時間的脈絡,定格成天水碧的永恒,郵寄著一封封寫在過去、駛向未來的信箋。此刻,我的思索像寂靜夜晚里忽明忽暗的星,“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是怎樣的好景致,云銷雨霽,綠蔭垂檐,又是少女的閑夏。我開始試圖尋找那些沉默的記憶,將素色紙卷里流轉的溫情,復刻成永恒的段落。
這般光景像編織的碎片,一針一線縫縫補補般,才能被勉強堆砌進“儲藏室”。為了記誦得更快,我和小伙伴創設起了語境,設計文字游戲,譬如“飛花令”“下句對上句”“詩詞對話”等。不知從何時起,那些因背誦不出詩篇的哀怨,逐漸在文字深深淺淺的印跡里,撫平了褶皺。我像翻開塵封往事的故事集,書頁如蝶翼在指腹間御風起舞,杏花疏影,在與詩人橫跨時空的浪漫對白里,如癡如醉。那場夏天的雨落在少女的心尖,深藍色的天空寄托著比云霞還斑斕的夢。
我從含糊記誦經典,到深深為之動容的過程里,慢慢長大了。直到讀大學后的一個隆冬,我同友人前往揚州,暮色闌珊,皓月當空,銀色的月光照映出斑駁的樹影,遠處的新橋上亮起了暖黃色的燈火,河的盡頭望不見一葉扁舟,只有零星的行人路過,呼嘯的狂風吹著橋畔瘋了似生長的枯草,廣播里放著哀婉凄惻的笛聲。任憑景點如何翻新,卻無法重現那荒廢的池苑、被砍伐的喬木,繁花似錦的廣陵,終不過是大夢一場。“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年少時不斷記誦還會出現偏差的《揚州慢》,此刻被我惦念于心。
記得駱玉明老師曾在書中寫過:“讀古典詩詞,能夠更好地建立我們跟我們的民族文化的一種血脈關聯,理解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和人生趣味。”年少時記誦古典詩詞,培養了我們感受民族文化的能力,古典詩詞能開闊少年的視野,促使少年擁有語言的敏感性與情緒的感知力,在龐大的語言體系中,替少年選擇出最優的那部分。那個遙遠初春種下的一粒種子,在多年后某個秋雨滴答的午后,終于長成了高高的麥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