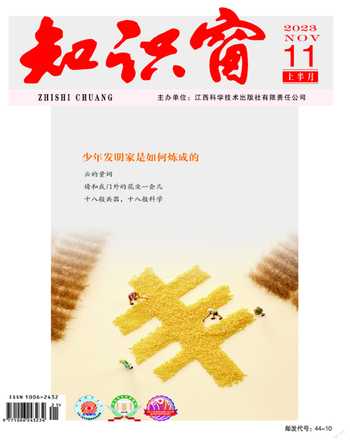屋檐是故鄉的眉
寒石
新辦公室窗外,有一片黑黝黝的土瓦屋頂和一個淺淺的屋檐。閑暇時,我會放下一眾冗務,閑坐窗前,心里期待著一場不期而至的雨。
屋檐是為雨而生的吧。現在的房子越來越細長高聳,像一棵棵無枝無蔓的樹,陰雨綿綿或者酷暑炙烤的日子里,頭頂上獨缺可以遮陰避雨的屋檐,陽光和雨以同樣的直白方式潑灑下來,街頭、路上的行人無處可躲藏。風對人的影響要小些,只是沒有屋檐的庇護,風的堅硬、潑辣,一如風的張揚、無羈。
從前的房子都是有屋檐的。在鄉村,一棟木結構樓房通常有四個屋檐。前屋檐通常都是敞開式的,向著風霜雨雪、日月晨昏,以及地上走的、天上飛的一眾生靈。后屋檐則被墻封起來,成為一家人日常起居的一部分。一間房子若沒有屋檐,是不可想象的,就像一個人沒有眉毛。一棵樹,若只見樹干而沒有枝丫,那就是電線桿。
現代人對房子的基本訴求是空間,是容積率,能包的都要包起來,屋檐成為雞肋般的存在。所以現今的房子,屋檐大多作無檐滴水處理,封閉得嚴嚴實實,哪里還有檐的影子。
民宅屋檐的功能肉眼可見。我家老房子,上屋檐窄些,一米左右,基本功能是保護板壁,免遭風雨、陽光侵襲。下屋檐就寬多了,幾乎就是一間正房的寬度。一對檐柱與橫梁的組合,以及整排的木椽子把檐頭深深挑出來,下面就是一家子一個半遮陰、全公開狀態的家庭或農事活動與操作場地。屋檐下,是農家一個個咸淡自知、風輕云淡的安恬日子。
在我的印象里,父親和母親一直在寬敞的屋檐下忙碌:晾曬、灑掃、聊天、吃飯、納涼,或者把竹椅、晾衣架、花盆等從屋檐東首搬到西首,又從西首搬到東首……有些時節,屋檐下堆放的是剛打的稻谷、番薯、芋艿或稻草、芝麻秸、毛豆稈。父親走后,母親堅守著這樣的日子。屋檐下,一年四季,她總有忙不完的活。累了,她就坐在竹椅上歇一會兒,乘乘涼,或曬曬太陽,陪伴她的是屋檐下隨手夠得著的鋤、犁、扁擔、掃帚、土箕等農具和家什。很難想象,沒有屋檐,她的生活會是什么模樣。
“拂水競何忙,傍檐如有意。翻風去每遠,帶雨歸偏駛。令君裁杏梁,更欲年年去。” 一對燕子落巢在一戶人家屋檐下,銜泥筑巢,捉蟲育雛,風里雨里,穿梭忙碌,日滋月長,竟有些留戀彷徨,想要年年歸巢這戶人家的屋檐下。這樣的情景劇在老家屋檐下年年上演。燕子是家鳥,是認家的。每年開春,我家那兩對家燕總像約好了似的,雙雙對對,大約前后相隔幾天,就會回到我家屋檐下,在板壁上筑巢,燕語呢喃,養兒育女。
屋檐是長在故鄉臉頰上的一道眉毛。我長大了離開家鄉,在城市漂泊,累了,倦了,還是要回到老家,住在有屋檐的老屋里,心里仿佛才踏實。屋檐是我鄉愁的一部分,也是我靈魂的皈依處。無論走到哪里,那一對如眉的屋檐,總是陪伴在我心靈的原鄉,為我遮風擋雨,在頭頂扯一片蔭涼。
下雨了。此刻,窗外如黛土瓦與屋檐間勾勒的這片天際,正如期飄著一場淅淅瀝瀝的雨。人坐窗后,看雨在屋脊上絲絲縷縷的纏繞,細細密密的陣腳落在土瓦上,激起一撥撥濃白雨霧,像一個人的心緒,始而紛紜錯雜,漸漸被稀釋、消融,趨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