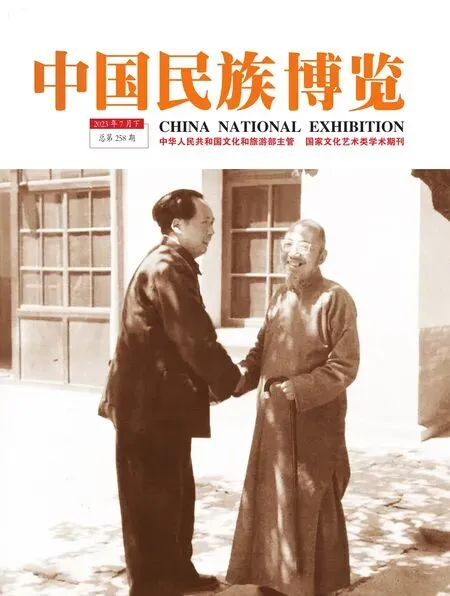《傾城之戀》影視改編“蒼涼”主題的偏移
姚培璇
(湖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湖南 長沙 410082)
引言
作為同是敘事藝術(shù)的影視與文學(xué),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是一個相當鮮明的文化事實。隨著聲光化電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影視藝術(shù)掌握的手段越來越有力地將讀者變?yōu)橛^眾。相比于影視藝術(shù)感官化、科技化的敘事手法,文學(xué)相對單調(diào)的敘事手法似乎落于下風(fēng)。即便如此,眾多優(yōu)秀的導(dǎo)演在將文學(xué)經(jīng)典影視化時,仍持有謹慎謙虛的工作態(tài)度。這是因為文學(xué)經(jīng)典的文字張力蘊含的特殊魅力幾乎是難以復(fù)刻的,尤其是蘊含在整部文學(xué)作品字里行間的主題情感意蘊常常在影視化后失去了神韻。正因此,巴贊說:“作品的文學(xué)素質(zhì)越高,改編作品就越是難與它相媲美。”
《傾城之戀》作為張愛玲的代表作廣受好評,其中許多意蘊深刻的佳句引起讀者的強烈共鳴。小說塑造的白流蘇與范柳原成為張愛玲小說人物長廊中的經(jīng)典形象。1984 年《傾城之戀》第一次影視化為電影。2009年《傾城之戀》被改編為三十四集的電視劇。兩部作品雖然各有動人之處,但都沒有將《傾城之戀》的“蒼涼”主題表達到位。電視劇版《傾城之戀》由于篇幅長、人物多、支線情節(jié)繁雜,最終的主題走向了家國情懷。與其說電視劇版《傾城之戀》是小說文本的改編,倒不如說是一部白流蘇與范柳原的同人電視劇。電影版《傾城之戀》情節(jié)與臺詞還原度很高,可見導(dǎo)演的本意并不像電視劇那樣進行創(chuàng)造性改編,而是希望拍出原著的神韻來。那么,在情節(jié)與臺詞還原度都較高的情況下,為何“蒼涼”的主題表達仍然出現(xiàn)了偏移的情況,這是本文想要討論的問題。
一、忽略色彩電影藝術(shù)語言
真正懂得運用色彩不應(yīng)當用現(xiàn)實主義的手法,而應(yīng)當用表現(xiàn)主義和象征主義的手法去運用。色彩在電影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色彩給觀眾帶來的感染力往往可以使作品主題實現(xiàn)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表達效果。《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黑白影片中那個紅衣小女孩給觀眾的視覺及心理震撼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色彩的戲劇價值與心理價值若能得到有效發(fā)揮,將使影片具備獨特的魅力。
《傾城之戀》原著中張愛玲多處運用鮮明的色彩進行渲染烘托,色彩中蘊藉了豐富的文學(xué)意蘊與內(nèi)涵。讀者閱讀時在腦海中進行再加工時便領(lǐng)會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蒼涼”氛圍。在電影版《傾城之戀》中這些蘊藉深厚的色彩片段卻并未得到影視刻畫。影片對色彩這一電影藝術(shù)語言的忽略使“蒼涼”氛圍失去了一個絕佳的載體。
張愛玲在描繪白公館時將物件的色彩進行了細致的刻畫。昏黃的燈光與青磚地營造出朦朧的氛圍。在這樣的光線下,紫檀匣子、綠泥款識、琺藍自鳴鐘、朱紅對聯(lián)、金色團花和玻璃罩折射的晶瑩華光,刻畫出一幅富麗堂皇而朦朧恍惚的迷夢般的畫面。這時畫面中出現(xiàn)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墨汁淋漓”是一個兼具色彩與形態(tài)的形容詞,流蘇覺得她就是那個字,虛飄飄的。這個突兀的墨色在虛幻絢麗的色彩環(huán)境下似乎也虛無起來。這一段色彩描寫非常精彩,奢靡富麗的白公館透出一絲陰森之氣,虛空懸浮、暗無天日之感躍然紙上。白公館的環(huán)境通過色彩實現(xiàn)了社會地位與精神氣質(zhì)的雙重刻畫,青春猶在的白流蘇在其間的壓抑與失意得以傳神表達,富貴繁華與青春年華虛無縹緲,難以捉摸,“蒼涼”之氣悠悠彌漫。
電影對這一段的處理則有形而無神。首先,中景鏡頭呈現(xiàn)祖先的畫像,鏡頭拉近定格在祖先官服的衣袖上,衣袖花紋繁雜卻不艷麗,并無鮮明的視覺焦點。隨后鏡頭拉向一座時鐘,是對文本“琺藍自鳴鐘”的呼應(yīng),但這座時鐘并未顯出色彩特征。女主的近景鏡頭之后,畫面出現(xiàn)一幅對聯(lián),鏡頭定格于“負”字。這副對聯(lián)雖也與文本物象呼應(yīng),卻紅得不鮮艷,似乎已經(jīng)掉色,墨跡工整娟秀,給人一種怯生生的觀感。與原文朱紅對聯(lián)、金字壽字團花、墨汁淋漓的大字組成的環(huán)境氛圍大相徑庭,其中蘊含的蒼涼夢幻也就無影無蹤了。
俄羅斯畫家列賓說過,色彩即感情。不同色彩(或同一色彩的不同運用)能引起不同的情感反應(yīng),產(chǎn)生相應(yīng)的情緒效果。張愛玲在《傾城之戀》兩次對紅色的著重刻畫是一個很恰當?shù)睦印5谝惶幨前琢魈K與范柳原見面之后,親戚鄙視地咒罵白流蘇癡心妄想,白流蘇聽得清楚,卻不做聲。她鎮(zhèn)靜地擦亮洋火,“眼看著它燒過去,火紅的小小三角旗……剩下紅艷的小旗桿。”這里的紅色象征著白流蘇在家庭的逼迫下,逃出去的信心已經(jīng)堅定,另博一片天地的野心熊熊燃燒。這段文字光影色俱全,是非常適合影視化的文本,但影視化效果卻讓人并不滿意。電影版《傾城之戀》僅僅是還原了“白流蘇點蚊香”這個情節(jié),是干巴巴的動作演繹,重點沒有落在白流蘇的心理刻畫,反而落在了白流蘇點蚊香時的背景音,這樣一個活在人世間艱難女子的心理掙扎變成了家長里短、爾虞我詐,流于俗套。
第二處紅色是白流蘇與范柳原約會時,張愛玲濃墨重彩地刻畫了一種植物——野火花。張愛玲運用“紅得不能再紅了”“紅得不可收拾”的字眼來形容野火花的紅。她寫道“壁栗剝落燃燒著,一路燒過去,把紫藍色的天也熏紅了”。緊隨其后,白流蘇與范柳原便在灰墻下進行了“整個文明都毀掉了”那段經(jīng)典對話。這樣熱烈放恣的紅色,是范柳原與白流蘇二人愛情的象征。兩個聰明人克制著、博弈著,誰都不肯落了下風(fēng)。但如果不用勾心斗角,他們心中對彼此的愛意像野火花一樣蓬勃,也就是說,野火花是二人隱秘內(nèi)心世界的委婉外化。遺憾的是,電影版《傾城之戀》將這一意象完全刪除,影片中未能看到紅色野火花的身影。
二、心理描寫的粗暴處理
電影藝術(shù)對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刻畫方法多種多樣,直白的畫外音與委婉的象征隱喻都能達到心理描寫的效果。造型、構(gòu)圖、音樂、光影都是構(gòu)成象征與隱喻的有效手段。因此,選取什么手段進行人物內(nèi)心的表達考驗著影視工作者的功力。
《傾城之戀》中大段的心理描寫使全文呈現(xiàn)出深沉綿密的風(fēng)格。從六小姐到范太太,若不是對白流蘇心理變化的細膩刻畫,《傾城之戀》將會淪為二婚女恨嫁富二代的俗之又俗的艷情故事。時代的沉重與世事的虛無凝聚在一個中國女人的漂泊與歸宿中,天災(zāi)人禍之下,愛情的渺茫與偉大在流蘇的心里沉甸甸又輕飄飄,白流蘇的故事不過是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的其中一個。因此,若想將“蒼涼”主題表達到位,白流蘇的內(nèi)心世界必須得到精準的刻畫。
在電影版《傾城之戀》中,對流蘇的內(nèi)心刻畫不乏可圈可點之處。流蘇在胡琴悠揚的背景音中對鏡自憐是蒼涼感較為濃厚的一段描寫。流蘇“偏著頭,微微飛了個眼風(fēng),做了個手勢”,她向左走了幾步,向右走了幾步,然后她笑了,“陰陰的,不懷好意的一笑。”白流蘇的肢體動作背后是怎樣的心理動機呢?文學(xué)文本是有答案的,白流蘇對鏡自視,蒼涼的胡琴連接著遼遠的古時與虛無的今夕,她一邊慶幸青春猶在,一邊又恐懼過兩年就老了,青春緊迫。時間悄無聲息地摧毀一切,忠孝節(jié)義故事的驚天動地都已化作一絲蒼涼的胡琴,更何況是她白流蘇的青春。不懷好意的一笑中應(yīng)是白流蘇野心與欲望的象征,她知道自己美貌猶存,必須利用它爭點什么。電影版《傾城之戀》借助影視藝術(shù)的可視性和動作性,抓住了重要的動作細節(jié),配合蒼涼的胡琴聲,蒼涼主題隱約可見。
但是,在白流蘇與范柳原的戀愛拉扯中,白流蘇的心理發(fā)展變化是小說的重中之重,是白流蘇行為選擇背后的心理邏輯,是整篇小說蒼涼主題的生發(fā)之處。電影版《傾城之戀》對這些細膩的心理描寫采取了粗暴的處理方式,使得這些心理刻畫僅僅成為情節(jié)發(fā)展的推動器從而失去精髓。
第一種粗暴處理方式是直接將白流蘇的內(nèi)心獨白處理成配角的臺詞。灰墻對話的名場面后,流蘇有一段關(guān)于精神戀愛與肉體戀愛的思考。流蘇是贊成精神戀愛的,特別的是,張愛玲并沒有將流蘇刻畫為追求柏拉圖之愛的高尚女子,而是強調(diào)流蘇贊成精神戀愛是因為精神戀愛更有可能走向結(jié)婚。這就說明對于流蘇而言,愛不愛不重要,重要的是以結(jié)婚為目的找到終身的歸宿和堅實的經(jīng)濟依靠。這一段心理描寫在電影中被處理為徐太太的兩位朋友在跳舞時的調(diào)侃,哄鬧的氛圍消減了這段戀愛故事里的沉重之感。
白流蘇與范柳原鬧別扭后有一段心里獨白也被處理為徐先生和徐太太的臺詞。白流蘇識破了范柳原的激將法,明白范柳原雖愛他卻不想娶她,不過是冠冕堂皇的陽謀,逼她就范而已,她絕不能束手就擒。白流蘇的精明功利躍然紙上,愛情這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白流蘇要逆風(fēng)翻盤。被處理為配角臺詞后,兩人之間的矛盾便失去深度,甚至變?yōu)榇差^吵架床尾和的情侶日常。
第二種粗暴表達方式是直接刪掉、不予刻畫。白流蘇回到上海后受百般嫌棄,她的內(nèi)心是非常希望出去找事做自食其力的,但是她怕一旦外出做工就失去了貴族淑女的身份,范柳原更不會娶她了。這一段心理描寫使“蒼涼無奈”之感傳達出來,身為新舊交替時代的弱女子,處心積慮將嫁人作為事業(yè)幾乎是沒有辦法的事,哪怕她心中有自立自強的火苗也在時代的狂風(fēng)中無法堅持。盡管她無法接受自己的婚姻的實質(zhì),但她卻逃不開這個枷鎖,因此也無法付出真心。可以說,《傾城之戀》蒼涼之感的沉重底色與當時時代的氛圍觀念息息相關(guān),因此這一段心理描寫的直接刪除令人非常惋惜。
三、光與聲的敘事功能
有聲電影出現(xiàn)后,影像與聲音共同組成了電影藝術(shù)的表意系統(tǒng)。聲音對視覺形象的加工刻畫作用毋庸置疑。作為聲音的重要元素,臺詞和音樂是電影版《傾城之戀》值得關(guān)注的地方。電影版《傾城之戀》臺詞還原度極高,對白、獨白和旁白基本都是書中原句。臺詞內(nèi)容的高度還原保留了原著的部分氣質(zhì),且兩位主演的音色較有故事感,使得蒼涼的主題意蘊不至于消失殆盡,這也是本文認為電影版《傾城之戀》只是主題偏移而非主題顛覆的主要原因。
可以說,音樂是電影的一個獨立敘事元素。音樂往往帶動觀眾的情緒,調(diào)整敘事的節(jié)奏,引導(dǎo)觀眾向著主旨意蘊的方向自主思考。電影版《傾城之戀》的開頭是昆曲《牡丹亭》中的驚夢選段,宛轉(zhuǎn)悠揚的戲曲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古典婉約氣質(zhì),且暗示了白流蘇與范柳原之間的情愛糾葛。這一部分的處理很高明,影片的整體氛圍和主旨意蘊都得到了較好的表達。在文本中,胡琴首尾出現(xiàn),前后呼應(yīng),說不盡的蒼涼故事盡在胡琴之中。在電影中四爺演奏的胡琴也起到了良好的烘托氣氛的作用。
光線的影調(diào)層次會直接影響到鏡頭的整體氛圍,是幫助敘事的重要因素。光的處理體現(xiàn)著影視作品的美學(xué)趣味和氣質(zhì)意蘊。《傾城之戀》蒼涼綿密的中國氣質(zhì)尤其應(yīng)該借助影視的光影技術(shù)得到展現(xiàn)和放大。《傾城之戀》原著中多次寫到月色,如范柳原給她打電話,他們在愛里崩潰爭吵。流蘇淚眼朦朧中看到大而模糊的月亮,張愛玲寫得很細膩,那銀色的月亮甚至有著綠色的光棱。這月色的象征意義值得細品,白流蘇淚眼朦朧,月影模糊,范柳原的月亮被藤蔓遮擋了一半,但月亮是又大又亮的。這隱喻著白流蘇與范柳原之間的愛情是有真誠美好的情意的,只不過兩人在博弈中費盡心機,不肯坦誠才看不見月亮。流蘇站在梳妝臺前,纖月一鉤,與海與鏡與窗相映,朦朧唯美,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白流蘇和范柳原第一次接吻。這與第一次表白時的月色大不相同,這時的月色清冷單薄,但他們二人都看得到。這次熱吻后,范柳原只和白流蘇待了一周就走了,白流蘇很快獨守空房。其實感情突破那天的月色就是這樣結(jié)局的隱喻。兩處對月色的細膩刻畫,使整個文本的蒼涼氛圍濃厚起來。從上述分析可知,兩處月光的刻畫并不是閑來之筆,應(yīng)該引起重視并在影視化中加以刻畫。然而在影片中,月色只是作為交代夜晚時間的附屬品,內(nèi)在蘊含的人物情緒與蒼涼主題并未得到深入挖掘。
由上文可得,電影版《傾城之戀》對原著蒼涼主題的刻畫雖不乏可圈可點之處,但由于影片對色彩這一電影藝術(shù)語言的忽略,對原文人物心理描寫粗暴處理以及未能充分利用光與聲的敘事功能,導(dǎo)致最終呈現(xiàn)的主題意旨偏移,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