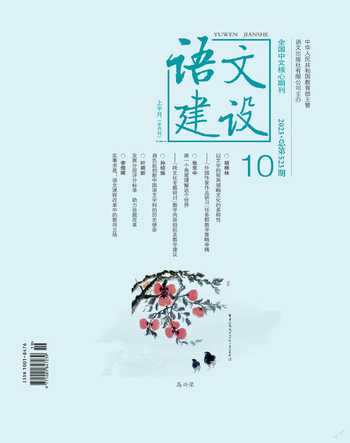肩負起創新中國語文學科的歷史使命
孫紹振
【摘要】中國語文學科具有特殊性。中國語文學科的現代化建構需要對搬用西方前衛文論的教條加以批判。首先,超越西方文論一味拘泥于讀者身份,被動接受現成文本,要在想象中主動與作者對話,思考為什么這樣寫而不那樣寫。其次,直接從豐富的文本出發,超越西方前衛文論的線性思維。初步構架文本的三個層次的立體結構,表層是意象(細節)群落的展示,是顯性的;中層是情志的起伏轉折,是隱性的;底層則是文體形式,是特別隱秘的。
【關鍵詞】語文學科;特殊性;主動對話;文本解讀三維結構
一、沒有語文學科的特殊性就談不上“學科大概念”
“大概念”論者關于先秦百家爭鳴說了那么多,雖然沒有說清楚“大概念”,但是多少有所觸及,重點是“人文價值培育”“民族文化認同”“文化自信”。這些不無道理,然而只從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提及的“大概念,是—切人文學科的共同屬性,并不是論者設定的主題——語文“學科大概念”,因為其中沒有語文學科的特殊性。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
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
從語文學科來說,沒有語文學科的特殊性,是談不上“學科大概念”的。雖然論者也沒有忘記在古典詩歌中要注意“審美情志”,卻只是—筆帶過,重點闡釋的是“梳理所學作品中常見的文言實詞、虛詞、特殊句式和文化常識,注意古今語言的異同”。但是,古今詞語的異同其性質只是普遍的工具性,而不是語文學科的特殊性。“大概念”論者所說這些不過是詞語的詞典意義,表達的只是詞語的核心意義,放在具體語境和上下文中,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其非常規甚至反常規的運用會產生隋趣、諧趣和理趣的分化。如魯迅《論“他媽的”》中說,中國罵人的粗話“他媽的”隱含著親切意味,甚至相當于“親愛的”。在《小二黑結婚》中,二黑的父親二諸葛罵他“小雜種硬沖人物頭”,實際上罵的是自己和老婆,人物的內在情感很是傳神。《紅樓夢》中王熙鳳得知丈夫在外娶了尤二姐做二房,說了一句“這才好呢”,這個“好”字,其中包含了多少殺機。而林黛玉臨終前說的一句“寶玉,你好……”其精彩就在于隱含著豐富的超越詞典意義的意味。王熙鳳的“好”和林黛玉的“好”,與《好了歌》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好”的差異有多懸殊,就有多少藝術和思想的深度精妙在其中。詞語的內涵是一個開放的載體,不管是白話還是文言,隨著文本的語境、體裁、作者的傾向不同而載入無限可能的趣味,文章的雋永深邃之處,往往就在這種超越詞典意義之處。這才是語文學科的特殊性所在。
舉一個比較復雜的例子。劉備三顧茅廬,求策于諸葛亮:“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這里的“孤”字用現代漢語解釋就是古代王侯的謙稱。可是,這時候的劉備既不是王,也不是侯,他幾度投靠各方勢力,狼狽落魄,后不得不依附劉表,劉表又猜忌他有野心,讓他擔任新野令,充其量就是一個縣的武裝部長,怎么能自稱“孤”呢?《三國演義》寫“三顧茅廬”時就很謹慎,把“孤”字改成了“備”,意味著就是一個普通人來求教。至于“欲申大義于天下”里的“申大義”,就是用正統理念統—全國人心。劉備明明是在練兵積蓄力量,意圖以暴力統一全國,卻冠冕堂皇地使用正統的“王道”話語招攬人心。
諸葛亮當然對他的這種“官話”心領神會,為他制訂了聯合孫吳,借荊州,入蜀中,建立自己的根據地的計劃。養精蓄銳,天下有變,兵分兩路問鼎中原,結論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諸葛亮并不掩飾,沒有用“申大義”之類的王道話語,直截了當地說明“霸業可成”。霸業,就是霸道,暴力奪取政權。“霸業”一出口,已經換了—套話語,把劉備的心思公開化,其效果是二人“情好日密”到令劉備的結義兄弟關羽和張飛不悅的程度。西晉陳壽寫《三國志》時,劉備建立的蜀漢王朝已經滅亡,但他并沒有把劉備像曹操那樣列入“本紀”,而是列入“傳”。那為什么還要讓他稱“孤”?這是因為陳壽曾為蜀官,有潛在的正統意識。其深長意味,不在字面,而在字里行間。
中國史傳文學的春秋筆法,在記言、記事的實錄中寓褒貶,其精彩之處就在這兩套話語轉換之間。這才是傳統語文學科的特殊性所在。用所謂“常見的文言實詞、虛詞、特殊句式和文化常識,注意古今語言的異同”,只能是盲人摸象。至于“雍容”“犀利”“雄奇”“樸拙”“領悟其妙處”,完全是印象式的空話,這不是“學科大概念”,而是不折不扣的空概念。真正的語文“學科大概念”,沒有西方現成話語可用,論者也就只能不厭其煩地申說:“學習先秦諸子散文,以加深對傳統文化之根的理解。要注意領會先秦諸子對社會人生的洞察,思考其思想學說對立德樹人、修身養性的現實意義。”說說去,還是人文學科的共同性,除此就無語可說,其原因在于根本沒有直接分析語文學科特殊性的自覺。要做到這一點,必碩直接從文本的豐富直覺中進行第—手的歸納,概括出文本唯一的獨特性。這就是說,要有相當的原創性,而創性的攔路虎,則是教條主義的“大概念”。
真正的語文學科不能什么都是“大概念”,而是語文學科的特殊規律,中國學派的語文學科。要揭示語文學科的特殊規律,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要從所謂“大概念”中擺脫出來,而且要加以批判,超越西方文論所執著的語言論單因單果的線性思維定式。五四運動時期的先賢“輸入學理”,未能完成的“再造文明”任務,將由我們這—代人來承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妙處的“領悟”,不是什么“雍容”“犀利”“雄奇”“樸拙”印象式的空話所能蒙混的。這些內涵貧乏的概念,馬克思稱之為抽象(貧困)概念,馬克思要求的是:從抽象上升為具體,從無限豐富的文本中,在矛盾的具體分析和轉化中歸納出新的內涵,在正反合的運動中,作螺旋式上升,達到多種規定性(內涵)的統一。提出中國學派的原創性的基本范疇、范式(或者用他們的話語來說“話語”),我們才有資本當仁不讓地與西方文論對話,—爭長短。
追隨西方前衛文論,卻不知其對文本分析公然宣布無能,國人卻如此迷信,原因很多。篇幅所限,謹略舉其大端。
二、擺脫西方前衛文論對作品的被動接受,主動與作者對話
西方文論流派眾多,在根本上同樣視作品為現成的產品,以接受為務,即使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強調接受的主體性,但是文本仍然是固定的,接受的被動性仍然是共同的。“大概念”論者企圖改變這種被動性,從文本以外之“知識”加以“綜合”、虛構成“大概念”,采用任務驅動等,其旨在擺脫被動。實踐證明,這種試探脫離文本更加遙遠,已經成為試錯。但這種試錯是有價值的。究其根源,不知經典文本乃是創造的結果,欲知其奧秘,僅從結果是無法看到造成結果的原因的。因為任何結果都有其豐富的原因,但是結果造成之后,原因就被遮蔽了。正如,花是紅的,但是花為什么這樣紅?其復雜的原因,科普作家賈祖璋寫了那么復雜的文章,涉及物理、化學、生物等方面,可能還沒有窮盡其原因。到了詩歌中,“霜葉紅于二月花”,結果是動人的。但為什么秋天的霜葉比春天的鮮花還美,原因就在詩人情感一剎那的、不可重復的特殊性中了。
拘泥于被動接受作家創造的結果,就不可能洞察造成結果的原因。因而西方前衛文淪公然宣稱,理論和閱讀是不相容的。為什么西方文論的泰斗如此無奈?至今無人正面回答。
其實,這個問題并不復雜,早在20世紀,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就指出產生這種悲劇的原因:“作品的被創作存在,只有在創作過程中才能為我們所把握。在這—事實的強迫下,我們不得不深人領會藝術家的活動,以便達到藝術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據作品自身來描述作品的存在,這種做法業已證明是行不通的。”西力學界幾乎沒有什么人聽懂了海德格爾對他們“行不通”的警示。一味把文本當作某種現成物,把自己僅當作文本的被動接受者,完全沒有意識到只有進入“作品的被創作”的“過程中”,也就是設想自己也是作者,與之對話,才能化被動為主動,洞察藝術和思想的奧秘。這_點說起來很深奧,但并不神秘。魯迅先生有—段話,可以作為海德格爾這一思想的注解:
凡是已有定評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說明著“應該怎樣寫”。只是讀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領悟。因為在學習者一方面,是必須知道了“不應該那么寫”,這才會明白原來“應該這么寫”的。
這“不應該那么寫”,如何知道呢?惠列賽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復著這問題——
“應該這么寫,必須從大作家們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領會。那么,不應該那么寫這一面,恐怕最好是從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學習了。在這里,簡直好像藝術家在對我們用實物教授。恰如他指著每一行,直接對我們這樣說——‘你看——哪,這是應該刪去的。這要縮短,這要改作,因為不自然了。在這里,還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顯豁些。”
西方前衛學者幾乎毫無例外地只看到作品這樣寫了,沒有意識到作者為什么沒有那樣寫,全然無視海德格爾的教導。只有在想象中,進入創作過程,才能從文本一望而知的表層進入—望無知的深層。也許這樣的思路在西方文論及其追隨者看來有空談之嫌。并不是所有經典之作,都有原稿、修改稿可資對照,但是,對于大量沒有原稿對照的作品,可以進行還原和比較:設想自己是作者,主動與作者對話,在想象中,參與作者創造作品的過程。小說都是虛構的,人物的言行、情節的發展都是作者匠心獨運的設置。
魯迅的《祝福》中,讀者看到的是洋林嫂逃到魯鎮,被搶親,丈夫和兒子死后,又回到魯鎮。表面上是客觀發生的事情,實際上都是魯迅設計的。五四時期—般的婦女題材作品,都是寡婦要改嫁,遭到封建宗法勢力橫加干涉,魯迅卻反其道而行之,讓祥林嫂不想改嫁。可以想象,如果僅寫祥林嫂力圖改嫁而遭受迫害,則僅能表現封建禮教之夫權的無理,而寫祥林嫂不愿改嫁,由其婆婆用搶親的手段強迫其改嫁,則能表現封建禮教族權(兒子屬于父母)與夫權之矛盾:按夫權不得改嫁,按族權又可用人身侵犯的手段強迫其改嫁,這不但矛盾,而且野蠻。祥林嫂改嫁后與丈夫、兒子生活在偏僻山區,本可安分守己地過完—生。可是魯迅又沒有那樣寫,而是狠心地讓其丈夫死掉,兒子被狼吃掉。目的是把祥林嫂逼回魯鎮,進一步把她逼上絕路:虛構出—個關心她的柳媽勸說她去捐門檻為改嫁贖罪。目的就是讓祥林嫂面對神權:閻王要把她鋸成兩半,分給兩個男人。閻王不去追究強迫改嫁者的罪行,反而懲罰祥林嫂,這就不僅是野蠻,而且是荒謬了。這樣的情節設計,就是為了揭露夫權不講理,族權不講理,神權也不講理。封建禮教的邏輯就是這樣野蠻而荒謬。
魯迅為什么沒有讓頗有反抗性的祥林嫂拒絕以一年以上的工薪為廟里捐門檻呢?目的乃是為了顯示對寡婦存在歧視的這種野蠻荒謬的偏見,不但魯四夫婦有,而且祥林嫂也視為天經地義。祥林嫂自以為捐了門檻就贖了罪,在年關祝福時,主動端福禮,魯四奶奶一句看來很留有余地的話“你放著罷,祥林嫂”,就使她精神崩潰了。這是為了強調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自己也為這種野蠻荒謬的邏輯所麻醉。全部情節之所以要這樣設計,就是為了顯示這個悲劇是沒有兇手的。兇手就在每一個人的頭腦中,每—個人都有責任。對這樣—個悲慘的結局,為什么要把它放在年關祝福的氛圍中?為什么要讓與這個悲劇毫無瓜葛的人——“我”來敘述,且感到不可擺脫的歉疚?而整個魯鎮的人都歡樂地祈求來年的幸福,這是為了表現對群眾麻木的愚昧慣性,同時也是對思想啟蒙前景的某種悲觀。
與作者對話,進入作者創作過程,是很復雜的,這里只是簡單舉例。全面系統概括起來,要有多達十個層次的操作程序的具體分析。
三、超越西方前衛文論的線性思維,建構中國文本解讀的三維立體結構
20世紀西方前衛文論,有所謂語言學轉化,把文本解讀僅歸結為語言,造成了單因單果的思維定式。但文本并不是平面的,而是三維立體結構。其表層由意象群落構成,這是一望而知的,顯性的;中層則是情志的動態脈絡,是文本的情神所在,是隱性的;其最深層的,乃是不同文本形式。歌德說:“材料是每個人面前可以見到的,意蘊只有在實踐中須和它打交道的人才能找到,而形式對于多數人卻是一個秘密。”這就是說,形式的規范性,只有內行才能領悟。須要補充的是,形式不但是由內容決定的,而是反作用于表層的時空延續和意象群落中的情志脈絡,為其定性的。這一點,我在論“大單元/大既念”系列文章中有所陳述。但總體來說,都是屬于靜態的概述,事實上,每—層次都須要系統展開。
詩的意象,外國權威只講到把情趣寄托在對象中,其實并不全面。對象不是全部,而是有特殊性的局部,而情感也必須是有特殊性的,是因時、因地而異的,并不一定是作家的全部情感,二者結合才構成意象。這還只是胚胎,還要在不同的形式中培育才能成為形象。在敘述文本中這不叫意象,而叫細節,優選特殊的局部同樣勝過總體。但是,詩歌是概括的,賀知章《詠柳》中的柳樹,是沒有時間地點的、有普遍性的,而朱自清筆下的《背影》僅為人體之局部,為特殊時間、地點和人物關系所決定,就勝過全部的外貌表隋的描寫。在意象和細節的群落之間,是作品的文脈或者意脈,是人物心理動態的起伏過程。《背影》的動人就在于,父親把已經成年的兒子當作小孩關懷,而兒子卻不領情,覺得他“迂”、土氣,等到父親為他買橘子,勉為其難爬月臺時,兒子感動得流下眼淚,卻不讓父親知道,日后想起來就感到愧疚,流淚。真正把文章寫出來,已經是八年之后。《背影》的精彩全在文脈的起伏變化中,其經典性就在于空前地揭示了:有—種親子之愛乃是持久的愧疚。愛是不完全的,往往是有隔膜的,但是,愛的深沉是不可磨滅的。—代又—代的讀者憑直覺為之感動,而要把直覺用明確的語言概括出來卻又是非常困難的。故在近百年之后,仍然有特級教師、副教授讀不懂,甚至要求將《背影》從語文課本中刪除。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中,讓阿長講了一個極端荒謬的太平軍抓捕婦女的故事,當清軍攻城時,讓其脫光褲子,清軍的大炮就炸了。本來對她非常反感的小魯迅,居然覺得她有“偉大的神力”,產生了“空前的敬意”。這顯然是反語,構成了幽默的諧趣。待他期盼而不得的繪圖本《山海經》由長媽媽春節后為他帶來,小魯迅驚喜不已,覺得她真的有“偉大的神力”,對她產生“空前的敬意”,同樣是“神力”“敬意”,此處變成了詩意的情趣。文脈如此大幅度的轉折,表現了魯迅不但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且是欣其善良。諺篇在當年的散文中,堪稱藝術上的神品。
所有意象和意詠的經營都受文本形式制約。《阿長與(山海經)》的文體是散文,故把愚昧而世俗的保姆寫得動人,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詩歌,就表現了不是親人,更勝親人,無條件的超世俗的愛。
如此這般的三重的立體結構還只是靜態的描述,作為藝術形式并不是自然成熟的,而是從草創到成熟,到亞形式的分化,到流派和風格的突破,有一個歷史的過程。正如真理不是靜止的結論,而是過程,在不斷的矛盾中,在不可窮盡的過程中轉化統——樣,不進入動態的、發展的歷史過程,是不能完成建構中華文本解讀理論的歷史使命的。原創性的建構要以歷史和邏輯的方法作動態的分析和綜合,中國語文學科的現代化建構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9
[2]在《邏輯學》一書中,黑格爾認為,抽象可分為知性的抽象和理性的抽象兩種:所謂“具體”,又可分為感性表象的具體和概念的具體兩種,其中前者為外在的復雜多樣性,而后者則代表對一切規定性的綜合。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概念化,將之作唯物主義的改造。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書中,指明—般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即“從具體到抽象”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將自己的方法概括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3]J.希利斯·米勒,致張江的第二封信[J].文學評論,2015(4)
[4]馬丁·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M].孫周興,選編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6:297
[5]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321
[6]朱光潛西方美學史(第十三章·歌德章)[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