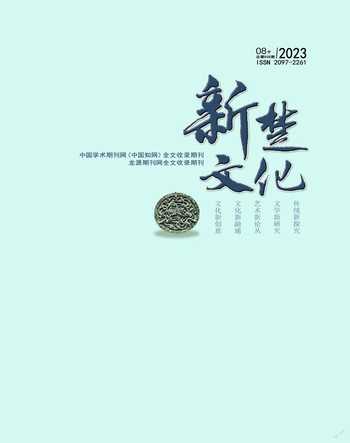歸于悲劇的掙扎與抗爭:《祝福》與《離婚》小說中的女性命運
【摘要】小說《祝福》與《離婚》對祥林嫂和愛姑的形象塑造,是魯迅對下層舊式勞動婦女命運的關注與書寫,在自己的命運中苦苦掙扎的祥林嫂和敢于與自己的命運抗爭的愛姑,最后都走向了悲劇。逆來順受的人和大膽抗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劇,魯迅用兩位底層勞動婦女的命運深層次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殘酷,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社會中,逆來順受的、大膽抗爭的均被推向了悲劇,女性的無路可走進一步深化了魯迅的小說主題思想:絕望的反抗,同時也讓我們認識了魯迅的思想和魯迅的主張。
【關鍵詞】掙扎;抗爭;女性;命運;絕望
【中圖分類號】I210.97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23-0035-04
魯迅的小說《祝福》與《離婚》中對祥林嫂和愛姑的形象塑造,是魯迅對下層舊式勞動婦女命運的關注與書寫。兩篇小說的女性主人公祥林嫂和愛姑雖均屬于舊式下層勞動婦女,但兩位主人公的性格有著鮮明的區別。《祝福》中的祥林嫂逆來順受,在自己的命運中苦苦掙扎;而《離婚》中的愛姑潑辣大膽,敢于與自己的命運抗爭。然而,在封建舊思想和舊禮教的約束下,身處底層的勞動婦女,不論是忍辱負重的祥林嫂還是與命運抗爭的愛姑,最后都歸于了悲劇。祥林嫂孤獨地死于祝福之夜,愛姑賣掉了自己的婚姻,兩位主人公最后殊途同歸的悲劇,體現了封建舊道德對女性的壓抑,更深層次地反映了封建舊禮教、舊道德的殘酷。逆來順受的祥林嫂、大膽抗爭的愛姑均被推向了悲劇,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社會,女性根本無路可走,令人絕望的社會殘酷卻恰恰反映了魯迅的精神世界:絕望的反抗。魯迅對女性精神和靈魂病苦的揭示,目的是要引起療救的注意,從而揭出造成精神病態的社會。
一、苦苦掙扎的祥林嫂
魯迅在他的《我之節烈觀》中說:“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界定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著自盡”謂之烈,“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于是,死了丈夫又再嫁的祥林嫂在“道德家”四叔四嬸那里便成了被排斥的對象,“你放著罷,祥林嫂”,四嬸的一句話,徹底扼殺了祥林嫂重新獲得希望和繼續生活的可能性,讓祥林嫂淪為了乞丐,最終孤獨地死在了祝福之夜。
當我們捋順小說中的時間順序,祥林嫂第一次出現四叔四嬸家里的時候,“頭上扎著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這個時候的祥林嫂,雖然因為是個寡婦,四叔皺了眉頭,但是因為是一個安分耐勞的人,工作起來“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所以在四叔四嬸家里做工成了定局。雖死了丈夫,但是由于并沒有所謂的“失節”,即丈夫死了以后沒有再嫁,所以,四叔盡管皺了眉頭但是也并沒有阻礙祥林嫂被留用做工的機會。擁有了做工的機會以后,祥林嫂食物不論,力氣不惜,“比男人還勤快”,“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她很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祥林嫂雖然死了丈夫,但是憑借著自己的勞動能力,依然可以繼續生活,所以她很滿足。沒有“失節”的祥林嫂,有機會可以靠著自己的能力換取生活。然而,在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下,女性是難以脫離家庭或家族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的,所以,祥林嫂擁有憑借勞動獲得生活的能力但是古代的宗法制度卻剝奪了她這樣生活的獨立權。于是,祥林嫂也無法擺脫被掌控的命運,新年才過大約十幾天,祥林嫂便被她的婆婆綁回去了。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后的又過了兩個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這是祥林嫂第二次出現在四叔四嬸的家里,“她仍然頭上扎著白頭繩,烏裙,藍夾祆,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著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這個時候的祥林嫂相較第一次的出現,“兩頰失去了血色”,“也沒那么精神了”,這些變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被綁回去的兩年間,祥林嫂經歷了被逼再嫁,又一次喪夫還喪子。這在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倫理下,在宗法“道德家”的眼里,簡直就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韙”了,是要被加倍的奚落和排斥的,“你放著罷,祥林嫂”,摧毀了祥林嫂再次憑借勞動換取生活的可能。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倫理道德觀下,祥林嫂順應這種道德倫理的自我意愿被摧毀,被迫“失節”,于是,對身處社會底層的勞動婦女來說,一個終極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她屬于誰?他們既無法獨立于家庭或家族存在,既被要求“守節”,又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就只能在別人的道德標準下和別人的需求中苦苦掙扎,在被迫再嫁的過程中,祥林嫂一路號、罵,喉嚨全啞,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也無法改變再嫁的命運,“婦者服也,理應服事于人”①。
然而,“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里,是容不住的”②。祥林嫂第三次出現,是在“我”的面前,“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這個時候的祥林嫂完全失去了“人”的精神和靈魂而成了“活物”,“活物”一詞精準地道出了祥林嫂精神和靈魂被毀滅、被吞噬的悲劇命運。
二、敢于抗爭的愛姑
愛姑是魯迅小說《離婚》中的主人公,小說一開頭就塑造了一個與逆來順受的祥林嫂完全不一樣性格的人物形象。“已經鬧了整三年”,“總是不落局”,從時間的持續這一角度,可以體現出愛姑的抗爭,當她的父親都覺得“煩死了”的時候,愛姑依然“憤憤地”不屈服于那些對她以及她的婚姻的不公道,要“賭氣”,她“不貪圖回到那邊去”,勢必要她的艱難,希望七大人可以為她做主。覺得七大人知書達理,能夠明辨是非,甚至敢于“拼出一條命,家敗人亡”。愛姑的抗爭源于她本身潑辣大膽的性格,于是她的抗爭僅僅是對于個體直觀感受不公的本能反抗,她的反抗并不是對社會環境理性思考后的選擇,于是,她把自己追求公道的愿望寄托在了七大人的身上,而七大人所維護的公道就是以夫權為重要內容的宗法體制和整個的封建秩序,在強大的封建勢力面前,在維護封建權威的大多數人的圍困下,愛姑先前的銳氣已經一掃而光,只能聽從七大人的吩咐。愛姑的幻想破滅了,她的抗爭以失敗而告終。
需要我們清楚的是,愛姑的抗爭并不是對那段婚姻的留戀和不舍,而是要尋求公道,維護自己的尊嚴,維護婚姻的尊嚴。魯迅所描繪的是一個在封建宗法制度制約的社會中被侮辱、被損害的女性的抗爭和抗爭的無意義的悲劇。愛姑抗爭的失敗和悲劇說明,婦女的解放、婦女問題的解決,必須以社會的解放為前提,社會環境不改變,即使婦女本身的反抗和抗爭意識再強大,最終也只能以失敗告終。一場離婚,身邊所有人都獲得了利益,“老畜生”“小畜生”的如愿離婚,莊木三的90塊洋錢,七大人、慰老爺的“主持公道”的實現,只有離婚事件的女主角愛姑一無所有。離婚事件中愛姑的被損害是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悲劇,而具有反抗意識和尊嚴維護意識的愛姑被損害而不自知則是魯迅的反諷。
三、歸于悲劇的命運
精神和靈魂被毀滅的祥林嫂,最后死在了祝福之夜。她的死亡本身無人關注,無人在意,“怎么死的?——還不是窮死的?他淡然的回答”,然而她死亡的時間卻引起了“道德家”四叔的在意,“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生前由于“失節”不容于社會,死后也要被唾罵,死亡之前的還帶著對封建倫理道德的糾結甚至恐懼,在探問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是否有地獄、死掉的一家的人是否能見面的問題時,祥林嫂被封建倫理道德折磨摧毀得體無完膚的形象昭然若揭。而“我”對祥林嫂問題的回答,則在更深層次上加劇了祥林嫂的人生悲劇,即無論是否有魂靈,對于祥林嫂來說都是無法消解的恐懼,有魂靈,意味著死后要被鋸成兩半繼續受苦,無魂靈,意味著現世的苦難和不幸是祥林嫂的全部,活著毫無意義③。
而愛姑呢?始于抗爭,終于順從,最后還是用洋錢換掉了自己的婚姻,具有反抗意識和抗爭行為的愛姑最終也屈服于封建倫理道德,歸順于扼殺了祥林嫂的封建思想,愛姑的抗爭變得徒勞而無意義,她的服從意味著從此以后走上了祥林嫂的人生道路。被迫用洋錢換掉婚姻之后,她變得溫和順從,甚至恭敬起來了,走在最后的愛姑感謝著慰老爺,“是的,不喝了,謝謝慰老爺”,成了一個活脫脫的祥林嫂,那么,被迫再嫁,成為別人茶余飯后的談資,然后死亡,除了這些還有什么?
祥林嫂的“活物”乃至死亡,愛姑從抗爭到順從,層層遞進地說明了封建意識、封建倫理道德對下層勞動婦女的迫害和封建思想的殘酷性。對于下層勞動婦女來說,被壓迫、被損害直至死亡是他們唯一的生存方式,逆來順受至死或先化掉抗爭而順從至死,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社會環境中,女性的悲劇是必然的結果。祥林嫂和愛姑,給我們展示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女性的絕望,女性的無路可走,活著無意義,是一個時代和社會的大悲劇,透過這層悲劇和絕望則是魯迅的“絕望的反抗”的精神內核。
四、絕望的反抗
絕望的反抗既是魯迅小說的主題升華,同時也是魯迅內在復雜精神世界的集中展現。祥林嫂們的死亡以及走向死亡的過程被詳細且一針見血地剖析,讓小說文本呈現出了濃烈的絕望,而這種絕望的描述的細節化的呈現則是魯迅藏于文本絕望背后的復雜的思想呈現,即反抗。與《故鄉》中結尾之處的“路”的意象,以及《藥》中“紅白相間的花圈”所呈現的希望不同,“路”和“紅白相間的花圈”與其說是希望,不如說是魯迅給予自己以及讀者的心理安慰,是緩解苦悶和絕望的,有一種聊勝于無的感覺;而《祝福》《離婚》中的絕望書寫,是冷靜克制的,字字句句詳細刻畫的細節是對絕望的有力剖析,剖析得越細致,越是對絕望的有力撕扯和解剖,即越細節則越有力,反抗則越徹底。
《祝福》中面對祥林嫂的問題,“我”含糊不清的回答以及落荒而逃的選擇,是“我”的無能為力,卻是魯迅的清醒的意識書寫,“我”無法給祥林嫂以希望,是魯迅對祥林嫂所生活的社會的清醒認知,祥林嫂的死亡,讓“我”決計離開,“我”的“負罪”逃離,恰恰是魯迅在靈魂深處的剖析,“魯迅的反抗絕望是不斷地刺痛自己的靈魂,把靈魂深處的痛苦、絕望、無助做無情的解剖”④。《祝福》中無法給出祥林嫂答案的“我”,其實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圍的一員,他們作為看客,審視旁觀著祥林嫂的人生和命運,圍觀咀嚼祥林嫂悲慘的生活,那陪出的很多眼淚,那特意尋來的行為,那嘆息,那滿足,后來那煩厭的頭疼,無不是魯迅對絕望的力透紙背的描寫和深入靈魂深處的無情剖析。“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⑤《離婚》中的愛姑,走在最后的愛姑的溫和回答,是《離婚》的最大悲劇,魯迅呈現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變得溫順的愛姑未來會怎樣呢?這是留在讀者心中的問題,而答案幾乎呼之欲出:過上祥林嫂甚至還不如祥林嫂的生活,被迫再嫁,成為別人茶余飯后的談資,然后死亡,這個看似開放性的結局,其實結果是唯一的。愛姑的變化是小說深沉的悲劇性的體現,小說最后用看似溫和的筆觸對愛姑溫順的描寫,呈現出了愛姑貌似從婚姻的泥沼中解脫出來的假象,是魯迅對愛姑內心感受的留白。若愛姑的溫順是真的溫順,那她的未來必然是祥林嫂;若愛姑的溫順是對人生體驗過后的絕望,是對自己人生命運的絕望,那便是魯迅對時代、對社會、對人生和人性的深入剖析,呈現的依然是魯迅絕望的反抗,“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絕望無處不在,希望正渺茫,希望的渺茫也正是絕望的渺茫。
從《祝福》到《離婚》,我們可以清晰地理解魯迅的思想,魯迅的反抗,深入剖析,直擊靈魂,在靈魂深處透出反抗的力量。魯迅對社會底層勞動婦女的命運書寫實際呈現的是魯迅對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深入窺探,是對人生、對人性的靈魂表達。魯迅對女性的書寫實際是對社會的剖析,祥林嫂的順從是悲劇,愛姑的抗爭也是悲劇,那女性該怎么辦?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提出,“錢是要緊的”,“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⑥。魯迅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和書寫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療救的目的上,揭開女性精神和靈魂的病苦,進而引起對女性療救的注意,而療救的目標實現,最終指向的還是整個社會,因此,最終揭出的是造成女性精神病態的社會。于是,社會改革,勢在必行,“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⑦。
注釋:
①魯迅:《我之節烈觀》,載《墳》,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②同上書。
③段從學:《〈祝福〉:“祥林嫂之問”與“魯迅思想”的發生》,《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④臧振東:《從〈故鄉〉到〈祝福〉:魯迅“第二次絕望”的小說呈現》,《名作欣賞》2021年第23期。
⑤魯迅:《娜拉走后怎樣》,載《墳》,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⑥同上書。
⑦同上書。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郜元寶.魯迅小說第一人稱敘述綜論(三)[J].小說評論,2022(03):13-18.
[3]高家鵬.魯迅小說中的“人,回不去”思想[J].魯迅研究月刊,2022(04):70-77.
[4]朱玉川.場域轉換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視域下的魯迅小說《離婚》[J].名作欣賞,2021(11):89-92.
[5]林雅慧,史揮戈.性別語言差異與魯迅小說中的女性表述——以《祝福》《明天》《離婚》為例[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5(03):155-159.
[6]李明軍.文化蒙蔽:魯迅小說中女性形象的精神桎梏[J].魯迅研究月刊,2004(07):75-80.
作者簡介:
侯慧慶(1979-),女,遵義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