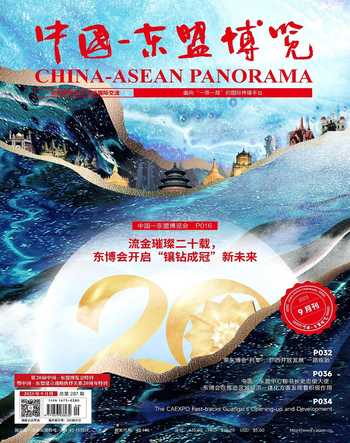外商直接投資助推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
喬治·甘巴 馬可·王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攜手共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此后十年,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互聯互通不斷加強,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經貿聯系日益鞏固。2020年,東盟一舉超越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標志著區域經貿合作新格局的正式形成;2022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中國—東盟雙方貿易額同比增長15%。
隨著中國—東盟伙伴關系從貿易向其他領域不斷深化拓展,人們期待在東盟市場看到更多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為命運與共的未來開耕播種。
作為當今世上發展最為迅速的兩大經濟體,中國和東盟在產業結構上具有極強的互補性。
東南亞地區擁有強大的制造能力和生產能力,地區內年輕消費群體日益龐大,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貿易和資本流動日益頻繁,數字化轉型持續推進,發展不斷向可持續邁進,凡此種種都給該地區帶來了巨大機遇。
全新生產基地
中國式現代化經濟是以穩定的初級制造業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中國也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通過大力生產高科技產品,提供高科技服務,同時加大研發投資,中國自身得到不斷發展,并向價值鏈高端躍升,而中國一些科技含量較低、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或將成為東南亞各國競相爭取的“香餑餑”。
其中,紡織服裝業最有可能轉移至其他亞洲國家。另外,隨著泰國、越南和印尼等國承接電子產業,中間產品和其他科技產業也在相繼轉移。
當下,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努力探尋地域多樣化經營,同時紛紛采取“中國+1”的生產戰略,東南亞的市場份額將持續擴大。與此同時,在全球制造業重心持續轉移的背景之下,更多的全球FDI將流向該地區。
2021年,流入東盟國家的FDI上升至全球總量的11%,創下歷史新高,幾乎與中國12%的全球FDI占比持平。同年,中國成為東盟最大的FDI來源國(東盟內部不計入該范圍),與日本并駕齊驅。盡管投資進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有所中斷,但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在疫情防控放開后將持續蓬勃發展。
2022年,中國在東盟的FDI項目大多集中在目的國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上。多年來,中國一直大力投資東盟各國發展勢頭強勁的制造業,從印尼和泰國的電動汽車供應鏈,到越南的電子產品,再到新加坡前景光明的制藥產業,隨處可見中國投資商的影子。
以中國領先電動汽車制造商比亞迪為例,該企業已著手在泰國打造年產能為15萬輛汽車的生產中心。泰國之所以成為比亞迪在東南亞的首個生產中心,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該國政府為每輛車提供高達15萬泰銖(約合3.1萬元人民幣)的購買補貼。
然而,泰國并非中國在電動汽車供應鏈上唯一的FDI目的地。中資企業同樣助推了印尼鎳冶煉廠的發展,而鎳的供應穩定對電動汽車電池的生產至關重要。作為全球最大電動汽車電池制造商,中國寧德時代與印尼國有礦業公司ANTAM和電池公司IBI簽署三方協議,共同打造從鎳礦開采到電池制造的動力電池產業鏈項目,該項目價值將近60億美元。
中國太陽能企業東方日升也公布了其在東南亞的首個生產設施投資。該公司將在馬來西亞制造高效太陽能光伏組件,未來15年內投資至少約100億美元。
此外,中資企業在新加坡的投資同樣熱火朝天。2022年底,無錫藥明生物和藥明康德同時宣布在新加坡制藥行業分別投資約20億新加坡元(約合107億元人民幣)。
提高生產效率
遍布亞洲的供應鏈已讓中國周邊的國家和地區在生產和產能上實現了質的飛躍。
源源不斷的投資,合作伙伴關系的確立,以及包括RCEP在內的貿易協定的簽訂,都可能給東南亞地區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從而與中國共享發展新機遇。
即便如此,為吸引更多全球制造商,保持市場競爭力,東南亞國家還需進一步提高自身生產效率。
過去幾年里,盡管全球經濟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影之下,同時深受其他市場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但我們依然能看到東南亞地區未來幾年內光明的發展前景,無論是可持續發展和數字科技進步,亦或是經貿往來和財富增長,一切都蘊藏著無限潛能。
這些也為中國企業在后疫情時代尋求持續增長、擴大全球影響力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開啟機遇之門的關鍵不僅僅在于掌握各領域的市場動態,還在于實現跨界企業的聯系與合作。從泰國的汽車行業和馬來西亞的電子制造業,到印尼的自然資源開發業和新加坡的制藥業、金融服務業,都需要有機聯系、緊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