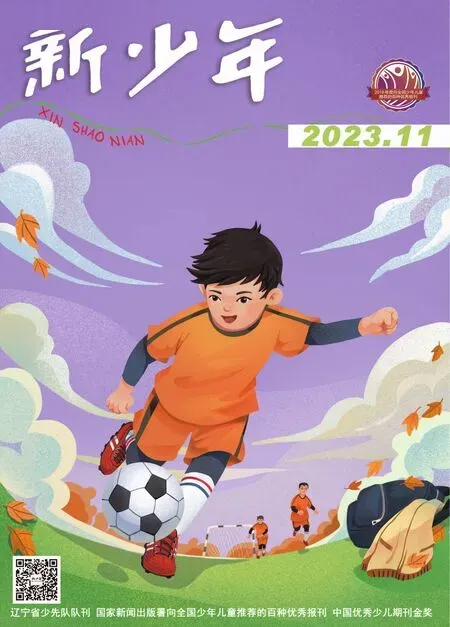藏在收音機里的童年
李仙云 文 剛子 圖
每每憶起童年的“戲匣子”,猶如徐徐打開了一本老相冊,往昔歲月里的一幕幕舊事浮現眼前,凝神回溯間不由得微微一笑。
小時候,不管與小伙伴玩兒得多歡暢,只要一聽到“嗒嘀嗒,嗒嘀嗒,嗒嗒——小朋友,小喇叭節目開始廣播啦!”我們立刻像回籠的鳥兒,靜悄悄地坐在收音機旁,有滋有味地聽孫敬修爺爺講《西游記》。每每聽完,還覺得不過癮,便用“過家家”的方式開始演繹“經典名著”。可是挑來選去,任誰也不愿意扮豬八戒。一次讓萍萍當白骨精,氣得她噘嘴就走,一個星期都不和我們玩兒。
在小喇叭節目里,我第一次聽到安徒生的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那凄涼悲慘的畫面,渲染了季節的寒冷,冬日望著屋檐下吊著的一串串晶瑩剔透的冰凌,童年的我,內心被一種酸楚與寒涼包裹,竟抽抽搭搭啜泣了好一會兒,引得姐姐笑我像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一樣。
小時候,大人們常聚于我家的庭院或巷頭,女人們手底下一邊忙著針線活兒,一邊興趣盎然地聽收音機里播放的秦腔。男人們則一邊咂巴著旱煙鍋子,一邊搖頭晃腦跟唱,聽到熱血沸騰時,就激動地站起來提袍甩袖,吹胡子瞪眼聲情并茂地唱幾句,有時走腔跑調常惹得大伙兒笑岔氣。母親那時最喜歡聽《花亭相會》和《三娘教子》,每當我任性倔強遭母親“修理”時,隨口總會扔出狠話刺傷她,母親就用三娘的口吻怒斥:“你真是人兒小來心兒惡,說出話來賽毒藥,平時白疼你了。”
爺爺田間勞作歸來,擰開收音機,一段《周仁回府》聽完,從心胸肺腑到四肢百骸,渾身的疲乏一掃而盡。難怪賈平凹先生說,秦腔是秦人大苦中的大樂。這集秦川“天籟、人籟、地籟”共鳴的劇種,就是在童年通過收音機,把鄉情鄉音的種子播進了我的心田,讓遠離故鄉千里之外的我,每每耳畔響起秦腔,就心潮起伏熱血沸騰。
當年,我曾跟隨當警察的父親生活在陜北一偏僻的山溝溝,恰是收音機,給我們單調得讓人抓狂的年少時光,增添了許多繽紛絢爛的色彩。每次中午放學鈴一響,我們像亟待出欄的羊群,拔腿就往家奔,顧不得填充饑腸轆轆的肚子,擰開收音機就側耳靜聽。印象最深的是風靡一時由王剛播講的《夜幕下的哈爾濱》,那曲折驚險的故事,在他抑揚頓挫、極富感染力的播講中,把大家的心揪扯得連午飯都食之無味,盡替主人公命運的跌宕起伏擔憂了。
往事悠悠,正是早期收音機播放的那些優秀的文學作品,為我的遐思遨游文學的碧空插上了翅膀,讓我把世情百態酣暢傾訴。時光飛逝,當青春漸行漸遠,童年往事也變得如同夢境,但每一次回眸往昔,那些裊裊輕音就在心間回旋激蕩,讓滄桑歲月也多了幾許朦朧詩意,暖心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