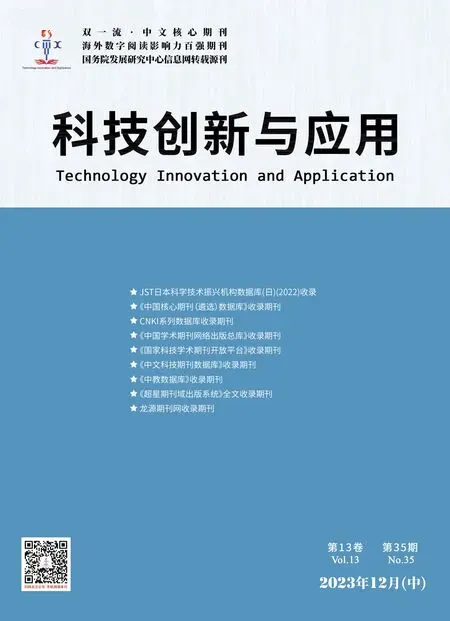苗尾水電站庫區滑坡地表變形及成因機制分析
陳 梁
(華東勘測設計院(福建)有限公司,福州 350003)
隨著我國西南地區水利工程的發展,水庫的大量建設不僅帶動了區域國民經濟發展,還大大緩解了電力緊張局面[1]。但水庫的建設也會增加一定的風險,水庫在蓄水發電過程中,隨著水位的提升,容易誘發地震與滑坡。
國內外學者對水庫區域的滑坡及地震進行了大量研究[2-4]。研究發現,水電站庫區的地勢一般較為陡峭,其庫區邊坡較多,加上降雨充沛等原因,容易導致邊坡失穩。許振棟等[5]對福建水口水庫區域的水庫誘發地震序列以及活動特征進行大量分析,對庫區最大誘發地震進行了預測。張楠等[6]查閱大量文獻,分析了水-巖相互作用、水位驟降時的空隙水壓力對庫區穩定性的影響,總結出庫水位上升過程中的水庫誘發滑坡形成機理。唐鳳嬌等[7]對水電站區域的25 個歷史水庫蓄水誘發滑坡進行了規律性研究,結果表明水庫誘發滑坡的主控因素為距死水位距離和高程,高程1 km 以下和距死水位400 m 以內的范圍內容易誘發滑坡。張保軍等[8]通過對水庫蓄水期間水庫庫岸穩定性監測,對岸區邊坡裂縫、溶洞、斷層滲透與地震誘發滑坡進行關聯性評估,結果表明,地震次生災害作用直接導致滑坡發生。鄭海益等[9]利用三維建模對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庫區滑坡體進行成因分析,結果表明水庫蓄水后導致松散邊坡浸沒于水中,水浸潤到邊坡土體后會導致土體內摩擦角降低,再加上庫水的托浮作用,最終誘發邊坡滑動失穩。
本文中案例滑坡區域內無居民,但滑坡體對岸居民點較多,且右岸過境公路由滑坡體中下部通過,道路開挖對滑坡體的穩定有一定影響。因此對滑坡成因機制進行了相關研究,對滑坡體進行穩定性評價。對庫區滑坡治理及預防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 研究區概況
苗尾水電站庫區河道呈不對稱的“V”型狹谷與“U”型寬谷相間分布,兩岸坡度一般為25~50°。水庫區分布有Ⅰ~Ⅳ級階地,庫內岸坡分布多個滑坡體、傾倒變形體、崩塌堆積體和泥石流堆積物等物理地質作用[10]。
其中馬拉滑坡位于瀾滄江右岸支流瓦窯河與阿馬拉河之間庫段,山前凹形斜坡內,距壩址約40.5 km,如圖1所示。

圖1 滑坡區域地形地貌圖
滑坡區對岸有居民區存在,區域地貌為瀾滄江河流堆積階地,地形坡度10~20°,分布高程為1 400~1 500 m。其中1 400~1 430 m 高程為瀾滄江II 級河流階地,階地前緣為陡坎,江邊基巖出露,階地上分布少量民房;1 430~1 500 m 高程為瀾滄江III 級河流階地,上覆少量泥石流堆積物,核桃坪小組居民位于III 級階地中后部,最低分布高程1 455 m 左右。
2 地質及水文條件
2.1 地形地貌
滑坡區基巖為侏羅系花開左組(J2h2)紫紅色、灰綠色板巖,傾倒較強烈。滑坡區一般坡度20~40°,滑坡體主要由碎石土組成,分布于1 650~1 408 m 高程。滑坡體下部為較破碎的基巖邊坡,六庫至蘭坪的縣級公路由1 407~1 409 m 通過。
2.2 地層巖性
場地基巖為侏羅系中統、上統地層,巖性為壩注路組(J3b)紫紅色泥巖、粉砂質泥巖、板巖及花開左組紫紅色、灰綠色板巖[11]。上部覆蓋層主要有崩坡積含碎石粉質黏土層,其中碎石母巖成分多為板巖、少量砂巖,勘探鉆孔揭示其厚度一般在2~9 m;Qdel滑坡堆積物多為假基巖,局部可見原巖體結構特征,厚度一般在30~70 m,上游側及堆積體后部略薄,下游側及堆積體前部略厚。
2.3 地質構造
場地內無活動斷裂分布,但近場區40 km 范圍內自有記錄以來,多次發生地震活動。現代地震震源深度均小于20 km,主要分布深度為5~20 km。根據規范及相關規定,本區抗震設防烈度為7 度,抗震分組為第三組,場地區基本地震加速度為0.15 g。場地區內無活動斷裂分布。
2.4 水文地質條件
區域內無地表徑流,岸坡三面臨空,不利于地下水的賦存,地下水類型主要為基巖裂隙水,賦存于基巖巖體結構面中,主要受大氣降水補給,向瀾滄江河谷排泄。勘探鉆孔揭示,岸坡地下水埋藏較深,近河谷段基本與江水位持平,區內未見地表徑流及地下水出露點。
3 地表變形及監測
地表變形與檢測是判斷滑坡發展階段及預測滑坡發展趨勢的基礎,也是滑坡穩定性復核的重要內容之一。
3.1 裂縫分布特征
上游側邊界裂縫的出現主要集中在高程1 530~1 570 m 的側陡坎邊,呈拉張裂縫,深度約30~60 m。下游側邊界裂縫主要集中在高程斜坡與平臺上,宏觀表現為寬度較窄、深度較淺的橫向拉裂縫。滑坡體前緣裂縫早期已局部貫通,自下游側邊界至河邊陡坎延伸約100 m,張開度約5~15 cm。而滑坡的后緣裂縫平主要集中在高程平臺,深度最高達到了3 m。剖面均呈弧形,顯張性力學性質。下游側邊界裂縫最先出現,隨后后緣裂縫、上游側邊界裂縫依次出現,地表裂縫發育部位主要位于古滑坡周界處。
3.2 滑坡剪切口分析
滑坡體上游側邊界開挖揭露古滑面,可見明顯擦痕,滑面的上盤為碎石土,下盤為傾倒變形巖體。前緣剪出口的上盤為滑坡堆積碎石混合土,下盤為傾倒變形板巖。
3.3 變形監測結果
地表監測主要為滑坡體周界內的6 個監測點(編號TP-H6-2、3、4、6、7、8)蓄水后出現變形,滑坡體周界外的2 個監測點(編號TP-H6-1、TP-H6-5)蓄水后未出現變形。表觀位移檢測點設置如圖2 所示,監測頻率為一周一次。

圖2 滑坡體表觀位移監測點布置圖
各表觀監測點的平面變形方向基本一致,見表1,即垂直河流方向(略偏下游);垂直位移均為沉降。以水平位移為主的監測點位于滑坡體前緣,以沉降位移為主的監測點位于滑坡體后緣及滑坡體下游側邊界附近。表觀監測數據顯示坡體的變形特征(坡體變形方向、裂縫發育的先后順序、裂縫張開寬度)與地表裂縫發育特征吻合度較好。

表1 各監測點累計位移量匯總表mm
4 深部位移變形監測
深部變形監測利用勘探鉆孔,共計8 孔,編號:ZKH21—24、ZKH31—34。監測期間根據蓄水、降雨及變形速率變化情況適當加密觀測頻率。
在孔深27~37 m 之間,孔深33.2 m 處為軟弱夾層,巖芯破碎且呈全強風化,結合鉆孔巖芯判斷孔深33.2 m 處為滑移面。巖心細節照片如圖3 所示。孔深58.0 m 處巖芯呈全風化狀,其形狀與上游側剪出口出露滑面基本一致。部分巖心細節照片如圖4 所示,鉆孔巖芯顯示,在孔深67~77 m 之間,孔深72.2 m 處巖芯破碎且呈全強風化,礫石具有一定的磨圓度,如圖5所示。

圖3 ZKKH21 孔深33.2m 細節照片

圖4 ZKKH34 孔深58.0m 細節照片

圖5 ZKKH22 孔深72.2m 細節照片
深部變形監測的變形方向、速率、累積位移與滑坡穩定性復核緊密相關,根據監測數據判斷滑面深度,結合地面裂縫開合度監測。各監測孔潛在滑移面的深度和累積位移量見表2。

表2 各監測孔潛在滑移面深度、累積位移量
探及深部變形監測顯示,坡體現階段變形深度與古滑坡的滑面深度一致;勘探揭示老滑面前緣水平段高程位于1 401 m 高程以下,坡體出現整體變形的時間是在水庫蓄水至1 401 m 高程2 個月后。
5 成因機制分析
5.1 變形范圍
通過對變形邊坡地表裂縫分布特征的調查,結合表觀、深部位移監測數據,確定滑坡體后緣高程1 620 m,前緣高程在1 380~1 390 m 之間,順河向長約420 m,垂直河向長約350 m,滑體厚10~75 m,滑面總體形態后陡前緩,后緣滑面坡度一般在45°左右,前緣滑面坡度近水平。滑坡堆積體形態詳見地質平剖面圖按平行斷面法計算其方量約430 萬m3。
5.2 變形特征
庫水位由1 372.7 m 高程抬升至1 392.8 m 高程期間,水庫回水至滑坡體庫段附近,滑坡體前緣岸坡(下游側邊界附近)產生了一定范圍的塌岸。此時,滑坡體前緣靠近塌岸區的TP-H6-8 號表觀監測點出現平面及沉降變形。隨后庫水位繼續抬升在1 401 m 高程左右,前緣新增幾處小規模塌岸。之后,滑坡體從前緣至后緣,周界內的各表觀位移監測點相繼出現變形,此時監測點最大變形量為55 mm(TP-H6-8),該時間段大部分監測點變形速率較緩。2 個月后,滑坡周界內各表觀監測點出現加速變形,此時庫水位已穩定在1 401 m 高程且地表出現肉眼可見裂縫,結合期間連續降雨量較大的影響分析,該時間段的變形一定程度上受降雨影響。
滑坡體前部下游側變形為水平、沉降2 個方向,滑坡體后部變形以沉降為主;滑坡體前部上游側變形以水平位移為主。
5.3 原因分析
坡體現階段變形深度與古滑坡的滑面深度一致;勘探揭示老滑面前緣水平段高程位于1 401 m 高程以下,坡體出現整體變形的時間是在水庫蓄水至1 401 m高程2 個月后,滑坡周界內各表觀監測點出現加速變形,蓄水后水位上漲導致庫區附近地應力承受增加,連續降雨后土體抗剪能力減弱,且地表裂縫分布位置與古滑坡周界重合。
5.4 滑坡體穩定性評價
根據滑坡體水平錯距及塌落水庫方量分析判斷,滑坡整體失穩發生堵江的可能性很小,其失穩主要影響右岸沿江公路通行、附近的基礎設施。但考慮庫水位變化對滑坡體的穩定影響較大,建議庫水位驟升驟降速率在正常工況下不宜大于2.0 m/d,非正常工況下不宜超過1.5 m/d[12]。
6 結論
根據前期地質條件與現場滑坡體及區域地質勘察,結合檢測數據對滑坡體成因機制進行了分析,總結為以下3 點內容。
1)馬拉滑坡是以巖質為主的古滑坡,水庫蓄水至穩定的1 401 m 高程后,老滑面水平段大部分被庫水淹沒,滑帶土泡水軟化,抗剪強度降低,在滑坡堆積物重力作用下,滑坡體整體沿老滑面產生蠕變滑移。坡體產生整體變形主要原因是水庫蓄水導致古滑坡復活。
2)水庫蓄水初期岸坡前緣塌岸,滑坡體前緣監測點出現微量變形,并表現為沉降變形。故水庫塌岸是滑坡體產生變形的一個誘因。
3)地表出現裂縫后,連續降雨導致大量雨水沿裂縫下滲,滑帶土體泡水軟化,抗剪強度降低。邊坡變形不斷加劇,裂縫向深部擴展,邊坡發生較大范圍變形。滑坡堆積體沿老滑面產生整體蠕變滑移,隨后變形一直不能收斂。分析認為,連續降雨是加劇滑坡體變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