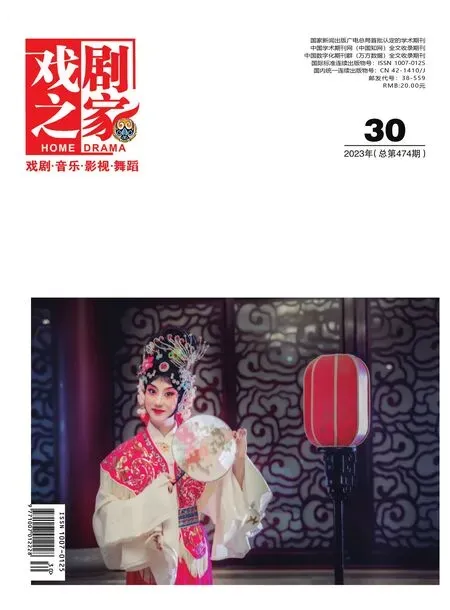明傳奇《西樓記》藝術(shù)特色評述
周婕殷
(上海戲劇學(xué)院 上海 200040)
中國古代戲曲多“簸弄風(fēng)月,陶寫性情”,為劇作家心志的發(fā)抒。明末戲曲家袁于令(1592—1674)系“寧協(xié)律而詞不工”的“吳江派”,但他的戲曲創(chuàng)作十分重視關(guān)目排場和語言的戲劇性。其代表作有《雙鶯傳》和《西樓記》等,《西樓記》尤其具有特殊意義。
《西樓記》敘寫世家公子與青樓女子的愛情故事。與明傳奇慣常的以舊題材改寫的創(chuàng)作不同的是,它取材自他的親身經(jīng)歷。祁彪佳《遠(yuǎn)山堂曲品》將它推為“逸品”,并在其中談到:“傳青樓者多矣,自《西樓》一出,而《繡襦》《霞箋》皆拜下風(fēng)。”①潘之恒《曲話》亦以五闋樂府細(xì)數(shù)《西樓記》之亮點(diǎn)。明中晚期的文壇,在陽明心學(xué)和李贄“異端”思想的滲透下,士大夫和文人墨客紛紛推崇“獨(dú)抒性靈”觀,提倡至情率性。袁于令亦曾表示對公安派的嘉賞。②本文從“主情”“寫真”和“奇構(gòu)”三方面切入,評述《西樓記》的藝術(shù)特色,管窺他受“性靈派”思潮的影響的表現(xiàn)。
一、主“情”
“主情說”是明代的主要審美思潮之一,湯顯祖、袁于令和潘之恒等都持有“主情說”。如果說《牡丹亭》是從女性視角展現(xiàn)劇作家的浪漫情懷和對理想的追求,那么《西樓記》則是透過男性視角書寫的愛情贊歌。不過,《檢課》一出頗似《閨塾》,而《錯(cuò)夢》常被研究者與《驚夢》相提并論。在昆曲《玩箋》的舞臺演繹中,“憨”“癡”的于叔夜,與《拾畫》的柳夢梅恍若一人。由此可見袁于令對《牡丹亭》作者湯顯祖的崇拜。
關(guān)于《西樓記》的主情,祁彪佳認(rèn)為《西樓記》“寫情之至,亦極情之變”。張岱亦在《答袁籜庵》中評它道:“皆是情理所有,何嘗不熱鬧,何嘗不出奇”,且認(rèn)為這是“文章入妙之處”。《西樓記》中對男主角的刻畫濃墨重彩,其情感之誠力透紙背。男主角于叔夜有情趣、恃才傲物,自負(fù)擅音律(魏晉音樂理論家嵇康的字也是“叔夜”)。他渴望知音,《私契》中【黃鶯兒】的“語兒曹,陽春古奏,和者甚寥寥”可見一斑。很快,知己出現(xiàn)了。《錯(cuò)夢》中的“花箋鐘王妙楷,晶晶可羨。羨殺你素指輕盈能寫怨”,點(diǎn)明了他對素薇才情的贊賞和內(nèi)心情竇初開的狀態(tài)。《疑謎》《錯(cuò)夢》和《泣試》幾出都聚焦于鋪陳于叔夜的深情。《離魂》中他“搖搖神思,莫不是三魂七魄早離肢體”,有杜麗娘和張倩女的癡態(tài);《泣試》中他道:“若得穆素薇為妻,即終身乞丐,亦所甘心;不得穆素薇為妻,雖指日公卿,非吾愿也。”一得知素薇死訊即哀傷過度,無心科考。
而穆素薇,一個(gè)在復(fù)雜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煙花女子,卻執(zhí)著于追尋真愛。縱觀中國戲曲史,一眾青樓女子從唐傳奇走出,到宋元南戲、雜劇,再到明傳奇……匯聚成一道獨(dú)特的景觀。她們意趣各異:有的秀外慧中、有的潑辣干練、有的俊雅德耀……而穆素薇則驕傲柔韌。她屢次抗拒財(cái)大勢大的池公子,也未委身于青年豪杰胥表。在《衛(wèi)行》中,胥長公從水陸道場將她救出后,為測試她是否堅(jiān)貞假意誘惑她,但素薇毫不松懈。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種“貞節(jié)崇拜”是父權(quán)社會(huì)意識形態(tài)在她身上的內(nèi)化。堅(jiān)貞也是“愛情信仰”的一種本能反應(yīng)。真愛無形,當(dāng)事人如果沒有行動(dòng),“真愛”將何以體現(xiàn)?大致如心理學(xué)家弗洛姆所說,愛不僅是對象問題,還透著理性與責(zé)任。
不過劇中的穆素薇還缺些“風(fēng)塵感”。初見叔夜時(shí),她發(fā)起“尊庚”“曾娶否”“曾聘否”的三連問,直言“情之所投,愿同衾穴”,這種落落大方的談吐使她不像妓女,倒像敢為愛情私奔的紅拂女。該劇是血?dú)夥絼偟那嗄暝诹睥鬯鶎懀@種“錯(cuò)筆”大概受劇作家自身經(jīng)歷影響,以致對女主角產(chǎn)生“暈輪效應(yīng)”,難免認(rèn)為穆素薇是完美的女性形象。
陳多先生認(rèn)為,袁于令對男主角的刻畫較細(xì)膩,而寫女主角的戲多為套話,沒能寫好。④這種現(xiàn)象的確存在。鑒于該劇中女性形象的刻畫以服務(wù)于男主角的塑造為主,女主角不似杜麗娘那樣主動(dòng),也是合情合理。在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古代,教坊樂伎出身的穆素薇迥異于官宦子弟杜麗娘,才情再出眾也無法改變她的身份認(rèn)同。為此,等不到于叔夜來赴約的她沒有過度悲傷的反應(yīng),用“紅顏?zhàn)怨哦啾∶驏|風(fēng)怨落花”“一泓秋水金星硯,半幅寒云玉版箋”等堆砌亦屬正常,折射出她深知自己無力對抗封建禮教的通透。
二、寫“真”
“求真”是晚明文學(xué)思潮之一,徐渭提出“摹情彌真則動(dòng)人彌易”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口號。袁于令則談道:“蓋劇場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以劇場假而情真……倘演者不真,則觀者之精神不動(dòng);然作者不真,則演者之精神不靈。”⑤袁理解的“真”有兩層含義:一是寫實(shí)的“真”,二是一種“真實(shí)感”,前者是訴諸大眾接受層面的“真”,后者是觸動(dòng)精英心靈的“真實(shí)感”。他的《西樓記》也被譽(yù)為晚明社會(huì)的風(fēng)俗畫卷。以下將從“行為”“場景”和“語言”三方面論述它的“真”。
1.行為之真。在昆曲舞臺上,《西樓記》流傳最廣的是《樓會(huì)》和《玩箋》兩折(劇本中合為《錯(cuò)夢》)。《玩箋》的賓白和科介很有《拾畫》《叫畫》的影子。不同的是,柳夢梅把玩的是杜麗娘的肖像畫,一種對人物做具象化的意象;于叔夜玩味的則是穆素薇寫的《楚江情》花箋,一種抽象化的意象,這兩種意象各具傳神的功效。
在《玩箋》表演的舞臺上,病懨懨小生的一系列動(dòng)作,如“[虛空模擬]”“[虛空做摟抱介]假抱腰肢定肩。依稀香氣鬢云邊。”“[做低唱介]心肝,悄叫一聲。似聞嬌喘。”看似低俗,但是放在二人愛而不得的背景下,“低俗”“輕佻”中包含的“真”更觸動(dòng)觀眾神經(jīng)。在《錯(cuò)夢》中,叔夜夢見自己遭鴇母和丫鬟怠慢,素薇變成“奇丑婦人”,被惡奴們?nèi)_相加,一切最后化作汪洋……陳多先生稱譽(yù)《錯(cuò)夢》與《驚夢》是明傳奇寫夢的“雙璧”。⑥盡管內(nèi)容相反——《驚夢》是魚水歡的驚喜夢,而《錯(cuò)夢》是魂魄絕的驚嚇夢。
該劇以“藝術(shù)趣味相投”為情感紐帶,而后兩人經(jīng)受住重重的愛情考驗(yàn),更契合現(xiàn)實(shí)情理。且《西樓記》中男女主角因情病危引起誤會(huì)及雙方悲痛欲絕的表現(xiàn),也是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無神化”摹寫。
2.場景之真。《西樓記》中有多處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寫照。《私契》一出中,村妓談到“我每那班彎話朋友。少不得我的弋陽曲子”“做遜介眾催唱介小凈:唱了新時(shí)曲罷。”以及“隨意將時(shí)曲一支唱作夸調(diào)介眾笑贊介”⑦……真實(shí)再現(xiàn)了“弋陽腔”“闊調(diào)”等在明代秦樓楚館大為流行的情景。
不似《霞箋記·春闈首選》中僅用“考試隨做”四字描寫考場,《西樓記·泣試》中寫到“一天星斗煥文章,諸士紛紛赴選場”“軍士擁如云。滿院朱衣。燈炬輝映。派卷分房。喊吶聲相聞”。描畫了號軍、青員、號房及斷續(xù)的喊號聲、催促交卷聲等,立體勾勒出明代科舉選場的情形。
3.語言之真。《西樓記》行文多采用能體現(xiàn)人物身份的語言,格外本色。《私契》中,詞場名家于叔夜談及填詞的要義:
〔生〕歌之所重。大要在識譜。不識譜。不能明腔。不明腔。不能落板。往往以襯字混入正音。換頭誤為犯調(diào)。攧倒曲名。參差無定。其間陰陽平仄喚押轉(zhuǎn)點(diǎn)之妙。又盡有未解者。恰才我聽歌半晌。那班少年。功夫正少。⑧
這也可以看作對湯顯祖文法的一種模仿。在《紫簫記·審音》中也有解說樂理的情節(jié)。⑨本劇的另一語言特色是感官性,即時(shí)常帶有含色欲的詞匯。在《集艷》《錯(cuò)夢》和《巫紿》等出中都不乏詼諧、逗弄之筆,村妓、老鴇和女仆楊花的言行尤為本色。如《集艷》中,為逗叔夜開懷村妓獻(xiàn)策道:
待我掐他一把。打他一下。抱住他親幾個(gè)嘴。咬他幾口。叫幾聲親肉俊心肝活寶夜明珠。……〔小旦〕老成女客這樣還魂騷。
清代董含對這種近似自然主義的寫法評道“詞品卑下,殊乏雅馴……喜縱談閨閫事,每對客淫詞穢語沖口而出,令人掩耳。”⑩其實(shí),“寫真”是作者創(chuàng)作理念的一種外化,脫離劇情談“詞品”失之偏頗。這種“寫真”性也推動(dòng)了該劇的流傳。梁廷枏《曲話》中轉(zhuǎn)引了袁于令聽轎夫嘆大戶人家里為何不唱“繡戶傳嬌語”的見聞,“繡戶傳嬌語”是《錯(cuò)夢》中的辭藻。孔尚任《桃花扇·優(yōu)選》中亦將《西樓記》作為“三大時(shí)劇”之一……可見,彼時(shí)此劇幾近家喻戶曉。
三、“奇”構(gòu)
“一線到底”“奇思巧構(gòu)”,是《西樓記》創(chuàng)作法的又一優(yōu)勝處。全劇四十出分“起承轉(zhuǎn)合”四部分——初遇、分離、生死零落、重逢。袁于令注重劇場性,注重通過演員的形體和語言去傳達(dá)性靈之美。
1.“一線到底”。清曲學(xué)家李漁有一論斷:“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認(rèn)為《荊釵記》《劉知遠(yuǎn)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之所以能傳諸后世,是由于“止為一線到底”而“無旁見側(cè)出之情”。“一線到底”的設(shè)置,縮小了觀眾的賞析范圍。從劇場接受的角度考量,該劇可算是“以雙線敘事為主”的明代愛情主題傳奇之特例。
2.“奇思巧構(gòu)”。袁于令的又一戲劇創(chuàng)作主張是“奇”。他曾贊賞王玉峰《焚香記》的關(guān)目設(shè)置:
又有幾段奇境,不可不知。其始也,落魄萊城,遇風(fēng)鑒操斧,一奇也……致兩人生而死、死而生,復(fù)有虛訃之傳,愈出愈奇。悲歡沓見,離合環(huán)生……?
臺灣地區(qū)曲學(xué)家張敬談道:“布置劇情,文武靜鬧間離,悲歡離合雜錯(cuò),自來傳奇排場之勝,無過于此。”?綜觀《西樓記》關(guān)目架構(gòu),女主角的戲份不少——“被逐、被奪、被救、被劫”,情節(jié)跌宕多變;男主角的戲則偏弱,一味地寫他相思病染。直到《錯(cuò)夢》一出才彌補(bǔ)了這一缺陷——奇幻夢境就此宕開一筆,生動(dòng)展示了叔夜郁悶、焦灼、絕望的多重心境。另外,分別寫生、旦的關(guān)目常以“情境反諷”法翻轉(zhuǎn)、交錯(cuò)前行,使敘事更順暢合理。
3.豪俠的點(diǎn)染。該劇中,袁于令借俠士之手對愛情絆腳石池同及其黨羽的嚴(yán)懲,實(shí)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shí)中情敵的報(bào)復(fù)。胥長公為兄弟施計(jì)出力,仗義舍生——貢獻(xiàn)了自己的寶馬、犧牲了愛妾,不輸虬髯客和古押衙。《俠概》《邸聚》和《衛(wèi)行》等出對胥長公形象做了詮釋。
對該劇中加入豪俠相助的做法,李調(diào)元認(rèn)為“于撮合不來時(shí),拖出一須長公,殺無罪之妾以劫人之妾為友妻,結(jié)構(gòu)至此,可謂自墜苦海。”?事實(shí)上,武俠文化在明朝十分盛行,“士為知己者死”也是當(dāng)時(shí)名士的一種價(jià)值觀,插入豪俠橋段既為《西樓記》增了幾絲浪漫色調(diào),也添了一縷歷史氣息。
四、結(jié)語
明晚期,在道學(xué)籠罩下涌動(dòng)著一股“現(xiàn)代性”價(jià)值觀的潛流。部分文人崇尚個(gè)性解放,個(gè)體情愛被賦予了神圣的價(jià)值,同時(shí),一種新的市民審美趣味應(yīng)運(yùn)而生。與西方文藝復(fù)興人文主義者強(qiáng)調(diào)自我的意識形態(tài)契合。《西樓記》以才子佳人的真才實(shí)學(xué)為愛情紐帶,雅俗并置——既有情深意遠(yuǎn),又不乏詼諧鄙俗。它主“情”、寫“真”、“奇”構(gòu),充分展示了“現(xiàn)代性”的藝術(shù)特色,不啻為明傳奇中的一抹亮色。
注釋:
①[明]祁彪佳.遠(yuǎn)山堂曲品[A].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C].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②據(jù)徐朔方先生考證,袁于令寫《西樓記》時(shí)不到20 歲。
③[美]艾里希·弗洛姆.愛的藝術(shù)[M].劉福堂,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④陳多.〈西樓記〉及其作者袁于令[J].藝術(shù)百家,1999,(01):43-53+23.
⑤[明]袁于令.焚香記·序[A].六十種曲[C].明毛晉汲古閣本。
⑥陳多.〈西樓記〉及其作者袁于令[J].藝術(shù)百家,1999,(01):43-53+23.
⑦⑧[明]毛晉.《六十種曲·西樓記》,繡刻演劇十本。
⑨[明]毛晉.《六十種曲·紫簫記》,繡刻演劇十本。
⑩[清]董含.三岡識略 卷七[M].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明]袁于令.焚香記·序[A].六十種曲[C].明毛晉汲古閣本。
?張敬.明清傳奇導(dǎo)論[M].華正書局,1985.
?[清]李調(diào)元.雨村曲話[A].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C].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