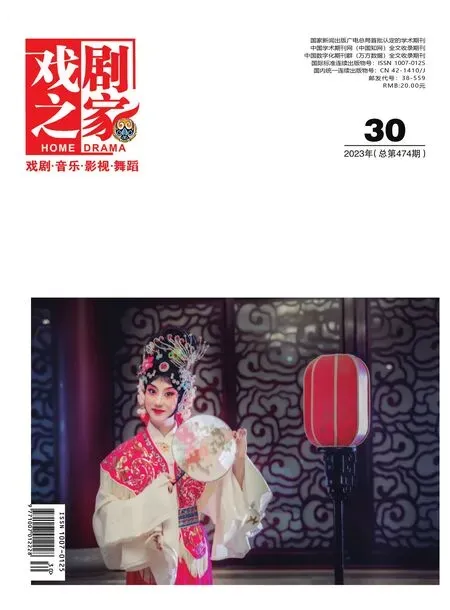以技為先,技藝統一
——再談戲曲表演中技術手段與人物體驗的關系
盛子明
(中央戲劇學院 北京 102200)
在戲曲表演藝術的探討中,向來不乏對技與藝的研究。前人基于各自的學理考辯和實踐經驗,對兩者關系和側重的說法各有不同。中國戲曲,作為一種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精髓與獨特東方美學精神的表演藝術,極其重視培養演員聲音和形體和形體兩方面技術,并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逐步完善了一套針對演員表演行之有效的訓練方法,即圍繞“功法”展開的基本功訓練,幫助演員在舞臺上實現戲劇性表達。筆者認為,受戲曲表演的獨特美學風格影響,功法構成了戲曲表演獨特的舞臺語匯,即戲曲表演不能脫離功法進行藝術表達。本研究指出,在戲曲表演中,演員首先要解決功法的技術問題,才能藝術地表達和呈現人物體驗帶來的舞臺情感。這是因為,功法是戲曲表演最基本的技術手段,而人物體驗是使功法轉化為藝術的根本手段,以戲曲表演來創作舞臺形象離不開技與藝的有機統一,本文將就此展開具體討論。
一、戲曲之根,植于功法
自20 世紀50 年代初開始的戲曲理論研究,為避免形式主義的指責,存在著與西方戲劇理論相接的趨勢,極其重視演員在戲曲表演中的人物體驗,曾出現反對戲曲表現形式的聲音①,這無疑對戲曲演員的舞臺呈現產生了巨大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反對向西方理論進行學習和借鑒,而是想說明戲曲作為一種以表演為核心的藝術,有獨特的美學特性和技術形態。因此,在戲曲的傳承和再發展中,我們首先要重視演員在表演中的技術形態,然后在此基礎上強調演員表演中的人物真實性,才能彰顯戲曲表演藝術的強大魅力。
因不同藝術的自身特性各不相同,所以其表現客觀生活的技術形態也不相同。戲曲演員在表演中通過自身所掌握的功法表現客觀生活。戲曲的功法,并不是前人藝術家們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在歷史的、社會物質生活的限制中,在無數的舞臺實踐、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一種具有鮮明虛擬性和寫意性的技術手段,戲曲演員們正是通過這種獨特的技術手段在舞臺上刻畫人物形象、展現故事情節和傳遞舞臺情感。這是因為,在戲曲早期的歷史發展中,因演出多在露天或野外進行,觀眾和演員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再加上戲班往往在多地流動演出,舞臺裝置也較為簡單。所以,為解決社會物質條件和舞臺呈現之間的矛盾,戲曲演員通過對生活進行藝術提煉,并汲取民間歌舞、武術雜技和說唱藝術等多種藝術技藝的表演因素,在舞臺實踐中不斷摸索和創造,力求既讓觀眾能看清、看懂舞臺上的表演,又能獲得愉悅的審美體驗,最終形成具有獨特民族風格和美學特征的舞臺表現形式。當這種表現形式反映在表演的技術形態上,就又形成了一套以“唱念做打”為核心、并有機結合“手眼身法步”的技術手段——功法。
綜上所述,在戲曲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國戲曲表演已經構建起以功法為主體的表演體系,并不斷豐富完善表演的手段。“戲曲運用‘四功五法’(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的表演,決定了它和其他戲劇樣式以及舞臺藝術樣式存在根本差異”②。換言之,戲曲功法的形成與戲曲源流息息相關,沒有功法就沒有中國戲曲藝術——功法構成了戲曲表演獨特的舞臺語匯,即戲曲表演不能脫離功法進行藝術表達。
二、以技求形,以神求藝
“以技求形”是指戲曲演員在舞臺上以功法為核心的表現人物形象的特殊表演技法,即“無技不成戲”。但無論戲曲的功法多么繁復和獨特,都不外乎音聲、形體兩種,即“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其中“唱念”是以聲音為媒介表現人物的技術手段,“做打”是以形體作為媒介表現人物的技術手段,二者共同構成了戲曲表演的舞臺語匯,是演員必須進行規范和訓練的四項基本功。而“手眼身法步”是演員在使用“唱念做打”時需要注意的技術要領和準則。戲曲表演功法訓練的目的,是讓演員掌握一系列外在的表現技法,使演員能夠借助于這些技法,塑造讓觀眾可觀、可聞的人物形象。
以《昭君出塞》這一折身段吃重的做工戲為例。作為尚派藝術的代表劇目,盡管這折戲只有半小時,但尚小云先生幾乎將旦角所有的步法都融入了表演中,同時,他的表演還吸收了大量的武生身段,充分反映了尚派濃烈、豪放的藝術風格,提升了該折戲的藝術境界。例如,在表現昭君文場別宮門上場時,尚先生巧妙地使用了“壓步”,上身極其穩定,行進過程中不晃不顛,既生動呈現了王昭君莊重的神情,又體現出她離別前不舍家鄉的凄然和無奈;再如,當昭君出塞乘馬時,馬夫恭敬請昭君上馬,昭君先是原地望馬,緊接著又急速扭過臉背對馬匹,緩緩起“云手”,慢慢拉“山膀”,隨后退至臺中,猛然一個朝天大投袖,一連串的動作行云流水,顯露出其嫻熟的功法;隨后,隨著不斷變化的打擊樂節奏,尚先生又使用“趟馬”“圓場”“腕花云手”“鷂子翻身”等功法,生動形象地展現了王昭君在出塞時與烈馬周旋的場景。尚小云曾說:“演昭君,好比畫幅活的美人圖,只有練就真功夫,才有可能把昭君這位古代有名的美女‘畫’得美上加美。否則,想象再美,扮相再好,到了臺上笨手笨腳,出乖露丑,那比毛延壽一筆點破美人圖還要糟糕。”③可見,成功塑造王昭君這一形象離不開扎實的功法。由此及彼,戲曲演員只有以功法為核心展開系統、規范的訓練,才能在舞臺上呈現出鮮活靈動又準確貼切的表演,最終實現人物形象的塑造。
但倘若戲曲表演僅僅停留在展現外在的形式美和技術美,也不足以被稱之為藝術。傳統戲曲藝諺有“神不到,戲不妙”之言,又有“要能傳神,才是活人”的說法,這里的“神”包含了人物精神生活和心理狀態的全部內容。實際上,任何表演藝術家在進行藝術表達時,都追求表現人物的“神”,戲曲也不例外。而戲曲演員正是通過攝取人物之“神”,將其表演上升至藝術層面,即“以神求藝”。毋庸置疑的是,為了在舞臺上呈現人物之“神”,演員就必須在深入研究劇本的基礎上,細膩、深刻地了解所飾角色。徐大椿在《樂府傳聲·曲情》中言道:“必唱者先設身處地,摹仿其人之性情氣象,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語,然后其形容逼真,使聽者心會神怡,若親對其人,而忘其為度曲矣。”④這里所說的“設身處地”,便是指演員要站在角色的角度感受和思索人物及其所處環境,將自身與角色緊密聯系在一起,對“性情氣象”展開創造性的想象,產生強大的信念感,才能在自己的心靈中體驗人物的思想情感,進而做到“自述其語”。
梅蘭芳先生之所以是世人景仰的戲曲藝術家,不僅在于其高超的舞臺表現技術,還在于他在表演中對劇中人物的深刻體驗和把握。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奇雙會》是梅先生常演的劇目,在此之前,很多演員在表演此戲時常常在表演上片面地追求喜劇效果,扭曲了李桂枝的性格,破壞了戲劇的主題。但梅先生在演出此戲時,立足于展現戲劇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思想的變化,將李桂枝塑造得更加豐滿、合理。例如“寫狀”一場,我們可以通過梅先生的面部神情看到李桂枝因父含冤而產生的哀愁與痛楚;當趙寵歸來,李桂枝又立即收起愁容,笑臉相迎,雖是笑了,但我們仍從梅先生的表演中看到其眉間依然縈繞著難耐的苦楚——李桂枝實在無法壓抑心中巨大的痛苦,所以和夫君寒暄過后便傷心哭了起來。在這場戲中,梅先生正是通過對情境的把握和對人物的體驗,才能生動地表現出李桂枝豐富又復雜的心理活動。因此,戲曲演員為了更好地在舞臺上呈現角色,必須立足于劇本情境的發展,不斷剖析人物豐富的內心活動,在人物體驗上下足功夫,獲得人物之“神”,才能成就真正的戲曲藝術。
從以上敘述可知,嫻熟運用功法是演員戲曲表演的基礎,而演員對人物的體驗是成就戲曲表演藝術的先決條件。因此,“以技求形”和“以神求藝”共同形成了戲曲表演中戲劇性表達的前提。
三、技藝結合,形神兼備
如上文所述,我們強調中國戲曲獨有的功法是中國傳統戲曲表演體系最重要的基礎,同時還強調了演員要重視人物體驗在戲曲表演中的重要意義,才能真正地成就戲曲藝術。張庚先生在談中國戲曲時曾說:“它既是一種體驗的藝術又是一種表現的藝術。它不光是體驗,還有表現,它不光是表現,又有體驗,兩者相互補充。就是說它又有內心又有外形。”⑤因此,在戲曲藝術的傳承和發展過程中,我們要將技術手段和人物體驗結合在一起,才能實現中國傳統美學追求的“形神兼備”。
“形由神生,神賴形立;形不開神不現,神不真形不活”。⑥實際上,“形”與“神”向來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形”作為一種藝術規范化的象征符號,是戲曲藝術家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在長期舞臺實踐中創造出的、表現各類人物的手段。因此,“形”是從表現簡單生活到表現復雜生活的長期藝術實踐的結果。同時,在戲曲表演中,需要通過功法才能展現“形”,即“神”的體現需要演員以“形”為物質載體在舞臺上進行表演,將抽象的“神”轉化為具象的“形”,使表達變得生動、鮮活,才能使觀眾看到人物的內心情感與精神世界。阿甲在《生活的真實和戲曲表演藝術的真實》一文中,用洪深客串《問樵鬧府》“書房”一場的失敗演出作為例子,指出我們在戲曲表演中不能因為使用技術手段而脫離人物體驗,也不能只一味強調人物體驗而忽視合理規范地使用技術手段。⑦所有出色的戲曲表演均是建立在高超的技術和精妙的體驗之上的。
如何完美地將戲曲的技術手段和人物體驗進行有機整合是所有戲曲演員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這是因為,在戲曲表演中的人物體驗具有特殊性——戲曲作為一種將歌舞和表演結合在一起的表演藝術,演員在表演中的人物體驗必須受到外部表現形式的制約,即演員要將自己體驗到的人物情感和精神世界進行外部形式的技術化表現。當然,戲曲是歷代戲曲藝術家借助功法表現人物體驗和形象思維的藝術,所有戲曲表演藝術家都有自己獨特的藝術手段,當藝術家將功法運用至爐火純青的境界后,功法會成為他們塑造人物形象、傳遞人物情感的“第二天性”——這些以功法為核心的技術手段不但凝結著藝術家對人物的體驗,還是他們成功刻畫藝術形象的技術保障。
《貴妃醉酒》是梅派最經典、最杰出的一部歌舞并重的傳統戲,而這出戲之所以能夠廣為流傳,離不開梅蘭芳先生的加工與藝術創造。梅蘭芳先生在這出戲的演出中,通過牢牢把握特定的戲劇情境,并在表演中高度融合技術手段與人物體驗,進而生動地刻畫出楊貴妃的形貌神采。在這折戲中,梅先生通過表現楊貴妃三次飲酒的場景,細膩地表現出楊貴妃不斷發展的內心變化。第一次飲酒,楊貴妃因聽說唐明皇轉駕西宮而苦悶,梅先生此刻的表演通過左手持杯,右手持扇,遮杯緩緩飲酒,既表現出貴妃心中的苦悶,又表現出她擔心宮人竊笑的強作姿態;第二次飲酒,貴妃因想起唐明皇與梅妃便心生醋意,于是這次飲酒比初次飲酒稍顯快了些,也不太注意用扇遮擋酒杯,與此同時,其眼神中還顯露些許怨恨;第三次飲酒,梅先生靈動地表現了一個不勝酒力的楊貴妃,難以自制,于是面露笑意,顧不得遮扇,將酒一飲而盡。由此,我們看到梅先生通過對楊貴妃三次飲酒的刻畫,創造出一個栩栩如生的醉美人形象,惟妙惟肖地揭示了楊貴妃苦悶無奈的心靈世界,梅先生用其精確、細膩的表演,完美地體現了人物之“神”。阿甲先生指出,戲曲演員要將戲曲功法訓練到筋肉仿佛有思想般敏銳,并將所有的心理活動融入筋肉與骨架中。⑧梅先生在《貴妃醉酒》中的表演,無疑將高超的技術精通自如地化入演員對人物的微妙體驗中,將戲曲獨有的舞臺語匯與人物的神情意態乃至精神氣質完美統一,進而達到“形神兼備”的藝術境地。
戲曲表演藝術需要演員具備高超的技術,也需要演員進行深刻的人物體驗。但“形似將跨門,神似才到家”,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無論如何,掌握功法是戲曲表演最基本的要求,同時功法是人物體驗表現的媒介。同時,戲曲演員在運用功法時,不能僅僅要從功法出發,還要立足于戲劇本身。演員要通過自身精湛的表演,表現人物內心的準確體驗,在表演中完美結合“形”與“神”。因此,戲曲演員的培養,需要以技為先,使演員獲得表演的能力,并在此基礎上不斷追求技藝統一,才能最終使演員的表演技術手段與人物體驗達到相融無間的藝術境界。
四、結語
掌握技術不是戲曲藝術表演的主要目的,但掌握技術是學習戲曲表演的必要條件。演員若想在戲曲舞臺上實現真正的藝術表達,“這一切還得要有結實的基礎功夫,正如寫字一樣,從描紅模的一撇一捺開始,規規矩矩地寫好正楷字,然后再寫行草,自然就變化裕如、揮灑自然了”。⑨雖然進行深刻的人物體驗不是戲曲表演藝術獨有的,但它依舊是歷代戲曲表演藝術家追求的。戲曲藝術的創造離不開演員對功法的運用,也離不開演員對人物體驗的追求,只有兩者兼備,才能實現戲曲技與藝的有機統一。
注釋:
①⑦阿甲.生活的真實和戲曲表演藝術的真實[J].戲曲研究,1957.1.
②傅謹,曹南山.戲曲表演美學體系的歷史基礎與研究方法[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63(02):124-131+196.
③鮑綺瑜.向尚小云先生學《昭君出塞》[J].人民戲劇,1980,(12):10-13.
④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七集[M].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174.
⑤張庚.張庚文錄 第四卷[M].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230.
⑥王慈,蔣風編.藝諺藝訣集[M].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65.
⑧阿甲.戲曲藝術的最高美學要求——“程式的間離性”和“傳神的幻覺感”的結合[J].中國戲劇,1990,(01):44-45.
⑨蓋叫天.談表演藝術中的身段[J].戲曲研究,19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