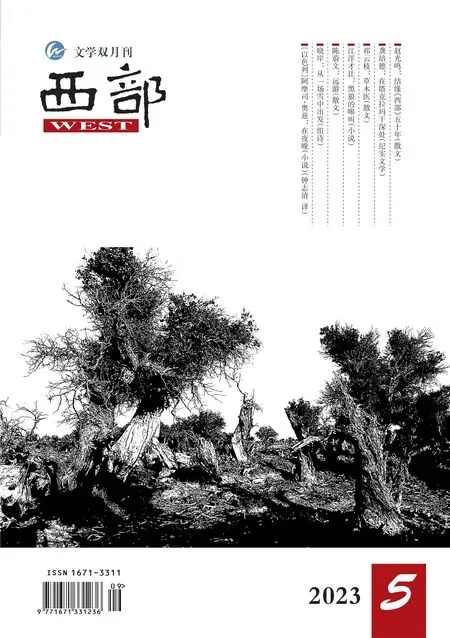夢起《西部》
王天麗
每一個寫作者都無法忘記作品第一次在省刊上發表時的喜悅與激動。
我一直喜歡文學,嘗試寫作的時間也不算短,大學畢業剛工作時就開始寫散文,在故鄉的報紙《塔城報》上發表了第一篇散文,后來在《新疆日報》《新疆經濟報》上發表過一些散文、隨筆,但是那種寫作很隨性,完全是一種情緒的自然表露,當然也很純粹,但距離我真正的寫作夢想——小說創作,還有距離。
我多么喜歡張愛玲,多么喜歡曹雪芹,多么崇拜馬爾克思、托爾斯泰……我什么時候也能像鐵凝寫一篇《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像張潔寫出《沉重的翅膀》,像史鐵生寫出《命若琴弦》,像沈叢文寫出《邊城》,像瑪格麗特·米切爾寫出《飄》,像瑪格麗特·杜拉斯寫出《情人》……或許是我太喜歡,文學在我心中永遠是塊神圣的高地,我始終都在仰望,始終不敢靠得更近。對于害怕“失去”,或許最好的辦法莫過于不去得到它。
年復一年,我仍然是個文學愛好者,在文學創作的邊緣兜兜轉轉,但小說創作的種子始終沒有發芽。但命運似乎也在眷顧我,我調到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圖書館工作。我剛到圖書館時那里條件很差,由于經費不足,圖書館長期處于建設階段,很長一段時間連購置新書的經費都沒有,但那些堆積在庫房里的舊書足夠我看了。有那么幾年時間,我幾乎將在高中、大學時囫圇吞棗似的讀過的經典名作重新讀了一遍,《悲慘世界》《約翰·克利斯朵夫》,包括大部頭的《追憶似水年華》等等。我一次次地在昏暗的書架中尋找,像見到了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還有久仰大名的新朋友;一次次感受到重逢的喜悅,感悟著文學的魅力,創作的沖動也在我內心里一次又一次涌現。時光荏苒,一晃都四十多歲了,我終于寫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大約兩萬多字的小中篇《秋無痕》,寫好以后并不知道該往哪里投稿,也不敢讓別人閱讀,只是在夜深人靜時拿出來自己閱讀,有時覺得自己寫得真好,并不比圖書館書架上排列的很多小說差;有時又覺得故事不夠吸引人,也沒有宏大的主題,簡直一無是處,恨不能扔進垃圾箱。時間到了2012年,我們圖書館也正式對外開放了,并定期開辦講座活動,邀請新疆一些作家來館里做講座。有一次準備請的是新疆文聯副主席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我恰巧剛剛讀了她的散文集《永生羊》。那陣兒新疆文學創作非常繁榮,周濤、趙光鳴、董立勃、劉亮程、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李娟等一批優秀的作家讓人耳目一新,他們的作品都收藏在圖書館地方文獻室。我尤其喜歡葉爾克西的散文,不光她的文字優美,更被她作品中呈現出眾生平等、尊重生命的思想和對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憂患意識所打動。我篤定她是個優秀的作家,她一定知道作品的好壞。那天我把自己的小說打印好裝在一個信封里,等到講座結束時找到了她,我懷著忐忑的心情把稿子交給她,就像把命運交給了她。我想如果葉爾克西老師說還可以,我就堅持寫下去;如果說不行,我就徹底放棄文學創作的夢想,安安心心地做一個文學領域的“局外人”。葉爾克西老師被我的真誠所打動,她收下時說一定會認真對待。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我大概等得太心焦,就鼓足勇氣給葉爾克西老師打電話,我要親耳聽聽老師對我命運的宣判。電話那頭,葉爾克西老師語調平緩,但非常清楚地說,小說讀了,很成熟,已經交給《西部》雜志社了。電話這頭的我,愣了片刻,隨后壓住內心的狂喜把顫抖的聲線拉直,說:“謝謝您,非常感謝。”
很快我接到了《西部》雜志社的用稿通知。我作為一名寫作者,第一次走進了紅山旁邊的文聯辦公樓,在八樓找到了《西部》雜志社,見到了編輯部的張映姝老師、柴燕老師,見到了黃永忠社長,他們無不熱情地給予我贊揚和鼓勵,讓我記憶猶新的是當時雜志副主編張映姝老師,她特地囑咐我:“好好寫小說,新疆寫小說的作家不多,寫小說的女作家更少,只要作品好,就不會被埋沒。”編輯柴燕老師也給了我同樣的鼓勵。從文聯辦公樓走出來后,我仍覺得自己像在夢境里,直到回家后又將那本帶著油墨香味的《西部》翻開,2012年第十二期,在“小說天下”欄目的頭題看到了我那篇小說的篇名、作者的名字,以及一行行整齊排列的鉛字。我真想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小說發表了。
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在了《西部》,我暗下決心要認認真真地進行小說創作了。
有夢想的人生,什么時候都不算晚。我和《西部》的緣分就此拉開了帷幕。一本雜志托起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夢想,堅定了我前進的目標。第二年我在《西部》發表了小說《椏兒》,我去雜志社取雜志時,遇到了當時任新疆作協副主席的董立勃老師,董老師夸我小說寫得不錯,但是,他又說:“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小說家,短篇小說要發表到一二百篇才行呢!要像劉慶邦、范小青那樣努力才行。”我狠勁兒點頭,在心里咋舌,也明白了文學創作需要艱苦的磨煉和大量的積累,我的創作之路才剛剛開始。隨后,我又在《西部》發表了《紅橡木床》《虛幻卻存在的鳥兒》《讀普魯斯特的女人》《薄荷紅茶》《銀色月光》《維也納森林圓舞曲》。《西部》用她博大的胸懷容納了我,為我的創作提供了一片沃土,在這個過程中,張映姝老師與我交集最多,每一篇文章交給她,她都會認真對待,提出修改建議,并鼓勵我向外省投稿,推薦我在省外刊物上發表文章。其他編輯也一樣,柴燕老師還為我寫過一篇文學評論,孫偉老師將我引薦給《十月》的編輯,并在雜志上成功發表了小說,讓我信心大振。雜志社的編輯方娜,雖然見面不多,每次有稿件投過去都會得到及時的回復。
2014年,《西部》雜志社推薦我參加了第四屆新疆作家上海創意寫作培訓班,那次培訓也是我步入寫作行列后的一次重要節點,讓我第一次認同了自己的作家身份。為期一個多月的活動中,我不光是受到了寫作上的專業培訓,還見到了大名鼎鼎的作家趙麗宏、葛紅兵,文壇新秀甫躍輝,以及上海大學的文學教授,聆聽了他們精彩的講座。去了蘇杭、南京等歷史文脈興盛、文人薈萃的地方采風,去了魯迅的故鄉接受文學的滋養。更重要的是,我見到了一批文學道路上的同道之人,王新梅、趙勤、薩朗、畢化文、南子、段蓉萍……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與人徹夜探討文學,第一次在深夜的小徑上放聲歌唱,幾乎每天都是半夜一兩點睡覺,凌晨四五點被院里枇杷樹上的小鳥吵醒,每天都處于亢奮狀態中。幸運的是,在后來的日子里,我們一直是朋友,彼此鼓勵,交流創作經驗,推薦好文章,介紹好編輯,分享發表作品的喜悅,訴說稿件不被采納的苦惱。這樣奇妙的人生旅程、人生經歷都是《西部》所賜。后來,我又多次參加《西部》雜志社舉辦的西部作家寫作營和文學改稿活動,聆聽疆內外作家、編輯們講課,不斷拓展寫作思路。通過這些活動,《西部》雜志社的編輯老師將我們引薦給內地刊物編輯老師,比如《青年作家》盧一萍,《作品》王十月,《長江文藝》何子英、吳佳燕,《黃河文學》阿舍,《廣州文藝》陳崇正等一批中國文壇上的優秀作家和重要編輯,為我們在省外發表作品牽線搭橋。
更值得慶幸的是2020 年,憑借在《西部》雜志上發表的短篇小說《維也納森林圓舞曲》,我榮獲了“哈巴河杯·第六屆西部文學獎”小說獎。這個獎項是新疆文聯《西部》雜志社設立的雙年獎,是新疆漢語言文學最高獎,也是新疆設立的首個全國性文學獎,我非常榮幸獲此殊榮,這也是我第一次因為文學創作得到了獎勵。我站在領獎臺上舉起沉甸甸的獎杯時,感受到了夢想的分量,文學的分量,它既沉重又輕盈,是飛翔的感覺。
似乎文學的大門在我面前敞開了,文學之路越走越寬,從2012年到2022年十年間,我在《清明》《星火》《滇池》《延河》《黃河文學》《青年作家》《長江文藝》《天涯》《作品》《十月》《人民文學》等文學刊物上發表中、短篇小說三十一篇,出版小說集《三色瑪洛什》《銀色月光》。我曾經計劃用十年的時間爭取在省外雜志上發表作品,再用十年時間出版自己的小說集放在圖書館書架上,現在看來,自己的計劃有些保守,當然這一切是因為有了新疆作協和《西部》雜志社的大力支持和培養,我提前實現了目標。
《西部》雜志,是新疆文學創作者仰慕的高地。雜志創刊以來,為新疆,乃至全國培養了許多知名作家,曾扶植出梁曉聲、張承志、唐棟、楊牧、周濤、章德益、趙光鳴等在中國文壇熠熠發光的著名作家、詩人。發表了大量優秀作品,為作者搭建了筑夢空間,為人民提供了優質的精神給養。特別是這幾年,我見證了《西部》的發展,它越來越壯大,越來越年輕,越來越包容,越來越優秀,就像辦刊理念所說的:創新、卓越、發展。
《西部》對于我永遠具有特殊的意義,她是我文學創作的搖籃,是引路人,是栽培者,給了我許多“第一次”,也始終像家人陪伴在我左右。沒有她,不知道我的文學夢想會不會發芽,不知道我還會不會堅持寫作,會不會還在另一條道路上艱難探索,就像歌里所唱:“如果沒有遇見你,我將會是在哪里,日子過得怎么樣,人生是否要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