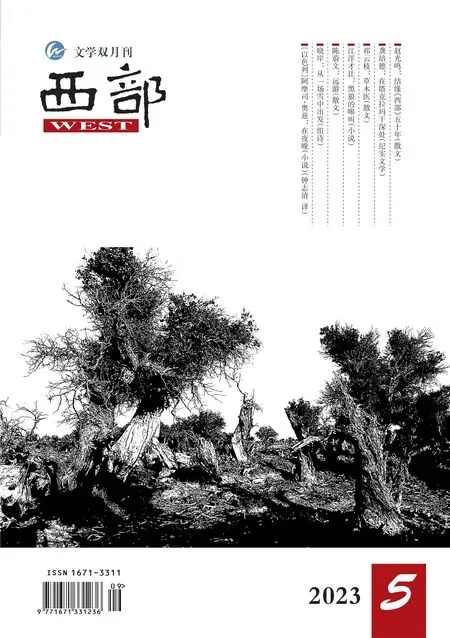我與《西部》
王世虎
細細數來,這是我寫作的第十個年頭。記得在更早以前,上初中時,第一堂英語課,老師問我們,你們的理想是什么?等到我回答時,當時腦海中只有一個詞poet(詩人),不得不說,這個詞在我后來的寫作中給了我力量,這是詩的預言。
十年前,我剛上大學,離開家鄉焉支山到金城蘭州求學,也是在這一年開始了我的詩歌創作。十年后的今天,我來到祖國的西部——新疆烏魯木齊工作,繼續和文學結緣,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新疆,《西部》一直以來都是各民族作家以及讀者最鐘情的刊物,更是被譽為新疆第一刊。其實,在內地各省市中,《西部》的名氣更大,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作為一本老牌刊物,不斷推陳出新,策劃了很多備受作者喜愛的欄目,受到一致好評。
打開《西部》第一頁,“尋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學表達”這句話給了我很多思考和啟發,我想這也是每個《西部》人的初衷。第一次在《西部》發表作品,是2022 年第四期新疆文本·烏魯木齊小輯欄目,刊發了我的五首詩歌,這對一個新人而言,是莫大的鼓舞。當然,這些年,《西部》也一直致力于推崇更多的年輕寫作者,給了年輕的作者很多機會。
當時,還有一件趣事,讓我記憶深刻。在第四期雜志印發以后,有好幾個讀者在烏魯木齊作者交流群里分享了我的那幾首詩,其中《想念著我的母親》《寫在小年夜》和《寫在入秋以后》三首詩受到很多讀者喜愛,大家都在找這個新的作者是誰。有朋友微信截圖發我,真是令我又驚又喜又惶恐,那是種復雜的心情。有一位讀者評論說,看到《想念著我的母親》這首詩,讓我也想起我的母親。這也不得不佩服編輯和《西部》的眼光是多么獨到。
2022 年5 月,某天突然接到《西部》編輯老師的電話,說準備邀請幾位在烏魯木齊的年輕寫作者參加寫作營,問我有沒有時間。當天下午,我就滿懷激動地去找了我們領導匯報,第二天便收到寫作營的邀請函,我也如愿地請上了假,參加了那次難忘的寫作營活動。也正是這次活動,讓我認識了很多老師,也結識了很多新朋友,我們歡聚在一起,以詩為伴。
寫作營期間,正值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八十周年,重溫講話精神,讓我們更覺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也更加堅定了我們為人民寫作的信念和決心。為期五天的寫作營,既有專家講座、座談、詩歌朗誦會,也有戶外采風等系列活動。
“身居鬧市不知春去,一進米東方覺夏深”,現在讀來,依然如在眼前,歷歷在目。天山村,窯坡村,這兩個位處中國北方的村落,卻對我影響頗深。一排一排的別墅,寬闊的街道,整潔的環境,和我記憶中的村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我的故鄉——窯坡村,如今已是廢墟一片,再無人煙,我知道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正離我越來越遠。此次寫作營我們住在天山村文雅民宿,距離烏魯木齊市區大概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一進門就是一片栽滿果樹的園子,旁邊種滿了花花草草,在房子兩側有主人種植的西紅柿、辣椒,還有茄子等等,好一副世外桃源的景象,惹人陶醉,不免沉浸其中。在房子的后面,還有一大片閑置的空地,旁邊擺放著兩架秋千和幾個石桌、石凳,白天可以喝茶,晚上可以看星星,談天說地,這不就是陶淵明筆下的田園生活嘛,我們感慨著,在這里拍照、錄制視頻,發朋友圈,告訴朋友們我的幸福和詩歌的幸福。按照活動安排,我們按時上課,幾位老師分別講散文、小說,也講影視、報告文學,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于我而言可謂是受益匪淺。后面,我們去了哈熊溝、玉西布早村、東道海子,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表演“新疆花兒”等,行程緊密而有趣。這里,有兩件事讓我記憶猶新。
2022 年5 月21 日下午,經幾位老師和民宿老板商量,我們要了一塊空地,并借了鋤頭和鐵锨,在房屋后邊那片荒蕪的空地上開辟了一塊地,并取名為“西部自留地”。盡管面積不算很大,但付出了我們整個下午的勞動。晚上,吃過晚飯后,天已經黑了下來,由堆雪老師帶頭,我、曹戊、亞峰四人用老板的手推車去圍墻后拉糞,給土地施肥。在拉完一車過后,亞峰早已不見人,躲在旁邊的秋千上說啥也不來,朋友說他就是我們的監工,彼此打趣著。我們三個人繼續鏟糞、拉糞、卸糞,一套動作下來行云流水,不一會兒就將三車糞平鋪在地里了。第二天醒來,手掌心生疼,我們遠離家鄉后,離土地越來越遠了,以至于土地和我們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當我們試圖去親近它的時候,它就以這樣的方式回復你。
后來,朋友在文章中寫道:我們的祖輩們世代生活在土地上,面朝黃土背朝天,他們是土地的一部分,土地也是他們的一部分,而我們不一樣,我們早已沒有了這種對土地的親近感,它也在拒絕著我們。也正是在那天,我寫完了詩歌《關于勞動》,其中詩的結尾兩句是“如今我年近三十/漂泊他鄉/對于耕種/我知道早已失去了世襲的可能”,友人評價說,這種失去感莫名的襲擊了我。對于在土地上長大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被遺棄。那一刻,我們擁有著靈魂的共鳴,生活讓我們痛苦,幸而有詩歌,可以承載其中的一部分。“襲擊”和“被遺棄”在心底深處深深觸動著我,因為我們都是土地是兒女。
活動結束后,至今也沒有機會回去看看那片土地,不知道怎么樣了。但我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有他自身的命運。我也相信,肯定還有機會會再回去,看看那片屬于我們的“自留地”。
第二件事是外出采風去東道海子那天,來回近兩百公里的路程,卻讓我難以忘懷。出了郊區以后,土路高低起伏,進入海子以后,有些地方甚至沒有路,一輛輛越野車行駛在荒漠上,坐在車里人就像大海的波浪,起伏不定。前面的車走過后,煙塵四起,跟近了之后就像穿行在沙漠底下,于是盡量減慢車速,這樣搖晃的幅度也會小一些,但每一個人的眼里都充滿了對事物盡頭的期待和熱情。當我們從車窗里看見那一片海子出現在我們眼前,不免興奮起來,甚至想在里面游泳,真是一個可怕的想法,但當時我確實這樣想了。
每一個生活在北方的人,心里都有一片海。而眼前的景象,實在是太美了,湛藍的天空飄蕩著五月的白云,一層層水的波紋從腳下四散而開,成片的蘆葦生長在兩岸,頭頂有白鷺斜飛,微風拂過臉龐,這一切都讓人充滿遐想,一切是那么的浪漫,有誰會不愛這里呢,有誰會不愛這樣的北方呢。我為聽到一片沙海的沉吟而感動,我為聽到一片海子的蘆笛而感動。這是祖國的西部,我的左側是東道海子,我的右側是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當你一個人走在岸邊,能明顯感覺到水漲水落的痕跡,這也是歷史的痕跡;一個人行走在這里,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不遠處,一只駱駝匍匐在空地上,一動不動,明亮的眼睛仔細打量著周圍,看著我們在對面走來走去,它始終都保持著一個姿勢,就這樣遠遠地看著我們走近再離開,像一位棲居在這片土地上的老人。當牧民騎著摩托車,揚起長鞭,將一群牦牛從那邊趕到這邊,牛跑起來的風沙直上云霄,似乎連接著地面和天空,遼闊的荒漠中,我們是不請自來的人。同行的老師說,荒漠是最脆弱的生態系統,一經破壞,便難以恢復。我們這么多人,突然闖入,對于這片靜謐的水域和大自然,我們是怎樣的存在,我思忖著。詩友在詩中寫道:壬寅年五月/一行人在東道海子/成為這片水域的一部分/在古爾班通古特等另一部分鑒定此刻的意義/而后,我們從照片中側身離開。
對此,我們不能給這趟旅途一個怎樣的定義,我們只能從照片中側身離開,盡量減少一些來過的痕跡,保持對自然的敬畏,那些遠古的詩意。
這片水域地處古爾班通古特沙漠的外圍,不算是沙漠腹地,沿途中長滿了紅柳、梭梭草等一批耐旱的植被,接受四季的洗禮。而那片波光粼粼的、一眼望不到頭的、晶瑩剔透的水域,將日夜起伏、涌動在我們的心口,成為新的長勢。回來的途中,早已是人困馬乏,再顛簸的路依然有回家的欣喜。友人在文章中寫道:我們在土地上勞作,也在土地上寫作,我們對文字足夠真誠。假如我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寫作的必要,更談不上什么真誠。晚上,我們又在秋千上蕩來蕩去,月色籠罩著我們,樹影婆娑,月光從樹梢上落下來,聆聽鳥叫和蟲鳴奏響的大自然的樂曲,整個人像在風中。就這樣我們一直坐著、搖著,什么都不做已經是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了。在人生的旅程中,能讓我們銘記的事物越來越少,但總有一些東西,在記憶深處閃閃發亮,這是我們的熱愛,也是我們的初心。
想起這些與《西部》的往事,仿佛那些日子就在昨天,不禁讓人心潮澎湃。今年,《西部》第三期刊發了去年我們在寫作營的采風詩歌,一次次的交織和激勵,讓我難忘,在新疆工作卻因為文學而倍感溫暖。這也堅定了我在詩歌創作這條道路上的信念和理想,重要的是給了我們年輕作者更多的機會,并獲得創作上的自信。《西部》對我有知遇之恩,張映姝和李穎超老師亦對我有知遇之恩,我對他們一直心懷感激和敬畏。他們都是我們身邊非常優秀的作家,他們的作品、人格,以及對文學的熱情和執著,是我們所有年輕寫作者學習的榜樣。
今年,新疆文聯成立七十周年,《西部》也走過了六十多年的光輝歷程,我想,這也是一代又一代的編輯老師默默耕耘的成果。我也相信,全國的讀者朋友、作家朋友和評論家們也和我一樣,始終熱愛著《西部》,并且關心它,愛護它,尊敬它,由衷地希望《西部》越辦越好,成為培養一代又一代年輕作家的搖籃。
再一次祝福《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