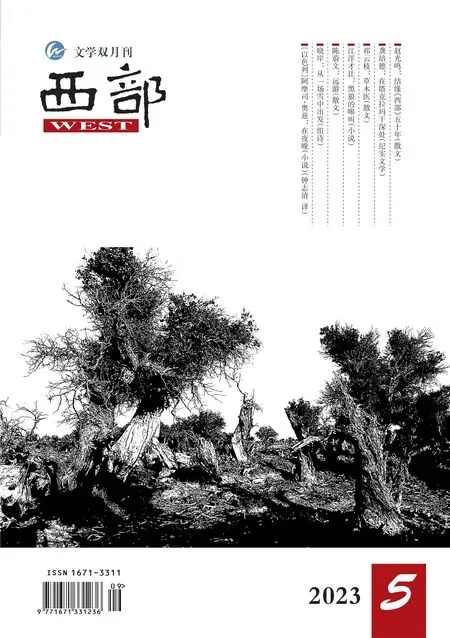六星街的主人與過客
張惜妍
那是個初夏,周末的黃昏,我約了依琳娜到六星街散步,我倆說好在黎光街六巷的青驪民宿門口會合。我走到中心轉盤,確定了一下方向,順著路牌尋找,我這個路盲,走著走著就迷路了。
鴿子飛過上空,哨音清亮,巷道里有老人坐在大門口的木凳上聊天,有主婦舉著膠皮管子澆花,潮濕的地面散發出泥土的清新,孩子們三三兩兩嬉鬧,貓咪跑過墻角,太陽的余光照在藍色的墻面上。
這個六角形的街區,街道曲折,小巷密布,漫步其中,如同卡爾維諾的書名《蛛巢小徑》。路牌設置得很迷惑,黎光街、賽里木街、工人街交錯并行,每個路牌都是從一巷開始按照數字排序到十巷。明明你正對著工人街的指向牌,轉個身又面對的是賽里木街,特別容易混淆。當我和別人說,“我在黎光街十巷的手風琴館等你”的時候,和我約見的人很有可能一邊應答一邊向著賽里木街的巷道走去。
有時打車,出租車師傅會問,哪個六星街?上海城的六星廣場還是師范后面那個?然后謹慎地調動大腦里的路線,試圖迅速定位到乘客指定的位置。
——“差不多能找到。”
——“那個地方岔路太多了。”
唉,都是不確定的短語,聽得我不放心,一路提醒他,那附近有個學校,還有個餐廳,有個氣派的大院子。其實,說了一路,我自己也沒說清楚,目的地到底在幾巷。不過下車時司機會好心建議,去六星街,要是想準點到達,最好提前十分鐘打車。我們都沒好意思說破——至少八分鐘是給迷路轉圈圈預留的。
六星街街區的規劃布局與十九世紀末現代城市規劃先驅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理論(1898 年)有著極其相似之處。街區整體上呈六邊星狀,中心是公眾建筑,外圍為居住區,形成一個獨具特色的居住模式。對于很多本地人來說,六星街就像一個環環相連的迷宮,外地人更是走進去出不來,出來進不去。
六星街的中心是一個六角圓盤,黎光街、工人街、賽里木街從中心點向四周輻射的六條街道。據說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這里俄羅斯族人居多,轉盤這兒有一個水井,是整個街區唯一的生活水源,就成為活動聚集地,人們在水井邊乘涼,在樹蔭下拉手風琴,唱歌跳舞、聚會、舉辦婚禮。
如果給這個叫六星街的地方寫說明書,有幾個關鍵時間節點是必要的。2009年,六星街列為舊城保護性改造的重點項目,保留了原始風貌;2010 年被命名為新疆歷史文化街區;從2019 年開始,市政府對六星街區建筑風貌、生態環境、經營業態實施全方位保護,那是對六星街更新改造提升成景區的起點。流光溢彩的城市史就此掀開一角。
從那時起,巷道的一側,各種施工材料堆放擠壓,路況變得狹窄而復雜。這個位于城市北側,占地四十七公頃的街區,倘若就年輪來算,歷史并不算長。據史料記載,1934 年,伊犁屯墾使公署由霍城惠遠遷至寧遠(今伊寧市),伊犁屯墾使邱宗浚聘請德國工程師瓦斯里在1934 年規劃設計之初,將源自歐洲規劃理論的放射形路網,與中國各民族傳統院落組合而成。從路牌可以得知,六星街由縱橫交錯的三條主要街道形成,分別是黎光街、工人街和賽里木街。而在1964 年之前,這些街道并無自己的專屬名字,它們被人們統稱為六星街。
經過近百年的變遷,多民族聚居的六星街在縱橫之間交織出奇特的文化共生現象,這是它最顯著的價值所在。來自首都的城市規劃師李昊,走過世界很多城市,心中有著理想之城的標桿,對于現實中的城市評價,有時難免苛刻。然而,站在六星街上,他說:“對于六星街,我實在是無法不贊美它。在這樣中西合璧的街坊中漫步,很容易感受到城市獨特的文化個性。在某條路上,我似乎依稀能看到英國萊奇沃思那樣的田園小鎮風貌,歷史的變遷又仿佛重現眼前。城市幸福感,也就來源于這種生活氣息。”
在六星街,那些刷著藍色圍墻、屋頂或門柱的庭院,傳統與現代融合并存,以馬賽克般的形式展現出了城市文化的多樣性。藍墻之外,一架花籬,搖曳著田園詩意。在游客眼中,走進迷宮一樣的巷道,仿佛走進一處公共藝術展示中心,演繹著絢麗的民居和鮮活的民俗生活。
新建的中心小廣場不大,長椅供人歇腳,老人推著嬰兒車走累了,坐在那里休息。天氣晴好的時候,常有一個俄羅斯族白發老人戴著墨鏡,坐在那里即興演奏手風琴,當他展開右臂,徐徐拉開琴,微瞇著眼,能感受到神情的舒展和自我的存在。他或許在琴聲中回憶:某年的某個夜晚,那時候族人眾多,時常有家庭聚會。面包香甜,熱茶溫暖,姑娘們的歌聲笑聲像解凍后的冰河,嘩嘩啦啦奔涌,起舞助興。他還是英俊小伙,拉著手風琴伴奏,深情的眼眸隨著紫色的裙子旋轉翩飛。如此生動的景象,屬于年輕時代,只有愛情才能展開眼神對視之后細節紛繁的劇情。
周末或者節假日,小廣場常有群眾自發的演藝活動,以老年人居多。巷道里也有年輕人自組的樂隊聚集,歌聲充滿真誠和夢想的力量。玩樂器的小伙子卡爾帕提穿著牛仔褲和藍色的圓領衫,他擅長把都塔爾彈奏與現代電子曲風結合編曲,配上他的煙嗓,即使最熟悉的流行歌曲,也會在星星閃爍的夜晚,給聽者帶來另一種驚喜和感動。
一年夏天,在六星街音樂庭院里,一場民間藝人的專場音樂會正在進行。我再次見到卡爾帕提,還是一樣的牛仔褲、藍色短袖衫。燈光迷蒙,煙嗓婉轉,唱著感傷的情歌,仿佛時光真的停滯在了某一刻,定格在了某場回憶之中。幸好,他所處的場景說明了這個酷愛音樂的男孩在時間的激流中保持自己的節奏,平穩一點,閑適一點,每一天、每一年都沒有與音符分離。
民間藝人賽努拜爾的都塔爾彈唱響起。
請你將茶杯倒滿
如若能再次相遇
我的心會無窮地開心
總是會傾訴彼此的感情
能和最親的人一起哭泣
也想和最親的人開心
……
即便是跨越語言、地域和民族,這種質樸深情的歌唱總會讓不同的人獲取共鳴。樸素、濃烈、堅韌、溫暖、純凈、深沉,這些可以無限堆砌的形容詞,皆不足以描述她的歌唱,她的都塔爾早已與家鄉、土地、親人和生命融為一體。每一種樂器都有各自的靈魂,借由一雙雙彈撥的手,將生活的褶皺填滿美妙的音符。
作家羅伯特·瓦爾澤曾寫道:“在夏天,我們吃綠豆,桃,櫻桃和甜瓜。在各種意義上都漫長且愉快,日子發出聲響。”夏夜在六星街,歌聲縈繞、器樂悠揚、笑意歡暢,有相親相愛的人,有遠方來客,燈火闌珊,人間值得。哦,就是那個難以忘卻的夜晚。演出結束后,我和友人卻找不見車停在了哪里。我們從巷頭找到巷尾,找了相鄰的兩條巷道,終于找見,七轉八拐,駛向回家的路。
人流在街角匯合又離散,街邊的樹,庭院的花,承載的記憶和情感更廣大復雜。街區的魅力藏于樹蔭之中,光暈的斑點打在墻上、路上和人們的身上,隨風晃動,夢境一般記錄著四時的更替以及歲月的年輪。我有時路過看見老人坐在樹下發呆,他身體欠安?不,也可能往事正在回憶里卷土重來。還有一次,我在樹下等人,無意瞥見身邊白楊樹上有一行刀刻的小字——我在這里等過你。一個悲傷的愛情故事,就用一句話概括終結,簡單又復雜。這棵樹就像一個親歷過重大事件的證人,身上攜帶著證據,無聲無息老去。
白楊、槐樹、梧桐、白蠟、橡樹……在無法擴建的路邊,向有限擴展的空間表達沉默。庭院里的人,從老人到孩童,都愛著街邊的樹,就像愛家人,從根部愛到樹梢。院門內的人,來來去去,生生死死。路邊的樹,則一言不發,供那些回味往事的人坐在樹下緩解孤單,獲得一些旁白和物證。
古麗努爾嫁到賽里木街有三十年了,我去她家的時候,她白衣花裙候在門前,身材高大、熱情溫暖。房屋是本地典型的藍色小院,走廊擺著紅色的海棠,盆栽無花果樹,還有那種寬葉的橡皮樹。古麗努爾生在兵團,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高中畢業后分配在一家國營賓館工作。她的第一個孩子是男孩,出生半年后被診斷為腦癱,她為了照顧兒子辭職。曾經多少個黑夜,她在丈夫的懷里泣不成聲,在親友們面前強撐歡顏。好在一家人相親相愛,抵御著兒子殘疾帶來的悲傷。在家人的精心呵護下,原本被醫生論斷活不過二十歲的兒子,已經度過了二十六歲的生日。她還有一個女兒在特殊教育學校當教師。“女兒就是為了照顧哥哥學了這個專業,她可盡心了,教她哥哥認字寫字。你看,這是哥哥給妹妹寫的字。”小學生的方格本上歪歪扭扭寫著“吃了,飽了。”四個字,熱乎、踏實,看得我眼窩潮潮的。
老劉是錫伯族,娶了一個漢族媳婦,家住在黎光街二巷與江蘇路的交叉處。下崗后,夫妻倆在街角開了一家小商店。他出生在六星街,熟人熟地。“我對這一片太熟了,活了六十年沒有離開過。我年輕那會兒,巷道里只要出現個陌生人,我瞅一眼就知道他要干啥。”他說的沒錯,騎自行車的少年,來到一扇后窗下,車鈴有節奏地叮當數次。屋里女孩聽明白了,找借口出門,坐上自行車迅疾而去。母親找不見女兒身影,趕緊關窗戶,好像窗外的樹葉在風中竊竊私語說閑話一樣。更遠處的一棵樹,看見一對青年男女進了通用機械廠的大門,牽手游蕩到月亮升起。“是我老了嗎?過去的事情忘不掉,現在的事情記不住。”當年的通用機械廠早已蕩然無存,一片住宅區覆蓋了曾經紅火的廠房,可在老劉心里,青春的回憶清晰如昨。誰說不是呢?我感覺,人到中年以后,眼前的事物越模糊,從前的事物卻越清晰。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里說:“在夢中的城市里,他正值青春,而到達依西多拉城時,他已年老,廣場上有一堵墻,老人們倚坐在那里看著過往的年輕人,他和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當初的欲望已是記憶。”
依琳娜帶我去過她的長輩阿拉娜的家,我承認自己帶著很大的好奇心,這一點和大多數人一樣,他們從哪里來?他們有著怎樣的故事和傳奇?他們是中國公民,身份證上的民族一欄填寫的是俄羅斯族。簡陋的屋子里,最顯眼的是墻上掛著的家人們的黑白照片。“這個,我媽媽,這個,我妹妹,她們都躺在六星街的墓地里。”
這所房子和里面舊式的物件告訴來者,這座城市里曾經生活過什么樣的人,以及這些人在這座城市里曾經發生了怎樣的故事。
阿拉娜的丈夫阿那托力久病臥床,卷曲的白發堆在頭頂,面容清瘦。床下竟有四五只貓咪在玩耍,時不時有一只調皮地跳上床,從老人身上踩過去,像在鼓勵床上的老人:要活下去,要生機勃勃。依琳娜用手指一指貓食盆,“看,日子不寬裕,啥時候來,盆里都盛著滿滿的貓糧,沒虧著小家伙。”
我經常看見七十多歲、身體肥胖、走路喘氣的阿拉娜,雙手提著艷麗的裙裾在俄羅斯風情園跳舞,沒想到家里是這樣的境況。“我喜歡跳舞,管它呢,活一天跳一天,高興就行了嘛。”
去年阿那托力去世了,阿拉娜還是照樣去跳舞,碰上了就聊幾句,她也不訴苦,只是淡淡地說:“一起生活六十年了,剩我一個人在家里不好受,出來跟大家跳跳舞,什么都不想了。”對于悲傷,人的天性中并無對癥的良方。以往的歲月里,無論生活多么艱難,在手風琴的伴奏下高歌跳舞,這是一種苦樂,一種達觀。
皮特羅是東正教堂主事的人,白色的教堂沉默低調,禮拜日到此做禮拜的族人并沒幾個,這里是他們最后的精神家園。倘若要找尋俄羅斯族曾給予這片地域的影響,舊教堂、墓地、手風琴館和那座經歷了百年的俄式破舊大門……歲月滄桑都在六星街上得到印證。連多數本地人也不知道在鬧市區竟然有這么一片古老的墓地。一個世紀以來,那些去世了的俄羅斯族人,就長眠在這塊墓地里。從黎光街二巷進入,透過榆樹的濃蔭,當年的教堂只留下了門樓和角樓的一部分,破舊的大門上釘著一個黃色木條的標志。門外是繁華世界,而門里屬于往昔,屬于另一個世界的寂靜。
皮特羅的老父親年逾八十,衣裝潔凈,絡腮胡子濃密花白,坐在夕陽里,身影有一種失落的優雅。皮特羅說教堂祈禱用的小蠟燭都是他做的,老人時而有些糊涂。他一本正經地把我叫過來,在我耳邊說,“我有一個秘密,我奶奶說了,不讓我告訴別人。”
我們已聽不到曾經回蕩在城市上空起伏蔓延的鐘聲,卻依舊有鴿子繞著教堂飛翔。那個在年輪里消失的人們聚集的六星街,偶爾會在皮特羅的老父親口中“復活”。
這都是與六星街有著深厚過往與情緣的主人。我的成長時光與這片街區無關,反而能因此獲得某種異質的、個人化的表達角度和感覺。我追溯著六星街的前世今生,我寫過它,并不意味著我就了解它,我對它依舊陌生,依舊會迷路。
有一回我又迷路了,誤入工人街五巷,巷口一戶庭院外立著一株高大的薔薇,根莖粗壯、枝條修長,一樹嬌艷的黃色花朵密密匝匝,特別壯觀。我在花樹前拍照、流連,冒冒失失走進院子和主人攀談,忘了自己要去干嗎,不過因此牢牢記住了那一樹薔薇。第二年夏天再經過那里,門口那一樹黃燦燦的絢爛消失了,從鄰居那里打聽到這家人出租了院落搬走了。我站在那里,就像做了一場夢,懷疑那棵花樹是我的幻覺。可明明好幾個人都告訴我,那里真的有兩棵招眼的樹,院門外是薔薇,院門內是櫻桃樹。改造后的庭院成了演藝餐吧,我進去過,在樹上摘過甜美的大櫻桃,而那一樹薔薇,竟然真的消失了。那么大一棵花樹,怎么能移走呢?在另一個地方活著嗎?
在新媒體視頻里高調亮相的六星街,以個性鮮明的風貌和魅力成為這座城市旅游的新地標。每一個來到這里的人,都要到六星街走一走,否則就好似沒有到此一游。
漫步在街區,民宿客棧、手工藝品店、餐廳、特產店鱗次櫛比。咖啡館、酒吧、飲品店越來越多。夜間燈火閃爍、勁歌熱舞,往來穿梭的年輕人俊顏鮮衣、咄咄逼人的青春,讓夜晚的六星街完全不同于白晝的小巷幽深。他們似乎在宣示:這街道,這座城,這時代,完全屬于又一輩新人。
全新面目出現的景區讓原本就找不到方向的路癡,更找不到路了。
王煒煒的民宿開在黎光街九巷,她和無數預定的游客一起經歷著六星街的迷失時刻。因為找不到路,就在附近打轉而放棄住宿的事時有發生。
——“導航那么精準,為什么你還找不見呢?”
——“你到了啊?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你,自己給迷路了。”為此,她親自設計了手繪地圖,拍成照片,發給每一位咨詢的客人。
依琳娜在廣場中心的俄羅斯風情園經營著一家面包店,建筑物明黃色的外墻加上墨綠色的木窗很是顯眼。更明顯的標識是,路邊樹蔭下立著一個俄羅斯姑娘舉著面包的彩塑。就算站在馬路面對面的方位,顧客還是常常找不見。
——“看見廣場上的三套馬車銅塑像了嗎?往馬頭正對的方向過馬路就到了。”
——“三匹馬?你指的是哪個馬頭對著的對面?”
這是依琳娜經常接到的詢問對話,搞得她啼笑皆非。因為她自己也是路癡。“朋友聽說六星街有好幾家咖啡館,讓我推薦一下哪家的好喝,我大腦里迅速展開了地圖搜索并確定了方位,表述時卻無法說清楚到底在哪條路上。只好對朋友說,說了你也找不到,自己去轉轉吧,轉到哪家進去就是了。”
看來,沒有一個路癡能順利進出六星街。
六星街成為“潮街”,三條主街上,大部分宅院被購置或者租賃,開設為時尚門店,新潮涌動、生機煥發,周圍的餐飲被帶動運轉起來,所有業態共同依附在這個被稱為“旅游景區”的生態圈鏈條上,像毛細血管一樣相互連接,又相互供養。
六星街的好光景到來了,咨詢招商政策的、打聽房源的、裝修開張的……很多客商沒能等到來年春天,那條彼此供養的毛細血管,被疫情剪開一條細微的口子。誰也沒想到,這條細長的口子,愈合的時間竟然長達三年。這三年,太難以描述了,感覺時間在瓦解,日子既飛逝而過,又好像永遠過不完。
無論因何而阻隔,時間的腳步總是堅定不移朝前走的,年輕的人和事永遠像浪潮一樣滾滾而來,那是發展的力量,在每一個時代成為不羈的風尚。即使游客稀落,新店鋪依然登場,明麗的色彩刺激著斗志,經營者對未來充滿信心。就像草原上的火災,土地完全被燒黑燒焦,所有綠色都消失了,可燒焦的土壤養分更豐富,新的植被長得更茂盛。人也是這樣,他們總能找到辦法,懷揣著希望重新開始。
許多人在嶄新又永恒的當下面臨選擇,“韌性”再度成為一個具有神奇魔力的字眼。所有的問題似乎都來自一種信念,失敗也好,痛苦也罷,各種人生障礙不過是一個終會過去的糟糕時刻。新的造夢邏輯,帶來新的希望和新的迷茫。痛苦正在過去,遺忘還沒來得及發生。但無論如何,六星街正慢慢從寒冬的陰沉走進陽光明媚的春天。
春節前,我帶女兒去拜訪一位暫居六星街的電影導演,聊得開心,不覺忘了夜已深。告辭以后,母女兩人又轉向了,索性順著路隨便走。除了行駛而過的車燈,幾乎沒有行人。走著走著,見一家院門口亮著燈,兩個巴郎在賣烤肉串,孜然的香味絆住了女兒的腳步,她站在烤爐前吃得那么享受。
那個夜晚,空氣寒涼,圓月高懸,天空明凈。月亮下面什么都顯得美,憂愁也可以轉化成詩意,要是月亮旁邊閃著星星更是感覺美妙極了。我和女兒繼續沿街步行,像把一本舊書一頁頁翻過去,讀出新意味。長大的孩子,蒲公英一樣隨風四散,即將大學畢業的她將飄落何方?這個冬夜,一盞小燈照亮的院門、烤肉的香氣,不知道會不會讓離家的孩子長久掛念。
這樣的夜晚,以前沒有出現過,像電影鏡頭般美好,轉瞬就消失了。我記著,寫下來,這美好就獲得了永恒。
冬天過去了,春天過去了。五月,初夏來臨,晚霞漸出,淺淺的金色余暉照耀下,六星街的玫瑰在空氣里暈開,自然而熱烈。這樣的一個夜晚,皮特羅的老父親溘然長逝,帶著他奶奶的交代,那不能告訴別人的秘密,再也見不到天亮。送別老人那天,我走在黎光街四巷,路邊的樹干斑駁得就像生活的裂痕,樹還是那些樹,在太陽最熾烈的日子也能感受郁郁蔥蔥的涼。生離死別終將來臨,我們在懷念一個人的時候,到底在懷念什么?有些告別是無法說再見的,那就叫做永別。但是你想起那個人,洶涌的思念無法停止。那些樹葉縫隙里投下的光影,就是生命里最珍貴的記憶。
想想前些年也走過這里的小巷,日子靜謐漫長,街角的小店放著陳奕迅的《十年》,聽歌的人心想,十年后的歲月遙遙無期。后來在小巷里又聽到《十年》,不禁輕嘆浮生也不過轉瞬。如今走在這里,反倒是會被不經意間撞見的某一個場景打動——同行的人,吹過的風,琴弦里流淌的詩,來不及告別的名字,樹皮上刻著的誓言……一切的一切,自然、平實,又自帶溫度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