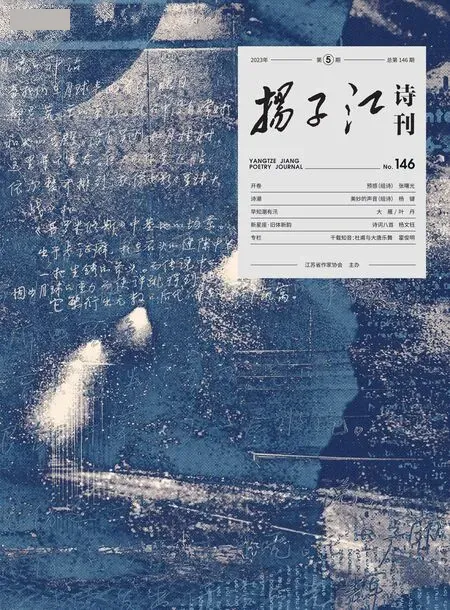“淵藪”:經驗的意境化何以可能?
——張阿克詩歌閱讀隨想
沈 健
張阿克的組詩,總體上看,屬經驗之詩。“理發”“沖澡”“失眠”“病中”“觀茶”“夜跑”,這些瑣屑、斑駁的日常生活內容,被選入詩題,賦以詩能,“明暗交匯的光線”之中,分行推出“光陰的遺物”,將個人在塵世秘境中“被深埋的暗”交替展開,是讀來腸熱之詩。
舊衣在柜櫥里掛著,如一件
擺設。它的冷清一再告誡自己:
在場,已是昨日的事情。
其后的時間,它一直依靠回憶
活著:那時,主人的光鮮和榮耀
一部分,像是由自己帶來。
偶爾,它也會記起委身一堆布料時
的情境:那種被深埋的暗,仿佛
余生的光陰都將身處淵藪。
眼下,這件被閑棄的衣物看上去
風平浪靜。它將暗涌的波濤
控制在自身狹小的體內,僅用
追憶,處置內心多余的激情。
這是《舊衣研究》全詩,在場的“舊衣”“柜櫥”“余生”,缺席的“身體”“主人”“布料”,集聚成一個錯綜繁復的場域,舊與新,空與實,邊緣與中心,角落與前臺,一個野心、權力、欲望、自矜、虛榮的心理微宇宙,既有沉思自嘲,又有省悟自警,“內心的激情”澎湃可聞。我比較喜歡這首詩,對詩中“光鮮和榮耀”一語卻持保留意見,如能替之以更市井勾欄的意象,詩給人的滄桑肌理也許更具包漿感。順便說一句,“衣柜”物象,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安妮·埃爾諾和奧爾加·托卡爾丘克都以之為題寫過小說,可謂一個多世代、多國家、多體裁的可觀照“淵藪”,可以不斷書寫下去。
《理發小記》更是富有諧趣:“沖洗只是預設的陷阱,那張/方椅,才是守候你多時的深算之物。”發膚受之于父母,積淀著豐厚的人倫意涵,剪刀咔嚓,世事流水,在“遲疑”“明了”之間,“一把剪刀”完成了人世的自我教育。詩人從自我、他者、世事和命運多個維度,把“理發”場景組合成一個錯綜立體的新境,既充溢著自嘲解構之智,又暗含了客觀重構之慧。這是智性經驗的個我之詩,讓人讀后回味再三,悵然久之。坦率地說,這類詩歌要寫好,并不容易;寫得好的詩人,也并不多見。
沒錯,詩是經驗的語言結晶,是個人身心觸發經驗的升華,因對存在的深切洞察而獲取超越性能量。這是里爾克以降現代詩的一個重要路向,但經驗的屬性、質地、及物點以及話語所勾連的人與萬物串聯的內在勢能,是此類詩成功與否的分野和尺度。張阿克的詩,經驗鮮活,措辭獨特,畫面立體,指向繁復,避免了哈羅德·布羅姆所謂“陷入本質上的貧乏和想象力的枯竭”。在我看來,它屬于經驗詩高地的一種眺望,敘述詩淵藪的一種鉆探。
春雪薄命,只當了一回人間的看客。
存世的短,看上去,并未影響它的認真。
它們輕手輕腳,不疾不緩的樣子
仿若捺著性子、埋頭趕路的莊稼人。
一場雪,安靜地來去,對于世事
并不發表什么看法,也不暗藏某種
改造的欲望。它們的白,以及消逝
輕描淡寫:有如一種無心的提醒。
此詩題為《春雪觀察》,短短八行,對雪落大地時的形狀、質地、形態未著一字,從“捺著性子、埋頭趕路”的性情出發,以擬人口吻澆注了一種忍耐、通達、悲憫、齊物的德性經驗。“一種無心的提醒”,既有道法自然的生命大智慧和大境界,也有秘味旁通的詩學氣韻與旨趣。類似之作還有《斷流河》《山溪》,思辨性敘述勾連出人世多樣態、多面貌的可能。
從經驗詩典型特征來看,《春雪觀察》《斷流河》《山溪》等詩帶有體驗介入色彩,具有傳統物象的象征意味,與前述的日常現代經驗詩并不完全相同。綜觀張阿克的詩,除日常生活場景小詩外,還有以社會場景為主體者,如《漁歌號子》《護城河》《棧橋》等事象小詩;以自然場景為主體者,如《海水》《鳥鳴》《樟樹》等物象小詩。但無論日常在場經驗,抑或自然社會的體驗經驗,都能通過個人化的智性建構,拆解生活表層聯結的僵硬機制,填實現實與想象縫隙的空泛,達成技術強度與詩意密度之間的微妙平衡。
需要追問的是,張阿克的詩何以能從眾多同類作品中被辨識出來,獲得夏荷初綻的獨立價值?在我看來,一個突出的特征在于,他的詩帶有鮮明的意境化傾向。我和張阿克不熟悉,從簡介上看,他的寫作歷練并不長,對他的古典詩歌積累更是毫不知情,但他的寫作中卻在整體方法上顯示出一種宋詩意境化的取向。
意境是一個中國古典詩學概念,指因生命律動而韻味無窮的具體化藝術圖景,其突出的特點為畫面鮮明,情景交融,虛實結合,氣韻生動。宋詩加入了敘事和議論元素,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的理趣指向。當代漢語詩歌自上世紀90 年代以來,情緒、印象、記憶、知識、科技、理論等經驗元素入詩,修正大詞抒情及物性空洞之弊,開拓敘事及物詩的新境界,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但物極必反,過猶不及,在當下詩壇的海量經驗書寫中,充斥著小感觸、小情緒、小哲理的贗品經驗和情緒二道販子美顏化、套路化、扁平化之作,一些陳詞濫調對人們的精神胃口造成無庸諱言的敗壞,一定程度上還耗損了新詩的聲譽。張阿克日常經驗的分行話語,不僅具有鮮明的畫面感和在場感,而且善于將畫面多維嵌套,深入到事象、物象深層結構之中,建立起多向度的復調對位、交叉映射、多重疊加的立體空間,形成詩意矢量的解析和語言勢能的綻放。在我看來,這也許可視作一種對古詩意境的技術重構與探索,一種近似于法國新小說非線性的敘述方法,被引入漢詩的經驗書寫。請讀這首《夜跑者》:
夜跑者沿著操場繞圈,像是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幽靈。他的體內
有光,照亮月亮缺席的路徑。
跑動時,黑暗被身體和看不見的風
同時撕開;路途被暗中測量
約等于后退的時間。
跑動時,他察覺有什么在幽暗中
滴落,與脊背上的汗珠
形成呼應。他還察覺,有些無法
見光的事物,正暗地里發生交易。
而時間的消逝看上去
并不增加經驗的厚度:夜跑者
環道而馳,數圈后回歸起點,過往
如同一頁未著一字的紙張。
最終,夜跑者停下來,帶著
滿腦的疑惑。而黑夜若無其事
仿佛置身事件之外。
在現代城市和鄉村,有氧運動、健身跑步的“夜跑”,已經成為常見的個人生活景象。詩人用光影幻化、敘議轉換、自言自語的方式勾勒一幅幅動態的畫面,人物、情節、環境和思想、情緒、氛圍多元疊加。“后退的時間”“無法見光的事物”“月亮缺席的路徑”“滿腦疑惑”,從小操場到大宇宙,從薄紙張到厚經驗,從“環道而馳的夜跑”到“來自另一世界的幽靈”,雜多零散的生存印象與飄忽體悟經由“覺察”的焦點,被整合到一個內在的密度高、刻度深的“淵藪”之中,打通了存在、現實、形式之間現代意境的關聯。
細讀張阿克的詩,想象、情緒、印象、回憶、移情、幻覺等,透過主體在場感畫面而建構的綜合“淵藪”,在繁復的對焦之間移動、閃爍、互構、成全,移步成景,轉行成像,此等立體多維的動態畫境,是不是可以算作古典詩歌意境在當代漢語中的一種翻新?
張阿克對現代生活經驗意境化處理的路徑較多,比如《善變的火焰》的巴洛克拼接,《漁歌號子》的愛舍爾疊加,《病中書》表現主義繪畫在閉環語境中的蒙太奇制作,屬于向現代繪畫語言的借力之舉。再如警句模式,也屬積極探索,盡管張阿克一再宣稱“收起詩歌中多余的修辭”,但大量警句穿插所暗含的隱喻、拆解、戲仿、反諷等技術運用,較好地起到提亮詩境、喚醒省思、激活靈視的作用。
“人為描摹的事物,只是幻影”(《漁歌號子》);“過程熱鬧/甜膩帶來健忘和不深刻;而過程冷清/淡淡的苦,卻能品出更多的余味”(《咖啡問題》);“只有卸下鐘擺,你才能看清想要的/是怎樣一種生活”(《病中書》);“平靜的玻璃介質下,埋著一口/洪荒的暮年之鐘”(《自畫像:中年》);“我們只是將幾行腳印留在沙灘上/我們的腳印很快就會被海水沖走”(《海水》);“而時間的消逝看上去/并不增加經驗的厚度” (《夜跑者》);“相對于根邊的水土,世界/只是陪襯,僅需保持/有限的聯系” (《樟樹》)……一方面在敘述背景中引入全球化時代的新變元素,另一方面,放低話語主體的姿態,采納與自然萬物平起平坐的調性來處置自然物象、社會事象,警句、詩眼、亮點詩行“循河谷而下”,給現代經驗詩添加了穿透力和洞察深廣度。
如此諸多要素的綜合顯示,張阿克的寫作與前人的關系,既有一種承續,又有一些偏離,還有一定的轉向。比如他與胡弦、陳先發、朱朱等當代江南詩人的關系,與卞之琳、袁可嘉、朱英誕等現代智性詩寫的關系。甚至還可以找到更結實、更飽滿、更精確的王小妮、畢肖普、希尼的一些蛛絲馬跡。我個人認為,如能以宋詩的意境理趣敘述為原始股,以上世紀90 年代以來日常經驗書寫為基本盤,雜之以上述各路詩人技藝,張阿克的發展可能性也許值得期待。也就是說,張阿克的實踐探索具有某種代表性,“從模仿拼盤到獨立風格”(馬爾羅語),一種被壓抑的傳統,或者說一種新拓耕作如何引進傳統詩學養料,并使之實現有效的當代轉換,這是需要張阿克和我們共同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