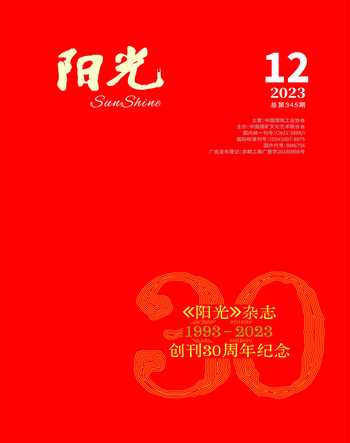陽光的算式,左右溫暖
邵悅
有詩寫道,“生活/只是極其簡單的運算/不斷加法。不斷減法”。詩的語言,總會帶著出其不意的預見性而來,留下意味深長的準確性而往。
確實如此。在紀念《陽光》雜志創刊三十周年之際,我心里不由自主排列的幾個簡單加減法算式,就把自己過往三十年時光里的五味雜陳,以及與《陽光》交集的故事,運算得一清二楚,算式左右,被明媚的陽光溫暖著,照拂著。
第一個算式,存在于時間向后推移的記憶中,是煤炭文化不斷進步的必然結果:
用當下,減去三十年,等于一九九三年——《陽光》誕生。
歷史上的今年,國際國內發生的諸多大事,如同過眼煙云一般,早就被世人淡忘,或被時代所淘汰。可這一年,發生在中國煤炭行業的一件大事,非但沒被人們淡忘或淘汰,還一直風雨無阻地走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自然,也會走向明天,走向未來,且被人們捧讀、傳閱、交口稱贊。
是的,由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主管、中國煤礦文化藝術聯合會主辦的全國煤炭行業唯一一家文學藝術期刊——《陽光》雜志創刊號,在這一年誕生了。一家刊物創刊,在文學藝術領域看來,事情不算大,也不算小,多了一家與作者讀者交流、溝通的平臺而已。可對煤炭行業來講,卻意味著創建了大礦山的精神家園,中國數百萬礦工有了精神文化生活的棲息地,恍若漂泊的靈魂,終于找到了皈依的客體。
《陽光》號的升起,無異于萬里煤海上升起一輪太陽。從此,那些烏黑的石頭,變幻成發光發熱的太陽石,翻滾的煤海浪花,演繹成劈啪作響的一朵朵太陽花,而那些黝黑憨實的礦工,就是名副其實的開掘光明的使者。
《陽光》雜志應運而生,使那些深埋地層億萬年的煤炭被開采出來后,燃出的每一塊紅紅火火的能源,通過文字及時傳送到祖國的四面八方;讓太陽般光芒四射的礦工精神,一張紙就可以承載,一篇文章就可以講述,并世代永流傳。
在此,我謹以一個寫作者和現任《陽光》編輯的身份,深深致謝那些為《陽光》期刊創辦、經營和發展,三十年嘔心瀝血、付出辛勤汗水的老師們!致謝那些始終支持、扶掖《陽光》的社會各界人士!致謝那些時刻關注、鼓勵《陽光》的煤炭行業內外廣大作者和讀者!
因為有你們,才有今天的《陽光》明媚不已,燦爛依然。
第二個算式,來自一個時間段的契合,是人事物偶合際遇的結果:
用我現在的工齡,減去三十年,等于一九九三年——《陽光》與我的工齡同齡。
個人歷史上的今年,正逢我邁出煤炭職工醫學院的大門,走進大東北礦區,被分配到鐵煤總醫院工作。當時,我并不知道自己工作的起點,與《陽光》雜志的起點,交集在同一年。更料想不到后來,會被《陽光》牽引一段姻緣,又與《陽光》結緣至今。可在礦山,因為有煤炭為介質,注定要匯集煤火一般明亮而溫暖的光輝。
在礦區醫院工作的第二年,我從礦工會宣傳干事那里,看到了一本《中國煤礦文藝》(后更名《陽光》),愛不釋手,沒想到煤炭行業也有自己面向全國公開發行的期刊。在那樣的年代,互聯網還沒有廣泛興起,文學藝術傳播途徑主要依賴紙媒。對從小酷愛文學的我來說,刊物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我向那位朋友索要了各期雜志,工作之余,悶在宿舍里,認真品讀學習那些小說、散文、詩歌,透過那些文字,我更深刻理解了什么是煤礦,也了解了煤礦工人井下采煤的艱辛,從心里更加敬重那些在地層深處采掘光明的人。并幻想著有朝一日自己的文字也能得到“陽光”的照耀,如若這樣,便是極大的幸事和滿足了。
后來我才意識到,兩個時間的交集并非單純的巧合,《陽光》的溫暖還包含天意有緣的成分。工作第三年的秋天,我嫁給了一位礦工,正兒八經地成了煤礦工人的家屬。沒錯,就是嫁給了那位送我《陽光》雜志的工會干事。打那以后,每一年我都有《陽光》可讀,被雜志里的作品溫暖著,明媚著,指引著。柳陰下,燈盞旁,捧讀一本《陽光》,如同沐浴在明媚的陽光里,即便行走暗夜,也有一束光照過來,仿佛夢想就在前方不遠處等著我。可就是自己的文字被《陽光》照耀成鉛字的渴望,遲遲沒能如愿。我在心里寬慰自己“只要追逐這束陽光,堅持不懈走下去,就不擔憂眼下的幽暗,終會漫步在明媚的陽光里。”就這樣,我與礦山、與煤海、與《陽光》結下了不解之緣,漂泊不定的根,扎在了礦山;美好的青春,獻給了煤炭;渴念的精神生活,系掛在了《陽光》。
第三個算式,存在于個人幸運的小天地,是那種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境遇:
二十年服務礦區的我,加上編輯《陽光》近十年的我,等于今天,卻大于個人本身。
“人生如戲”也好,“戲如人生”也罷,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期許,那種天遂人意的感覺,如同焦渴的禾苗適逢一場及時雨,雨后又是彩霞漫天般的美麗與美好。我在心里無數次感念《陽光》的厚待,感念燃燒的煤炭送來紅紅火火的暖意和光明。
在礦區醫院工作第二十個年頭,或許是心有所念,必有所成,或許是對《陽光》的癡情感動了老天,好事接踵而來,《陽光》雜志社同志來鐵法能源公司調研工作。《陽光》雜志社社長、主編盛軍“伯樂識馬”,我便榮幸地被《陽光》雜志聘為詩歌欄目編輯。
以煤為媒,二十歲妙齡的《陽光》與二十年工齡的我,交匯在一起。一想到自己就要親手來編加“詩意陽光”,內心抑制不住的愉悅感再一次爆棚。當天晚上,用詩句記錄了突如其來的驚喜:
從明天,起
我不再是平庸之人
而是一本,被陽光打開的書
憂郁,陰霾,小性子
都已知趣兒地從我體內抽離
生怕明亮的言辭,拆穿它們的詭計
從此,以后
我的箭,在陽光的弓上拉滿
射向哪里,射中什么,都明媚不已
恍如夜空,嵌上了太陽
白晝,疊加了白晝
……
很快,興奮的心情被緊張不安的情緒取而代之。我非常清楚,參與編輯這樣一份全國公開發行的煤炭行業大刊,絕非簡單容易之事,心里難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稿子選出差錯,影響其他編審環節,給雜志社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我退一步安慰自己,“緣在天意,事在人為。與《陽光》近二十年的情緣,可謂至深至純了,如今,承蒙《陽光》眷顧,際遇一個全新的自己,定會有陽光溫暖的庇佑。”做事不服輸的性格,主導自己走到了當打之年,干勁兒正濃,何愁這份工作做不好?更何況與自己的文學夢關系密切呢?
十次春秋輪回轉眼而過。近十年來,雜志社的信任、賞識、鼓勵和鼎力支持,像一把偌大的保護傘,為我遮風擋雨,更如同一束明媚的陽光,照亮前行的路,催我上進,有陽光溫暖的呵護,何懼前路風雨坎坷?勇敢前行便是。
有人說編輯工作是給人“做嫁衣”的苦差事,稿子修改得再完美,版權也是作者的,與編輯無關。確實,編輯的職責就是把每一篇選稿仔細編輯加工,讓優秀作品通過刊物平臺,無瑕疵地、漂漂亮亮地“嫁”出去,讓讀者讀到好作品。因為文學情懷與夢想,我格外喜歡這份累并快樂的“做嫁衣”工作,“嫁衣”做給他人,如同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看到自己編加的稿件,印刷成千上萬冊,飛往祖國各地,被人們捧讀在手,那種快樂,不亞于舒展隱形的翅膀,在蔚藍晴朗的天空下自由飛翔。
近十年來,《陽光》在編選稿件過程中,多是側重“煤礦人寫”、“寫煤礦人”的稿子,激勵更多寫作者寫好礦山故事,為中國礦工精神鼓與呼。同時也兼顧行業外的質優稿件,廣泛傳播中國煤礦文化,擴大《陽光》的知名度,力求那些從《陽光》“嫁”出去的稿件,披著陽光的嫁衣,自帶溫暖,自帶明亮,走到哪里,都是光彩照人。
每一期《陽光》出刊,我都打心里興奮,為刊發作品的作者高興,也為“陽光”又增加了一期的厚度而高興。
編選稿件的過程,也是我學習提升的過程,特別是那些名家的作品及其創作談,更是讓我受益匪淺,內心的求知欲得到滿足。編、學相得益彰,實乃求之難得。總有人說我這幾年在文學創作上進步很大。若個人真是有了點滴的進步,也全是《陽光》的功勞,是《陽光》搭起的平臺,照耀著我,又打開了我;鞭策著我,又溫暖了我;教誨著我,又托起了我……
近十年來,編輯過的稿件無計其數,稿子越選越精,卻把自己越編越厚,編成一本漸次增厚的被“陽光打開的書”。編加在“詩意陽光”里,成長在“陽光打開的書”里,一詩一文皆洞明,一朝一夕總關情。
第四個算式,來自時代飛速前進,是現在與未來美好愿景的鋪陳:
百年富礦,加上數百萬礦工精神,加上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愛,等于《陽光》美好的現在和光明的未來。
自古道,“打江山易,守江山難。”在信息化、數字化飛速發展的互聯網、物聯網時代,各種新媒體、融媒體頻繁輩出,應接不暇,常看到某家報刊說停刊就停刊的消息。確實,時下的紙媒,生存與發展前景令人堪憂。《陽光》雜志也同樣面臨巨大的壓力和嚴峻的挑戰。要想刊物更好地生存和發展下去,必須轉變經營理念,調整思維方式,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為使《陽光》辦得更好,雜志社每年都要組織召開全國性的《陽光》工作會議,與國內各大煤炭企業及時交流友誼、溝通情感,進一步加固《陽光》根基的同時,促進期刊穩步發展。為給煤礦工人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陽光》雜志社社長兼主編盛軍,每年都親自深入到煤炭企業,了解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有的放矢地抓好《陽光》雜志運作的每個環節。雜志社還多次組織開展“中國作家走進煤礦”采風活動,礦山是能源最豐富的文學富礦,深入礦山,扎根礦工,便可以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服務礦山,謳歌中國礦工。
令人欣喜的是,隨著時代飛速發展,數字礦山、智能開采、綠色能源等高新煤炭產業技術,與大時代齊頭并進。被煤炭能源托起的《陽光》,從不缺少紅紅火火的能量。近年來,《陽光》雜志越來越備受社會的廣泛關注,深受廣大讀者的愛戴和支持,每年除各大煤業集團大批征訂外,還有很多讀者個人自費訂閱、購買《陽光》。刊物與讀者建立起互為互用的關系,“雙向”理解、支持和愛護,才使得今天的《陽光》向好、向上、穩中求進地發展。
凡是相遇皆成美好,而美好出自艱難;凡是過往皆為續章,而續章續的是希望。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是夸張的手筆,是世事歷經艱難、走過坎坷后灑脫與豪放的抒懷。就在這“一揮”之間,大浪淘沙,時光淘洗萬物,或被急流淹沒,或被飛速發展的時代淘汰出局。《陽光》雖有大礦山腳下烏金滾滾的能源可依可靠,有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奉獻的中國礦工精神可歌可泣,卻也與世間萬物萬事一樣,經歷三十年的風雨洗禮、冰雪考驗,火紅的初心從未更改。如今,正當而立之年的《陽光》,朝氣煥蓬勃,芳華始照人,散放的每一束光,落地生輝。
三十載《陽光》熠熠生輝,終是感恩所有遇見,因為每一份遇見,都是天空和大地對陽光的饋贈:遇見一陣雨,便有雨后彩虹璀璨奪目;遇見一場風,便吹走浮萍,留下堅固;遇見一棵草,便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遇見一朵花,便有美麗可綻放;遇見一棵樹,便有繁茂可參天;遇見八百里煤海,便有燈火通明的動力源頭……因為所有遇見,才有今天的《陽光》艷陽驕驕,才有未來的《陽光》光輝燦燦。
“東郎屹立向東方,翹首朝朝候太陽。一片丹心萬古存,誰云坐處是遐荒?”古往今來的詩句里,總能讓人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人生過半,我越發想遠離俗世物是人非的侵擾,獨享一小塊陽光充盈的凈土,或讀、或寫、或編,與文字為伴,與《陽光》共情,看流年風景,聽時光吟誦,“與誰同坐?陽光清風我。”
未來已來,在新時代的大考面前,宇宙萬物的運算法則,無論加法還是減法,無論等式還是不等式,算式左右兩側運算的都是美好希望,最終的答案,都歸結于陽光自帶明媚,人間自有真情。
讓我們在溫暖祥和的歲月里,心手相牽美美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一路與陽光同行,一路與陽光同輝。
以一首小詩,謹寄感恩《陽光》之情:
編加陽光
以十年為一計
近旁的陽光,恰好照耀了我
以十年為一束
第三束陽光,恰巧編加了我
我不確定
太陽石上的文字,能否被火焰讀懂
卻可以確定,它指派的光源
比任何事物都陽光充足
暮晚的太陽
并未落下去,只不過是
轉到地平線以下——
世界的另一面,繼續恩澤萬物
如同一本期刊
從單頁碼,翻到雙頁碼
從上一期,轉到下一期
從一個十年,輪回到另一個十年
太陽的品質,陽光得
令人感動
身體里的一分熱,正發一分光
再把這分光,編加成詩
獻給人間煙火
邵 悅: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中國煤礦作家協會副秘書長。《陽光》雜志編輯。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魯迅文學院新時代詩歌高級研修班學員,魯迅文學院首屆全國煤礦作家高研班學員。作品散見《人民文學》《詩刊》《光明日報》《青年文學》《北京文學》等多家報刊,作品入編《中國詩歌年選》等多種文集。著有詩文集《火焰里的山河》等8部。獲中國長詩“新銳詩人”獎、全國煤礦文學烏金獎,獲《人民文學》《詩刊》等征文獎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