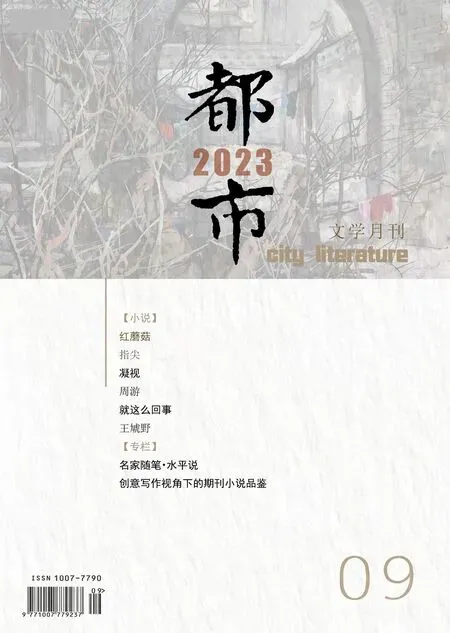戲劇性和主題
——讀蔡駿《火柴》
○鐘小駿
《火柴》是作家蔡駿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說,發表在《當代》2023 年第2 期,我是在《小說月報》2023 年第5 期上看到的,全文萬字,是這期短篇的頭條。
小說創作大概會有兩個階段,或者說兩個方向,一是鋪排成篇,強調故事性;二是直抒胸臆,以泄心中塊壘,這兩個方向依托的都是技術或者說“技巧”,但因為出發點不同,會有些彼此之間的摩擦,無關高下,也不分對錯,只是在一個系統內認為重要的“元素”在另一個系統內的重要性會下降,比方說“主題”,比方說“戲劇性”,這一點,不言而喻。
因為基礎出發點的不同,會延伸出某些技巧的使用方法不同,比方說“想象力”,夸張些說,某個時期的主流文學“模型”對想象力的使用甚至已經脫離了中文“想象力”這個詞本身的含義,而有了自身的“賦魅”,也因此我需要在此聲明一下,本文中的“想象力”是指基本的文學技巧。
一只貓的出現會引發什么?關于一個地點的回憶會引發什么?關于一個人呢?“2016 年秋天,因為一只健碩的流浪貓盤踞在我的汽車引擎蓋上,外邊剛好是寒秋的蘇州河滾滾而過,促使我完成了中篇小說《貓王喬丹》(首發于《十月》)。”“不知不覺帶入了許多曹家渡的記憶——曾經的‘滬西五角場’,三區交界的神奇地帶,從靜安寺通往蘇州河的渡口,五角星似的五岔路口,永遠張貼著手繪海報的滬西電影院,密密麻麻鋪滿屋頂的三角形街心島——如同一艘驚濤駭浪中的微縮戰列艦,連同黑夜里我外公沉重的呼吸聲,都已沉沒到海底墳場去了。而今重新浮出海面的是賽博朋克的二十一世紀,是天主教堂的哥特式尖頂,以及晚高峰排隊擁堵的車流。”“2020 年,我開始有意識地寫“滬西曹家渡”,完成了《戴珍珠耳環的淑芬》(首發于《人民文學》)。2022 年,先是《饑餓冰箱》(首發于《上海文學》),然后是《斷指》(首發于《芙蓉》),直到今日的《火柴》,感謝《當代》雜志。”
這是關于想象力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總是在寫作訓練中強調“觀察”,并由此提出了“素材”的概念,但其實不可避免地,在這里我們總是會面臨前面提到的兩個系統的“抉擇”:是選擇“事件”本身,還是選擇事件背后的“意義”?其實,這就是“戲劇性”和“主題”之間的偏重選擇。有些創作者在面臨這個問題或者說選擇的時候會聽憑本能,但除了具有明顯偏重性的細節本身——人咬狗、大洪水這樣有強烈“戲劇性”指向的,妓女愛國、乞丐救國這樣強烈“意義”指向的——之外,是大量存在于我們日常生活中,同時具備兩種指向,但分別不夠鮮明的素材,這些素材,需要經過我們的處理才能變成我們創作時的養料,也就是“細節”。而我們進行處理時所依靠的,或者說我們處理的原則,說是我們的審美,其實就是我們對兩種系統的取舍。
“2022 年8 月,我重讀了威廉·福克納的小說《燒馬棚》,重看了李滄東的電影《燃燒》,記憶里悄然點著一枚火柴,照亮了少年時代那些轉瞬即逝的朋友們。”人怎么會沒有童年,沒有朋友呢?所以,不會有人不理解蔡駿要說的這個故事,但還是那個問題,怎么讓人相信,或者說怎么讓人能夠進入到你的故事,你的空間里呢?“……這一日,法國梧桐黃葉子一簇簇蜷了地上,我立在教堂門口排隊做核酸。輪著我是最后一個,打開手機掃好碼,聽到有人叫我名字。負責掃碼的大白對我招招手,我看一眼防護服里的面孔,除開性別一無所知。她講普通話,我是綢緞,記得我嗎?我說,你是綢緞?她說,蔡駿,做好核酸不要走……”只要注意到小說題目下面作者的名字的讀者,一定會在這個開頭之后解決這個問題,蔡駿寫了一篇主人公叫“蔡駿”的小說,它讓讀者相信,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但沒有人的生活是為了小說服務的,作家的生命中不會充斥著“殺人”“放火”“出軌”,當然同樣也不會充滿著“救贖”“真愛”“相知”,大家都是普通人,你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蔡駿”是不是有著一個“中俄混血”、引發了著名的“大興安嶺火災”、身上隨時能掏出讓人進入迷幻狀態的“紅魔鬼蘑菇”、酷愛玩火的名叫“火柴”的少年同伴,我們不得而知。而一個靈動的、漂亮的、家境優越的、同時與我和“火柴”產生羈絆的,被我們稱為“綢緞”的小姑娘,在多年之后與我相遇,緊接著“殺夫”“縱火焚家”,然后請我開車送她去與上海相隔“三千二百千米”的漠河,因我不同意又把我的副駕駛座前的手套箱給點燃,最后“翻過高速公路護欄,大衣毛皮領蓬松,像一頭逃出動物園的母鹿,隱入黑魆魆的綠化帶”,這整個件事,又是否真實呢?
其實這就是這篇小說的敘述過程了。蔡駿在進行核酸檢測時遇到了當年的小學同學“綢緞”,建立聯系后相約在下次小學同學聚會時再見,結果綢緞遲到,請蔡駿開車送她,可指的路越來越遠,最終在加油站說其實她要去漠河找“火柴”,蔡駿等綢緞睡著后掉頭開回了上海,驚醒的綢緞點燃了手套箱,接著下車消失在黑暗中,而蔡駿轉頭開向漠河。
按照“故事”的分析方法,我們看到的只有一個“事件”,或者說只有一個“行動”,這肯定是不合格的。也因此我們明白這肯定不是一個傾向于“戲劇性”的作品,換言之這是一個作者有著強烈的表述欲望的“主題”作品。那么,我們觀察的自然也就是作者的意圖究竟是什么,以及是否完成了意圖的傳遞。
“2022 年,大約有三分之一光陰,我被困于家中。這一年,雖然距離曹家渡一步之遙,每天看著蘇州河水流淌而過,幾乎可以計算出多少分鐘前流淌過三官堂橋下、穿過武寧路橋到我面前,但我的肉身來到曹家渡心臟地帶的次數屈指可數。相形之下,我的靈魂卻無數次回到曹家渡,回到我童年棲息過的底層天井,回到冬天冰冷刺骨的室內,用生著凍瘡的手指貪婪地閱讀某一本書……無論《火柴》的故事是否虛構,但《火柴》中的‘我’確是純然真實的我,《火柴》以及‘曹家渡童話’其他諸篇作品中的我以及曹家渡以及傾注其中的情感和憂傷亦是真實的。而此種憂傷,一半來自個人歲月的流逝和內心的回望,一半來自時代劇變和面目全非的故鄉。正如郁達夫先生說過的:“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真的。”
所以反過來說,作者自身觀察到了,或者感受到了一個東西,一種情緒,很想與人分享,“為了這碟醋,包了一頓餃子。”餃子好不好吃是基本的技巧問題,但別人如果說這“餃子”怎么怎么對或者不對,應該是6 個或者8 個褶,該是韭菜豬肉或者芹菜雞蛋餡的等等等等,也都對,但那不是請客的家伙的目的,你就說你吃餃子的時候蘸沒蘸著醋,這才是根兒,這才是這頓餃子的意義。
那“想象力”是什么呢?是拿著醋之后,沒想著我去做頓面條或我去煮塊肉,而是想著我要吃頓餃子,于是有了故事的輪廓,然后我去找面,這是“素材”;我又去找豬肉和韭菜,這是“事件”;我要調餡,這是“結構”;撒進去的醬油姜蔥,就是“細節”。這一系列行為是你面對著一碟醋干出來的,想到用餃子來展示醋,就是最大的想象力。
當然,有的時候你愛吃韭菜雞蛋餡的,卻偏偏沒有韭菜,那吃純肉餡的,或者索性就吃了一碗面,都是一回事。把這個醋用上,才是你的目的。
多說兩句兩種系統在觀察方面的區別導致的最終差異。比如“老人打麻將”這個素材,如果你看到你會怎么使用?張愛玲年紀很小的時候總看到家中有幾個女子在打麻將,從來不以為意,多年后她回家,看到當年那幾個女子已經變成了老太太,還是牌搭子,這時張愛玲已經掌握了麻將技巧,很快就發現牌桌上大家的牌要不然只剩幾張,成了“小相公”,要不然就是很多張,成了“大相公”,可大家都沒有發現,仍然正常地抓牌打牌,好像聊天才是目的,打牌不過是附帶。這個細節至此已經很是生動,可之后她說,她站在旁邊聽了一會兒,發現這幾位連聊天的內容都和以前一樣,這就是那碟醋。
蔡駿和我同年,這篇《火柴》的醋我很有同感,里面的餡也出乎意料的很是喜歡,他說“那一年電視臺在放娜塔莎·金斯基的洗發水廣告,每趟看到都讓我神魂顛倒。”我沒看過這個廣告,我知道蔡駿在說什么,我真想看看那個娜塔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