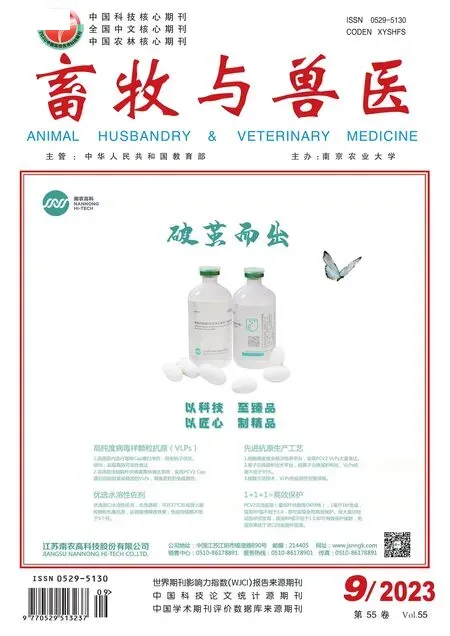牛結節性皮膚病研究進展
程肖曄,王曉亮,常廣軍,左冉坤,沈向真*,李知新*
(1. 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2. 寧夏動物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寧夏 銀川 750000)
牛結節性皮膚病(lumpy skin disease,LSD)是一種由痘病毒科的結節性皮膚病病毒(lumpy skin disease virus,LSDV)導致的牛傳染性疾病[1],是一種急性至亞急性的疾病,其特征是發熱、皮膚黏膜及內臟結節、消瘦、淋巴結腫大、皮膚水腫,有時甚至死亡。LSDV感染的發病率差異很大(5%~45%),一般來說,其死亡率小于10%,但發病率高達90%[2],能夠在短時間內出現在距離最初(局灶性)暴發地點幾百公里的地方。牛群患病后,身上會出現大量的皮膚結節,損害皮膚的完整性影響皮革生產,食欲減退體重下降。除此之外,LSD還會影響奶牛產乳性能,導致產奶量急劇下降,有時還會導致死亡,嚴重影響奶牛經濟產業的發展。
1 病原學
1.1 病毒特征
引起牛結節性皮膚病的LSDV與綿羊痘病毒(sheeppox virus,SPPV)的同源性高達98%以上,與山羊痘病毒(goatpox virus,GTPV)基因組核苷酸之間的同源性高達96%,三者只能通過分子特征來進行區分。LSDV在電鏡下呈橢圓形或磚形,覆蓋著短管結構,病毒粒子大小約320 nm×260 nm[3]。痘病毒中的正痘病毒可以引起水牛痘,病毒粒子由1個核心、2個側體和2層脂質外膜組成,是動物病毒中體積最大、結構最復雜的病毒。與許多在宿主細胞核中復制的 dsDNA 病毒不同,痘病毒有自己的復制機制,因此在細胞質中復制;病毒基因以雙相方式表達,早期基因編碼參與基因組復制的非結構蛋白,晚期基因編碼病毒結構蛋白。
1.2 基因組功能
LSDV基因組是雙鏈DNA,含有156個開放閱讀框(ORF),由一個被2.4 kb的末端反向重復序列(ITR)包圍的中間編碼區域和156個假設基因組成[4]。痘病毒的進化通常是通過基因丟失和縮小宿主范圍而進行的,通過基因組序列分析發現,在SPPV、GTPV和LSDV的端粒中也有同樣的基因丟失模式[5]。SPPV和GTPV的大多“管家”基因氨基酸序列原本與LSDV有98%以上的同源性,但由于插入剪切和移碼突變,有3個蛋白質家族的C末端結構域發生改變,于是SPPV和GTPV與LSDV中的ORF_138基因同源性降低到了84%[5]。LSDV的基因功能包括復制、結構和組裝、轉錄和翻譯、生長和凋亡、錨蛋白重復、宿主免疫逃避、毒力、假定蛋白和體液免疫等[6]。
1.3 免疫機理
痘病毒在感染宿主細胞過程中,通過抑制宿主細胞中白介素-1(IL-1)的合成和釋放,編碼可溶性細胞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TNF-α)、IL-1和干擾素-γ(IFN-γ)等,合成病毒編碼的類表皮生長因子和類轉化生長因子等,對抗宿主細胞介導的抗病毒免疫作用,從而逃避宿主的天然免疫和適應性免疫[7]。山羊痘病毒的免疫逃避主要通過細胞介導,除了通過受感染細胞的出芽釋放到細胞外的包膜病毒粒子外,大多數病毒仍留在受感染的細胞內。這些細胞可能會感染鄰近的細胞或使病毒逃到血液中傳播到全身。據報道,皮內接種后,SPPV和GTPV能夠感染單核細胞/巨噬細胞,表明這些細胞可能有助于病毒的全身性傳播[8]。最近有研究顯示痘病毒還可能使用 G 蛋白偶聯的趨化因子受體樣蛋白來促進免疫逃避[9]。ORF_138是山羊痘病毒屬共有的基因,其作用類似于OX-2樣蛋白,OX2/CD200家族蛋白通過膜定位和與CD200R受體的特定相互作用,下調體內巨噬細胞和T細胞活性,并抑制抗原啟動。山羊痘病毒屬(CaPVs)成員在基因組水平上有95%以上的相似性,因此所有CaPVs都具有共同的主要抗原,從自然感染中恢復的動物能夠抵抗再感染。然而,最近在中東和非洲之角暴發牛結節性皮膚病的現場經驗表明,這種交叉保護只是部分的[10]。
2 流行病學
2.1 國內外流行情況
LSDV起源于非洲,自2012年以來,該疾病迅速而廣泛地傳播到中東和巴爾干地區、南部高加索地區和俄羅斯聯邦的部分地區。牛結節性皮膚病是一種死亡率低的牛類疾病,在非洲,這種疾病的平均發病率為10%,患病牛群的死亡率為1%。在疫苗接種充分發揮作用之前,該疾病迅速從一個地區傳播到另一個地區[12]。2015年,牛結節性皮膚病蔓延到希臘,2016年,歐洲東南部7個國家,即希臘、保加利亞、北馬其頓、塞爾維亞、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和黑山,還有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哈薩克斯坦也報告了疫情[12]。2018年,該病蔓延到東歐國家。
2019年該病傳入我國新疆地區并首次確診[13],截至目前,中國7個省共報告了8例LSD暴發。8次暴發的總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19.5%(156/801)和0.9%(7/801)。每一次單獨暴發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6.6%~100%和0~16.7%。在1年之內,LSDV在中國最西部和最東部的省份先后被確定,甚至到達了中國大陸以外的臺灣島。福建、山東、四川、寧夏等各省份(自治區)牛結節性皮膚病疫情均是由外購牛引起。截至2021年9月,國內共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陸續公布了牛結節性皮膚病疫情[14](如表1)。這無疑是對中國牛養殖行業的重大威脅,為了保證相關貿易的安全進行,我國在實驗室診斷、支持治療、場所消毒和疫苗接種等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11]。
2.2 傳播途徑
研究表明,在沒有合適昆蟲的情況下,動物間沒有發生疾病傳播,未表現臨床癥狀,動物的口腔、鼻腔或結膜中也沒有檢測到病毒[15]。在大多數情況下,LSDV的長途傳播與動物的運動有關,但明顯的季節性模式表明,節肢動物很可能是疾病迅速傳播和短期傳播的主要原因。到目前為止,LSDV傳播最有可能的媒介是吸血節肢動物,如穩定蠅(枸櫞酸蠅)、蚊子(埃及伊蚊)和硬蜱(頭蠅和鈍蟲)[12]。節肢動物可以通過結膜、皮內和靜脈傳播LSDV。有研究顯示,與皮內接種相比,靜脈接種LSDV會對宿主產生更明顯的臨床癥狀[15]。從長期受感染動物的精液中可以分離出LSDV,表明LSDV也可通過精液傳播。
2.3 易感動物
LSDV感染反芻動物,對人類沒有感染性。它是一種影響牛以及水牛的病毒性疾病,某些品種的牛比其他品種更容易感染,特別是薄皮的牛,如澤西島和根西島的牛品種和埃塞俄比亞的福格拉牛[2],以及非洲桑加牛。也有研究表明LSDV可以感染一些非洲的其他野生動物[5],已經證明LSDV可以通過實驗感染長頸鹿、黑斑羚和阿拉伯牛津魚[16]。然而,尚未見報道有任何野生動物的LSD暴發。這些研究表明,野生動物在LSDV的傳播中沒有發揮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受感染動物的死亡和被捕食,可能會導致其余種群中存在少量的血清陽性,這種潛在的危害尚不清楚[2]。像SPPV和GTPV一樣,LSDV對上皮細胞具有易感性。
3 臨床癥狀
LSD的發病率差異很大,在3%~85%之間。在流行地區,發病率約為10%。LSD的死亡率在1%~3%之間,但在嚴重的暴發情況下高達40%。這些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不同很可能和牛的品種、健康狀況、病毒分離毒株和參與傳播的昆蟲媒介的不同有關。感染LSDV后死亡的具體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與許多因素有關,包括牛的品種、病毒毒株、繼發性細菌感染、動物的健康狀況以及參與傳播的昆蟲媒介的類型;另一個因素是由副痘病毒引起的偽牛痘和牛結節性皮膚病的混淆[17]。
LSD會出現至少5處典型病變,特征是發熱、淋巴結病、皮膚結節和眼鼻分泌物黏稠增多,皮膚損傷通常表現為乳頭上的痘損傷,也可能在其他部位引起皮膚損傷,此外全身出現0.5~5.0 cm大小的堅實平頂丘疹和結節,如會陰、大腿、頸部、臀部、陰囊、頰黏膜和頭部內側[12]。如果該癥狀伴有發熱(高于39.5 ℃)或產奶量減少20%,則定義為嚴重病例。LSD最明顯的臨床癥狀是形成全身的皮膚病變,這些皮膚損傷愈合后會留下永久損傷的疤痕。
4 實驗室診斷
4.1 傳統實驗室方法
雖然LSDV會引起明顯的皮膚和內臟病變,但仍需要實驗室確診。經典的方法如電子顯微鏡,可以用來識別皮膚病變中的痘病毒,然而除非應用特異性抗體免疫染色方法,電子顯微鏡并不能區分SPPV、GTPV和LSDV這3種毒株。
通過病毒的分離盲傳可以在細胞或雞胚上觀察到病變從而進行診斷。皮膚結痂以及鼻腔和口腔拭子是病毒分離最有效的樣本[27]。牛結節性皮膚病的病毒分離一般有2種方式:一是利用雞胚培養,病毒可在雞胚絨毛尿囊膜上增殖,但雞胚不死亡,接種5日齡的雞胚隨后置33.5℃孵育,6 d后收毒;另一個比較常用的方式是利用細胞分離。目前,初級羊腎或原羊睪丸細胞是最常用的分離細胞,然而,原代細胞最明顯的缺點是需要不斷地建立新的培養物來避免細胞批次變異和外來物質的污染。因此,相應的細胞系是更為方便的選擇。目前幼羔羊睪丸細胞系(OA3.Ts)[28]和牛腎細胞(MDBK)[29]已被評估為原代細胞的替代品。有研究顯示該病毒可以在許多其他細胞培養物上生長,如犢牛和羔羊的腎上腺和甲狀腺等原代細胞,以及倉鼠腎細胞(BHK-21)和非洲綠猴腎細胞(Vero)[30]等。LSDV的細胞病變產生較慢,通常在10 d后才能看到細胞病變,盲傳5代后可以用特異的熒光抗體觀察到細胞內出現胞漿內包涵體。已經適應于細胞培養物內生長的病毒,可在接種后24~48 h內使細胞培養物內出現長梭形細胞,并且細胞聚集生長并且成團,經過反復凍融離心后可收毒。然而,這種方法耗時長,需要一定的實驗條件和專業人員,且并不能對病毒做出鑒別診斷,因此難以推廣。
4.2 免疫學方法
通過誘導不同細胞斑塊的形成,抗山羊痘病毒血清免疫染色可診斷出山羊痘病毒,其具有以細胞拉長為特征的細胞病變效應,但不能區分LSDV、SPPV和GTPV這3種病毒。目前測定山羊痘病毒抗體的金標準是病毒中和試驗,然而這種方法雖然能有效檢測病毒抗體,但它速度慢,耗人力且需要活的病毒,這在無病原國家通常是不合適的。在擁有特異性抗體的情況下,免疫印跡方法(Western blot)具更高的特異性和敏感性,然而這種方法需要熟練的抗體制備技術,在基層無法推廣。使用滅活山羊痘病毒可以作為ELISA抗原,但是在常規診斷實驗室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病毒培養需要嚴格的生物控制設施。
4.3 分子學方法
聚合酶鏈反應(PCR)和實時PCR檢測(qPCR)是檢測山羊痘病毒基因組快速而敏感的診斷技術。實驗室可以從結痂組織均質上清液、抗凝血液或冷凍牛精液中提取基因組DNA(有研究發現在患病牛鼻沖洗液中也出現了少量病毒[18]),裂解后用洗脫緩沖液洗脫,紫外分光光度計檢查DNA濃度,并將DNA儲存在-20 ℃中備用。
PCR檢測方法比抗原捕獲ELISA方法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且不需要特異性抗體,降低了經濟成本。早在1998年Ireland就通過包膜蛋白(LSDV074)的引物成功檢測到了病毒[19],之后該方法成為多種檢測方法的衡量標準。然而山羊痘病毒屬的3種病毒相似度太高,無法通過普通PCR方法進行區分。
qPCR的優點在于更敏感并允許量化,還避免了在識別LSDV基因組時出現交叉污染的風險,降低了假陽性的概率[18]。RPO30 (RNA聚合酶亞基)[20]、P32和GPCR 在山羊痘病毒屬中高度保守,可以用來識別山羊痘病毒分離株。P32抗原是一種存在于所有山羊痘病毒中的結構蛋白,含有主要的抗原決定簇,其編碼的包膜蛋白與牛痘病毒H3L基因編碼的P35蛋白同源,并定位于成熟的細胞內病毒顆粒的膜表面。GPCR基因編碼1個與G蛋白偶聯趨化因子受體亞家族相關的蛋白。該蛋白具有G蛋白偶聯趨化因子受體超家族的關鍵結構特征,如7個疏水區域和第一、第二細胞外環中的半胱氨酸殘基。由于疫苗LSDV株中存在一個27 bp的缺失(LSDV126)[21],可用于野生型LSDV的特異性檢測[22],而SPPV和GTPV在其同源EEV序列中也出現了這27 bp的缺失,所以該區域也可以用于針對綿羊、山羊或牛病毒分離株的特異性分析[23]。
其他常用的生化檢測方法還包括基因測序、變性高效液相色譜技術(HRM)和環介導等溫核酸擴增技術(LAMP)。通過LSDV中保守序列測序,進行基因比對和系統進化樹分析,可以找到病毒來源和相似性,為流行病學調查提供指導和方向[24]。HRM指可以采用高分辨率熔化分析DNA片段進行PCR擴增,以檢測病毒[25],目前這項技術還沒有用于LSDV檢測。由于高度依賴DNA的質量和濃度,該方法無法在常規診斷中使用。LAMP是一種簡單、特異性和成本效益高的方法,其診斷精度與PCR相似[26]。
5 疫苗研發
目前的疫苗開發主要側重于減毒活疫苗的生產。減毒活疫苗主要可分為異源減毒活疫苗和同源減毒活疫苗。由于SPPV、GTPV和LSDV同屬于山羊痘病毒屬,且有交叉保護性[31],所以山羊痘疫苗和綿羊痘疫苗都能用來預防控制牛結節性皮膚病的傳播。山羊痘減毒活疫苗屬于LSD的異源減毒活疫苗,對于LSD的免疫接種,目前我國推薦使用5倍劑量的山羊痘疫苗用于預防 LSD[32]。在非洲和中東,有幾種異源減毒活疫苗目前被用于牛和小反芻動物接種,如羅馬尼亞(Romania)和南斯拉夫RM-65毒株(SPPV)以及Gorgan和Mysore毒株(GTPV),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牛上產生的副作用,但卻只能提供部分交叉保護[33]。
國外常用的疫苗是同源減毒株,如KSGPO-180、KSGPO-240和南非Neethling毒株 (LSDV)[34],其中Neething毒株已成功使用幾十年,但在俄羅斯發現幾種類似疫苗的重組菌株后,它們的安全性最近受到了質疑。2016年哈薩克斯坦暴發LSD,該國大規模地實施Lumpivax疫苗接種,此疫苗后來被發現是由3種不同毒株重組而成[33],對其他國家如中國、越南的致病毒株出現埋下了隱患。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建議在引入一種通常不用于牛的疫苗株之前,需要使用最敏感的品種(山羊或綿羊)進行對照試驗,因為山羊痘屬病毒疫苗株可在一些牛的接種部位產生較大的局部反應,除此之外LSDV疫苗接種提供的保護持續時間尚不清楚。由于這些因素的不確定性,導致一些畜主不愿意冒險打疫苗,從而阻礙了疫苗的推廣使用,然而LSD暴發會導致嚴重的經濟損失,所以更為安全有效的疫苗研發是十分必要的。
基因改造減毒活疫苗是未來應對疫病暴發的重要方向。與其他痘病毒一樣,LSDV 基因組編碼大量的免疫調節基因,通過基因工程方法刪除或插入這些基因可構建減毒活疫苗毒株[31]。
LSDV基因組中存在9個在SPPV和GTPV中不存在的基因,這是SPPV和GTPV因進化而丟失的基因,可能是LSDV感染牛的原因之一。這9個基因分別是LSDV特異性基因(LSDV132)、IL-1受體(IL-1R)(LSDV013)、LSDV002、LSDV155、LSDV004、LSDV153、LSDV009、LSDV026和LSDV136。這9個基因里有2個已經預測了其功能,第一個是位于ORF_013的IL-1樣受體,其作用是作為IL-1受體的誘餌來發生免疫逃避;第二個是位于ORF_026的F11L,已有研究證明其可以通過抑制Rho信號和破壞皮層肌動蛋白層在促進病毒逃逸中發揮作用[35]。除此之外的7個基因目前已經有人在進行相關研究。聶福平[6]已對ORF132進行功能預測并成功構建表達載體,為新型疫苗的研制奠定基礎。當黏液瘤病毒(也缺乏F11L同源物)被插入痘苗病毒中的F11L時,病毒的繁殖和體內外的傳播能力均得到增強[36]。ORF_009類似于痘苗病毒N2L的C末端結構域(25%~30%蛋白質序列標識),這是一種可以編碼IRF3抑制劑的基因[37]。目前對于這些毒力基因的研究還不透徹,需要進一步研究。
LSDV中的保守基因可以作為基因突變缺失的目標位點。胸苷激酶(TK)基因是山羊痘病毒屬病毒復制的非必需基因,缺失TK基因的GTPV突變株在神經細胞中的復制能力大為減弱,使疫苗株更加安全[38]。對LSDV的TK基因研究表明,與許多痘病毒一樣,TK活性對LSDV的生長很重要,該基因可以用作重組疫苗的插入位點[39]。由于痘病毒基因組大,減毒的LSDV還可以作為重組疫苗載體,與其他病毒疫苗形成二聯苗。
在LSDV基因組中還存在一些疫苗相關突變基因位點,如ORF_134,ORF_144,ORF_145和RF_019。其中ORF_134基因編碼的蛋白質與B22R(變異體)超家族C端有32%的相似性,而猴痘病毒B22R超家族中的MPXV197蛋白可抑制T細胞反應,增加病毒毒力[40]。ORF_144可能是牛痘病毒VV-Cop-A55R的同源物,編碼BTB/POZ結構域,cullin結合位點和4個C端kelch重復。有研究顯示所有的LDSV疫苗株的ORF_144位點上都存在+1的移碼突變(在S256處的T2至T3處)[5]。ORF_145則很可能是VV-Cop-B4R的同源物,編碼4個錨蛋白重復序列和1個C端PRANC/F盒結構域。這些牛痘病毒基因通常是通過kelch和錨蛋白介導的相互作用來促進病毒和宿主蛋白的泛素化和降解[41]。ORF_019可以編碼第二個類似于ORF_144的BTB/kelch蛋白,可能是VV-Cop-F3L的同源物,在有些LSDV疫苗中也觀察到了ORF_019的失活。
Erster等[42]對LSDV126基因和全病毒基因組序列進行系統發育分析,發現LSDV分離株形成了強毒和疫苗毒兩類。在這項分析中,所有缺乏快速感染牛能力的痘病毒只攜帶1個27 bp片段的拷貝,這表明LSDV126基因在痘病毒感染牛的能力上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還發現LSDV126形成的糖蛋白——VYDLPPND二聚體,被預測為1個抗原表位,而疫苗株中則沒有。這種表位的缺失可能有助于降低疫苗的傳染性,同時保留其在接種動物中誘導免疫狀態的能力。目前國內已有研究針對LSDV126發展出特異性探針來進行鑒別診斷[22],但是對于其免疫學特征還沒有進展,這可能是未來疫苗研究的一個方向。
此外,4種LSDV疫苗LW1959、Herbivac、OBP和Cro2016都出現了ORF_087和ORF_131的缺失。在這些分離株中,ORF_087編碼了一種可能由于缺失約50個氨基酸而無明顯作用的蛋白[43],它可能就是LSDV中晚期表達基因(VVCOPD10R)的同源基因,可以編碼2種山羊痘病毒屬突變蛋白之一,從而催化mRNA分解。ORF_131可以編碼一種在催化上不具活性的痘病毒過氧化鋅歧化酶的同源物,該蛋白的同源物可以調節超氧化物信號,也是影響病毒熱應力敏感性的主要病毒衣殼成分[44-45],已有研究表明SOD同源物可能提高免疫原性并降低毒力[46]。
值得注意的是,LSDV中國毒株(LSDV/China/Xinjiang/2019)被推測為疫苗樣毒株[47],提示目前在國內流行的病毒很有可能是疫苗株與自然毒重組衍生形成的,這種復雜性不僅給國內的牛結節性皮膚病疫情防控帶來了難題,也為疫苗的研制帶來了難題,如何有效檢出病毒以及研發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是目前的研究熱點。
6 小結
目前,WOAH將牛結節性皮膚病列為法定報告的動物疫病,我國農業農村部暫時將其作為二類動物疫病管理。牛結節性皮膚病的有效防控需要了解其直接或間接的傳播方式以及各種節肢動物的媒介作用,做好蚊、蠅、蠓、虻、蜱等蟲媒的滅殺工作,并對隔離場所內外環境進行嚴格消毒。必要時采取封鎖、撲殺等措施。按照動物防疫法和農業農村部規定,對牛結節性皮膚病疫情實行快報制度。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牛出現疑似牛結節性皮膚病癥狀,應立即向所在地畜牧獸醫主管部門、動物衛生監督機構或動物疫病預防控制機構報告,有關單位接到報告后應立即按規定通報信息,按照“可疑疫情—疑似疫情—確診疫情”的程序認定疫情。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開發出一種快速確認的診斷方法,探究當前使用的疫苗的有效性,了解疫苗保護的免疫學相關性,開發出新型、安全、高效和性價比高的動物疫苗,包括滅活疫苗和潛在的重組疫苗,同時加強對各級畜牧獸醫主管部門、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工作人員的技術培訓,提高從業人員防治意識[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