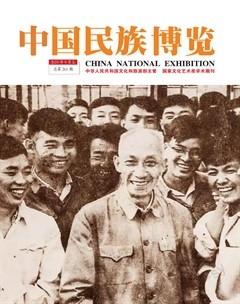淺析不同版本“趙氏孤兒”結構重塑的差異
李敏
【摘 要】“趙氏孤兒”的故事經由元代戲劇家紀君祥的藝術加工后,首次以戲劇的面貌進入大眾視野,自此成為國內經典的戲曲母題。因其有著極高的悲劇性和思想價值,它先后在不同時代被改寫成多重版本。由于創作者的主觀思想、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觀眾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劇本的結構形式呈現出獨樹一幟的風格。故而,本文將京劇版、田沁鑫話劇版與舞劇版作比較評論,分析三者在結構重塑上的差異,進而剖析它們所宣揚的不同價值觀。
【關鍵詞】趙氏孤兒;結構情節;主題觀念;人物形象
【中圖分類號】J821;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17—017—03
在元雜劇《趙氏孤兒》問世前,程嬰救孤的故事在社會中就有很大的影響力,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皆看重故事中的“忠義”精神。在紀君祥改編成雜劇后,趙氏孤兒的故事霎時間傳遍大江南北,成為中國第一部走出國門的戲劇作品,后在不同時代受到不同程度地改編及搬演。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雖改編作品的故事情節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改編者向觀眾呈現的審美意識、價值取向亦有所差別。筆者選擇京劇《趙氏孤兒》的原因一是看重該戲劇作品的經典性,二是深入剖析其結構形式有助于豐盈當下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選擇田沁鑫版話劇《趙氏孤兒》的原因最初是被田導“我做戲,因為我悲傷”的話所觸動,在觀看整部話劇后,又深深地被劇中包裹的理想主義色彩所吸引,孤兒身上散發的種種焦慮、掙扎的情緒直擊我心;選擇舞劇《趙氏孤兒》的最大原因是被演員的表演張力所震撼,各環節間的情緒傳遞細膩且真實,讓我不由得沉浸在此刻的歷史空間中,跟著演員或緊張、或憤怒、或哭泣。
故而,本文選取這三個改編版本作對比評論,深刻剖析三者在結構重塑上的差異,以此來探究不同的價值取向。自古以來,傳統意義上“忠義之臣”的“忠”指的是“報效君王”,而京劇《趙氏孤兒》卻將“愛民”思想化為忠義精神的主體部分,更看重“愛護百姓”的忠,從而生發反封建、反壓迫的思想意識。田沁鑫版話劇《趙氏孤兒》依托《左傳》的只言片語,旨在彰顯程嬰身上難能可貴的誠信意識。在社會價值觀歪曲、混亂的狀況下,驅使程嬰決心救孤的不再是誓死效忠君主的愚忠,而是一種“抱誠守真”的誠信精神。舞劇《趙氏孤兒》的劇情采用平凡化處理,意在消解傳統舞劇的說教意義,突出歷史洪流中小人物的生命境遇,從而向觀眾呈現普遍意義上的人性及道德。
一
戲曲理論家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過:“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換言之,一部戲劇作品大獲成功的關鍵是看創作者能否將零散的素材編織地渾然天成、緊密細致。京劇《趙氏孤兒》是劇作家王雁在1896年以劇目《搜孤救孤》為模本,并借用傳統秦腔的唱法創作而成。全劇在忠奸對立的模式下徐徐展開,圍繞著“搜孤救孤”這一核心從開場到結尾不斷地打造各種懸念,令觀眾連續產生新的審美愉悅,進而將戲推向高潮。全劇共分為四部分:趙家滿門遇害、程嬰救孤出宮、公孫二人設計保全孤兒、孤兒復仇,而第三場《撲犬》的情節最是迷霧叢生,在極度驚險的情境下突顯善惡斗爭的慘烈。
首先,基于結構重塑的需要,劇作家進一步增加并變動了故事情節,以此升華愛民思想。該版將《斥賊》《行刺》《撲犬》放在戲曲的開場部分,旨在突出趙盾與屠岸賈之間的矛盾并非是私人恩怨,而是事關國家與民生的忠奸對立。其次,在新增的孤兒《遇母》這場戲中,孤兒斬殺屠岸賈的行動既不是受新君主的命令,大仇得報后也沒有元雜劇里的加封情景,只有母子團圓的喜悅。這一改編雖然削減了悲劇的“悲”,卻使得孤兒的身份得到了合理的邏輯支撐,并且極大滿足中國人喜好“大團圓結局”的審美訴求。這種大悲后亦有大喜的創作手法也傳達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理,為觀眾提供強烈的情感慰藉。除此,京劇將“愛民”思想化為“忠”的一部分,以此宣揚“愛護百姓”的進步精神。戲曲一開場,伴隨著西皮快板,魏絳緩緩唱著“主公不把早朝上,貪戀酒色太荒唐……闖進桃園把理講”,類似的唱段在劇本中比比皆是。劇作家這樣安排,一是為了從側面體現出生活在暴君統治下百姓的真實現狀;二是為了表明趙盾、魏絳敢于指佞觸邪、痛斥君主的“附膻逐臭”,將創作主題升華至愛民及反封建的高度。再者,由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倫理綱常一直占據封建宗法制社會的絕對話語權,這就意味著群體價值勢必會逾越于個體價值之上。而“仁”“禮”更是儒家宗法制社會“群治”的根基,二者的實現均以“克己”為前提,即將犧牲個體的自由意志作為先決條件。故而,這種宏大的話語敘事體系勢必會影響劇作家王雁的創作,劇中她將程嬰與屠岸賈設為主要人物,在緊湊的矛盾沖突中拿捏縱橫交錯的人物關系,對程嬰的性格塑造在審美層面上呈現出一種超脫人性的“大義”。他為保全孤兒不惜鞭打好友、犧牲親子,這種比自我犧牲更難以承受的悲慘考驗中更易彰顯人物的忠肝義膽。一言以蔽之,全劇刻畫的諸多游離于封建倫理框架外的、自發的復仇行為,總體表現出一種超越且試圖消解封建倫理的反抗精神。
二
當代社會對于個體價值的重視及推崇,必定會引發戲劇界內對傳統題材的解構與重塑。無獨有偶,北京人藝與中國國家話劇院先后推出兩版《趙氏孤兒》,它們皆摒除了原有的宏大話語敘事,將隱藏在價值符號背后的個體價值重新推到大眾面前,讓所有的忠奸善惡包裹在人性的復雜性中。而中國國家話劇院版的《趙氏孤兒》更是將趙孤塑造成哈姆雷特式的悲情角色,當身世之謎揭曉后,孤兒深陷于迷茫和身份缺失的痛苦中,猶如哈姆雷特在了解殺父真相后的進退失據。故而,田沁鑫導演對戲劇結構作了如下調整:以往劇本中的說話權都是給予程嬰、公孫杵臼這樣的忠臣義士,屠岸賈作為反派角色不會被賦予自我辯護的權利。在現代社會,民眾對平等的渴望和呼喚愈發強烈。此觀念投射到話劇中則體現出劇里每個人都有平等說話的權利。田沁鑫給予屠岸賈向孤兒陳述身世的資格,為此話劇不再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開展劇情,而是將故事的開端限定在十六年后孤兒長大成人這一時間段,期間又夾雜著往事的插敘回憶及孤兒夢境。因為有著平等的話語權,程嬰和屠岸賈二人分別向孤兒講述成人前的事情。孤兒周圍充斥著兩種聲音、兩個立場,不由得陷進無邊的迷茫當中。其實此時的孤兒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父母雙亡的孤兒形象,而是一種精神孤獨的象征。而田導又敏銳地捕捉到“當下的生活雖看似繁花似錦、便捷且時尚,但人與人的交往卻止于表面,沒有深層的內心接觸”,有著無盡的心靈孤寂。所以,她在劇末讓孤兒發出了“今天以前,我有兩個父親,今天以后,我是孤兒”的吶喊聲。這樣安排,一是為了體現孤兒敢于走出兩種權威話語牢籠的堅定信心,二是讓其用人文反思者的身份去警醒世人重新認識自我、勇于對抗孤獨。除此,導演還利用詩劇的表現形式,將中國的靈動意境說與西方的抽象美學原則一同融進舞臺布置中,從而刻畫復雜的時空結構,呈現出強勁的視覺沖擊力。比如,舞臺的底色為大面積的“紅與黑”色塊,直接體現了中國式的審美心理。因為中國人習慣把紅與黑與明暗結合起來,并將其視為生命與死亡、喜慶和晦氣的象征。
由于趙氏孤兒的故事有著漫長的完善過程,這期間歷史記載難免充滿不確定性,這種細微差異既為后世的創作者提供無限的思考空間,也給予改編后的作品必要且合理的邏輯支點。田導則憑借《左傳》中的只言片語暗示這場悲劇發生的雙重原因:一是晉國皇室與趙氏家族或許積怨已久;二是莊姬與趙纓的不正當關系可能間接導致悲劇爆發。故而,在保留元雜劇基本脈絡的基礎上,她大膽地將“趙朔弒君”的情節加入劇本中,并利用氛圍式的思想傳達既讓觀眾看到了真實的春秋歷史,也消解了元雜劇里“正義與邪惡”相對立的意識。縱使弒君源于莊姬荒亂被發現后的誣告,趙家滿門忠烈亦會變成眾人口中的“亂臣賊子”。所以,話劇顛覆原著的目的,或許不是為了廓清這段歷史,而是為了彰顯程嬰身上難能可貴的誠信意識。在社會價值觀歪曲、混亂的狀況下,驅使程嬰決心救孤的不再是誓死效忠君主的愚忠,而是一種“抱誠守真”精神。
除此,田沁鑫以特有的女性眼光有意識地在劇中增添莊姬的戲份,并著力挖掘她的內心情感,繼而解構傳統的女性形象。莊姬既是女人又是母親,她在身體的反抗與建構中呈現出不同的心理訴求。田導這樣設置是為了隱晦表達女性的身份認同危機,進而剖析出女性成長中的憂慮與反思。古代社會是父權制社會,男性往往享有絕對的支配權及凝視權,田沁鑫卻在《趙氏孤兒》里用直白的語言書寫了莊姬身體的反抗意識,以此彰顯女性對于男權社會的初步顛覆。故事的開場,莊姬就以魑魅魍魎的模樣游離于舞臺上,對孤兒、程嬰和屠岸賈三人進行凝視,用提醒程嬰勿忘往事的辦法將懦弱的女性身份置換出去,轉為“復仇”中人。
簡言之,程嬰在話劇中被置于一個禮樂缺失的時代,身為一介草澤醫生,能讓莊姬托孤、韓厥與公孫杵臼赴死相助,全靠他的誠信及道義。在他身上最難能可貴的精神不再是徹徹底底的“義”,而是一諾千金的誠信意識。加之社會中普遍存在著情感缺失現象,田沁鑫重塑話劇結構與人物形象亦是為了緩解群體心靈的孤寂與不安。
三
舞劇《趙氏孤兒》采用獨白的形式遞進劇情,共分“屠殺夜”與“成人日”兩個篇章。首先,為了讓觀眾更容易看懂劇情,舞劇采用“線性”的劇情結構。以程嬰為主線,輔以程嬰妻及屠岸賈等副線,用循序漸進、環環相扣的演繹方式講述一個完完整整的故事。其次,舞劇采用隱喻表意、首尾呼應的敘事結構。道具是建造完美敘事策略必不可少的藝術手段,不僅是因為它本身具有表情達意的審美功能,更重要的是準確使用道具能夠最大化地提升舞劇的表達空間,與觀眾形成情感上的共鳴。舞劇《趙氏孤兒》用到最多的道具是紅綢及紗幕,前者作為象征性的“規約符號”存在。比如在《救孤》這幕中,紅綢化為“親子”的意象,一團紅綢散落在地時,暗示著孤兒被屠岸賈無情殺死,引發觀者強烈的心理聯想。而后程嬰妻絕望地抱起“孩子”,紅綢從她手中慢慢脫落,出現一座細長的“紅橋”。在這里紅綢暗示著“血脈”和夫妻間的“紐帶”,也隱喻著可怕的死亡。而屠岸賈被孤兒殺死時,一條紅綢從天而降亦代表死亡。后者的功能在于指引劇情轉變以及構建時空結構。也是在《救孤》這幕中,當舞臺上“重映”程嬰與妻子的恩愛日常時,后臺的黑色紗幕迅速化為敘事時空的“分界線”,使觀眾一面沉浸在二人相濡以沫的心理空間中,一面目睹著現實世界里官兵用全城嬰兒的性命威脅交孤的凄慘場面。加之道具與音樂的巧妙配合,整部作品充斥著生命與死亡的沉重感,以此升華“一義孤行”的宏偉主題。再者,編導用中國古典舞的律動方式去塑造空靈生動的人物形象,表現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為觀眾展現最真實的善惡形態,進而對趙氏孤兒的故事完成現代化的重塑與顛覆。此外,舞劇采用“投奔”仇人進行復仇的結局,似乎營造一種眾叛親離的氛圍,從而踐踏主人公脆弱的尊嚴,彰顯這場忍辱負重的救孤行動是程嬰想逃卻逃不開的生死疲勞。
劇中將程嬰塑造成有著普通人最平凡的情感的忠義之士,支撐他完成“復仇”全局的信念不再是被滅門的趙氏全族,而是自己的妻子及早夭的孩子。舞臺上演員們用豐富的舞蹈語言書寫著強勁的情緒張力,既讓觀眾看到程嬰身上“一義孤行”的不屈精神,又在忠孝難兩全的躊躇中牽引出人性的掙扎。在《托孤》這場戲中,莊姬與家丁一起下跪哀求程嬰收留趙孤,程嬰表現出的神色不似京劇中的堅定,反而多了幾分躊躇和害怕。只見演員胡陽跌跌撞撞地后退、用下跪磕頭、翻身的動作來彰顯程嬰內心的驚慌失措。但當程嬰看見家丁們被屠岸賈誅殺時,仁心仁術的他忽然就邁不開逃跑的步子,毫不猶豫地丟下藥箱跑去營救……如此看出,程嬰在畏懼與仁愛之間本能地選擇后者。在目睹親子被摔死后,胡陽用獨舞將一個父親的痛苦、自怨自艾及對妻子無比愧疚的心情淋漓盡致地演繹出來。以上劇情的平凡化處理,皆是編導對程嬰的普通人身份所作的合理申訴,同時又想消解舞劇的說教意義,使觀眾在強烈的情感落差下體驗小人物的生命境遇。縱使程嬰表現地再大義凜然,也不過是個被命運裹挾著被迫扛起道義重任的普通人。
一言以蔽之,舞劇中的人物逐漸從“大忠大義”的模板下抽離出來,聚焦于個體真實的生命境遇,對元版人物作重塑置換,以此在人文的關懷中彰顯情感的魅力。
參考文獻:
[1]田沁鑫.我做戲,因為我悲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2]陳杰.經典戲劇作品的現代價值——21世紀戲劇舞臺上的《趙氏孤兒》[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20(5).
[3]鄒紅.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歷史劇《趙氏孤兒》的改編策略[A].和諧社會:社會公正與風險管理——2005學術前沿論壇論文集(下卷)[C].2005.
[4]宋堯.《趙氏孤兒》的京劇版與電影之比較批評[J].安徽文學,2014(5).
[5]文維丞.論“趙氏孤兒”主題的轉變對劇本創作的影響——以《趙氏孤兒》元雜劇、京劇、電影劇本為例[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6(4).
[6]瞿錦雯.論田沁鑫版話劇《趙氏孤兒》中的女性身體書寫[J].當代戲劇,2021(3).
[7]蘇翔.淺析中國舞劇《趙氏孤兒》[J].民族藝林,2017(3).
[8]沈佳楠.個體生存境遇與生命經驗的當代表達一淺析舞劇《趙氏孤兒》的改編策略[J].舞蹈,2020(2).